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法律系畢業,立即改念歷史。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網址:blog.roodo.com/chita
這個八月是二戰終結七十年漣漪激盪的時節。一方面,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安保法制(新安保法)引發國內外議論(內部騷動更甚於國際質疑);另一方面,廣島、長崎都先後舉行了原爆七十年的紀念活動,首相安倍晉三重申「堅持非核三原則」(對核子武器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當然,玉音放送的八月十五終戰日,從來就不是句點,那是接力問答,安倍有關終戰七十周年的談話有提及道歉但是否誠意?後續如何?其後,安倍的中國行暫緩,中國假九三之名(日軍受降日)閱兵,連戰前往北京匍伏稱臣……一切的一切,漣漪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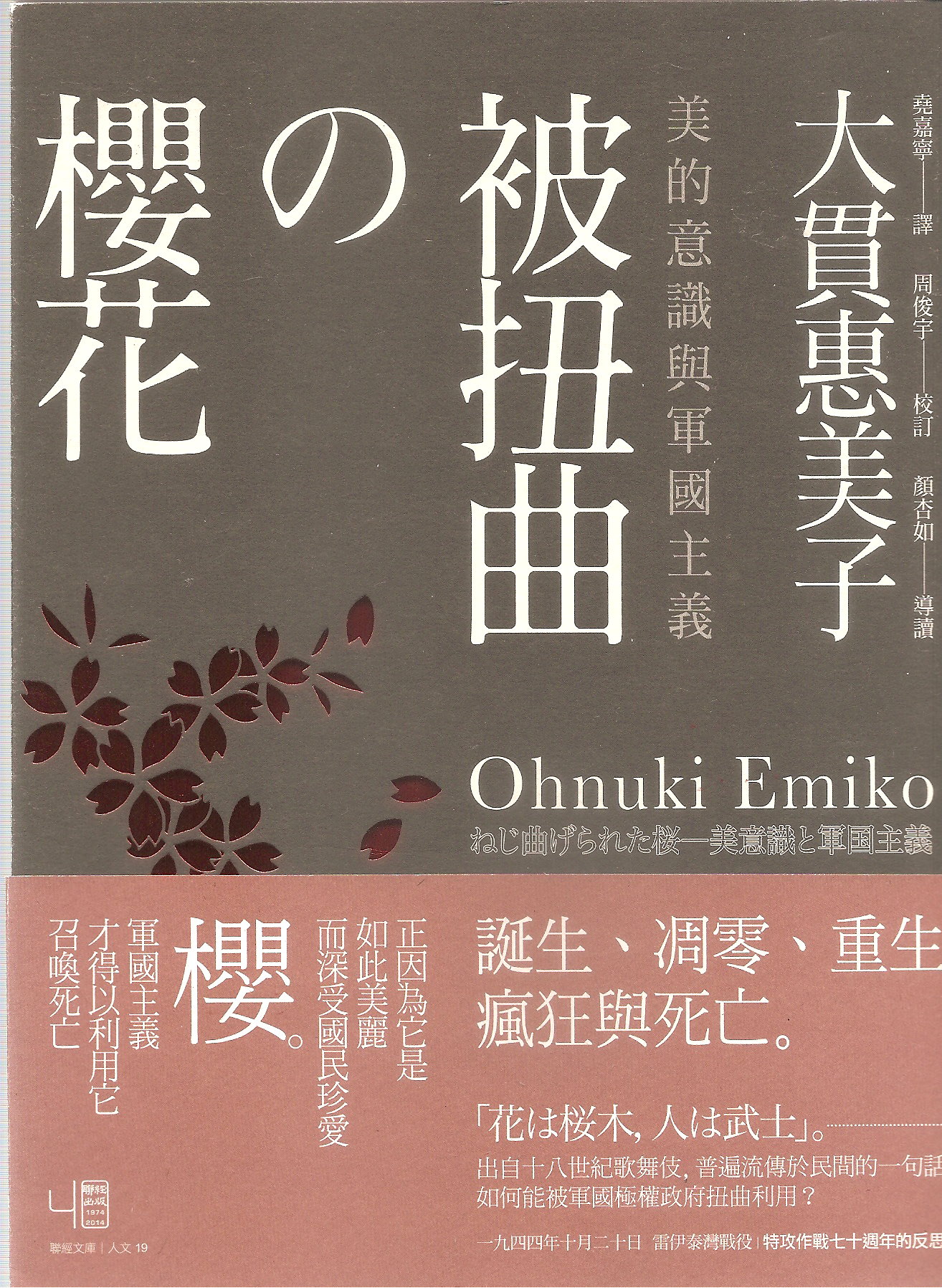
相較於德國對二戰的全盤認罪,日本的彆扭以及戰後的迅速復甦,致使嫉恨在東亞(尤其是中、韓)蔓延開來。咎責日本是絕對必要,但周邊的中、韓、朝(鮮)等國不以追求東亞和平為職志,徒以仇日作支架(甚或是以仇日遮掩內部矛盾),也是治絲益棼的主因。簡言之,將日本視為鐵板一塊,不認真思索日本國內對戰爭的態度,且隨時間物移必有新的詮解,就勢必一再扎稻草人猛刺,遑論進一步理解日本這民族是怎回事!
長期以來,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世人理解日本「國民性」的經典力作。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劍(刀)是武士象徵,日本文化的矛盾/雙重性(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在其筆下鮮明有致,之所以如此,潘乃德認為幼時教養與成人教養斷裂所以致之;她更以西方人重視內在罪責(sin),東方人著重表象羞恥(shame)作為「文化類型」的對比。凡此,都深深影響了戰後的日本研究。即使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探求日本文化的方式較潘乃德上天入地求之遍,但形之於《鏡像下的日本人》、《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諸書的基本框架仍是潘乃德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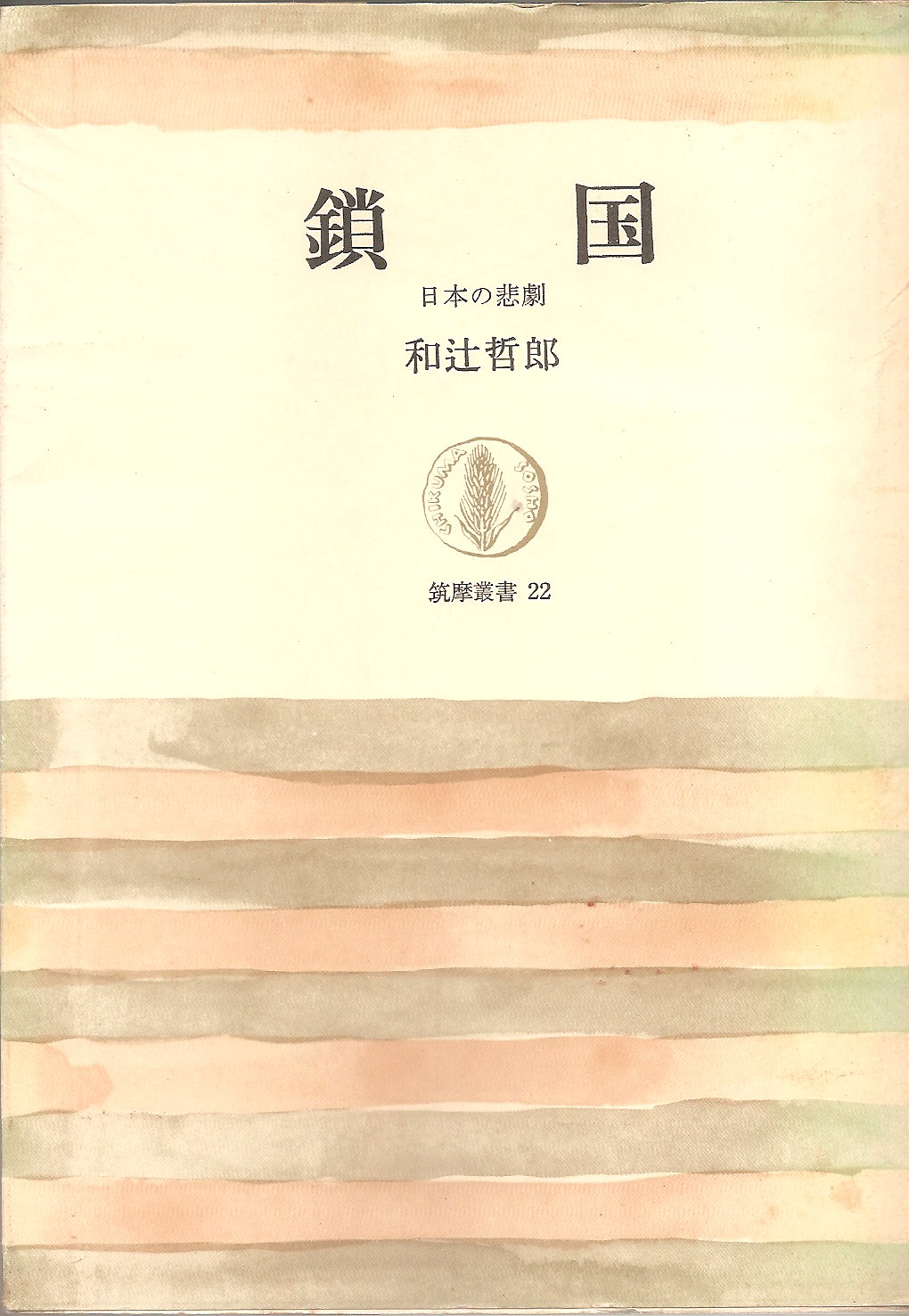
見宮廟之美(謎)而盡在牆外逡巡不前,終窺不得堂奧。所以與其試問外人(雖然這些洋菩薩都很了得),反求日本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終戰初期,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即撰寫《鎖國──日本の悲劇》(1950年),指陳「近世初期新科學發展以來,歐美人花費三百年的歲月使科學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而日本民族在這發展的期間鎖住國門,其後的250年間通過國家權力遮斷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響」。
然而這種喟歎近於德國歷史主義大家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在1946年以83歲高齡疾書的《德國的浩劫》(Die Deutsche Katastrophe),俱屬時代老人的生命感懷。畢竟,德國歷史主義的理路與國家主義的風潮時有交錯,而京都學派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亦頗曖昧。所以和辻哲郎、邁乃克的沈痛懺語必緣於切割,而切割常會藕斷絲連,難以立即直指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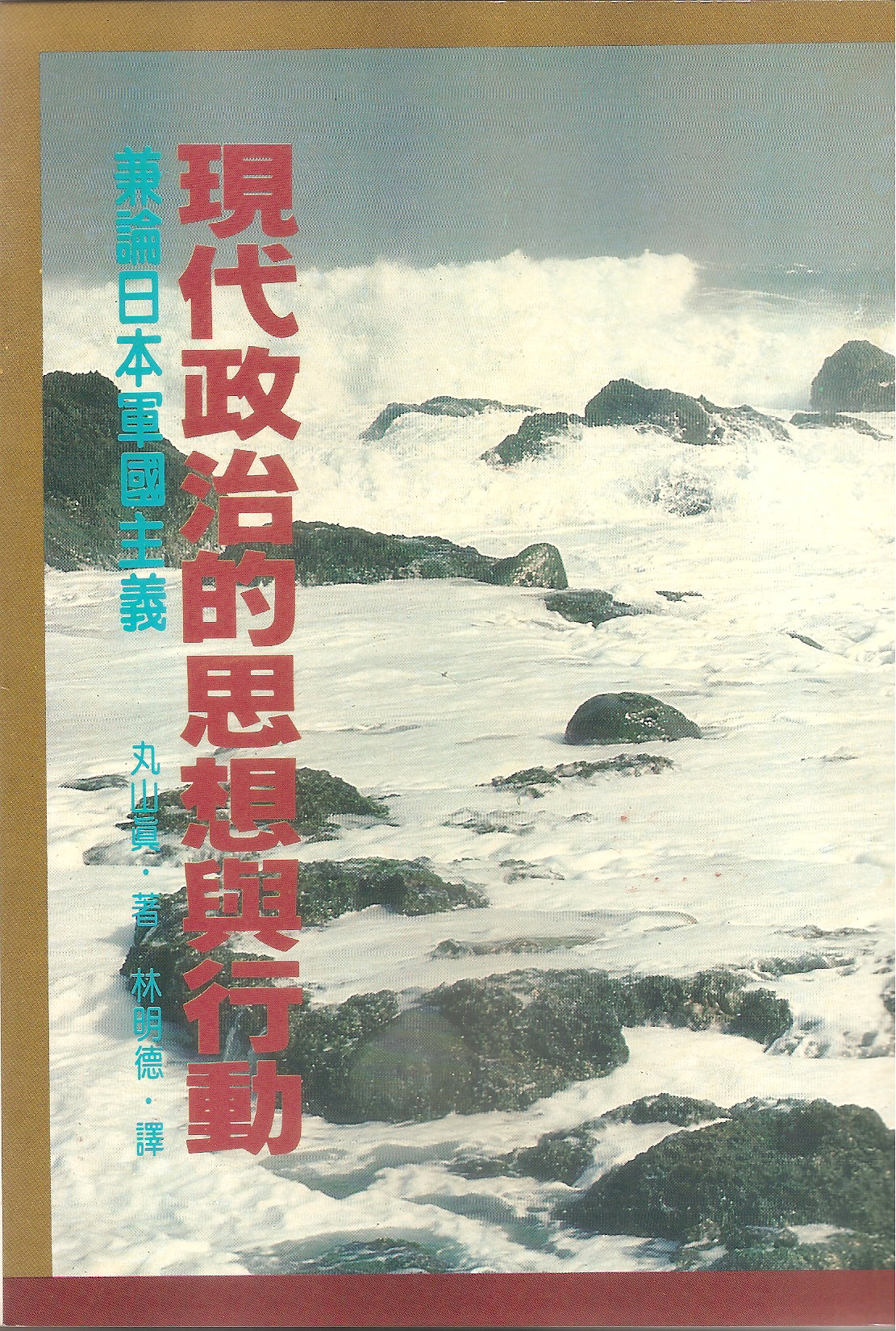
深度批判首推丸山真男。作為戰後日本政治思想宗師的丸山,他批判日本的「超國家主義」(ultra nationalism),直入核心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侏儒法西斯體制,亦即掌握統帥權的天皇緘默、不介入,各層級官僚、軍人的個人意志脆弱以致隨風搖曳,終讓軍方、浪人以下剋上,造成既成事實後讓日本一步步通往修羅道。這既是憲政缺憾,更與日本政治的精神狀況息息相關。丸山追溯日本的傳統思想,提出一種「執拗的低音」的理念,認為外來的儒家、佛教、基督教諸文化,都會被日本深層不移的本土性所修正,這些神祕、內在的風俗、法則,到了高舉「八紘一宇」的軍國年代,就如薪火全面延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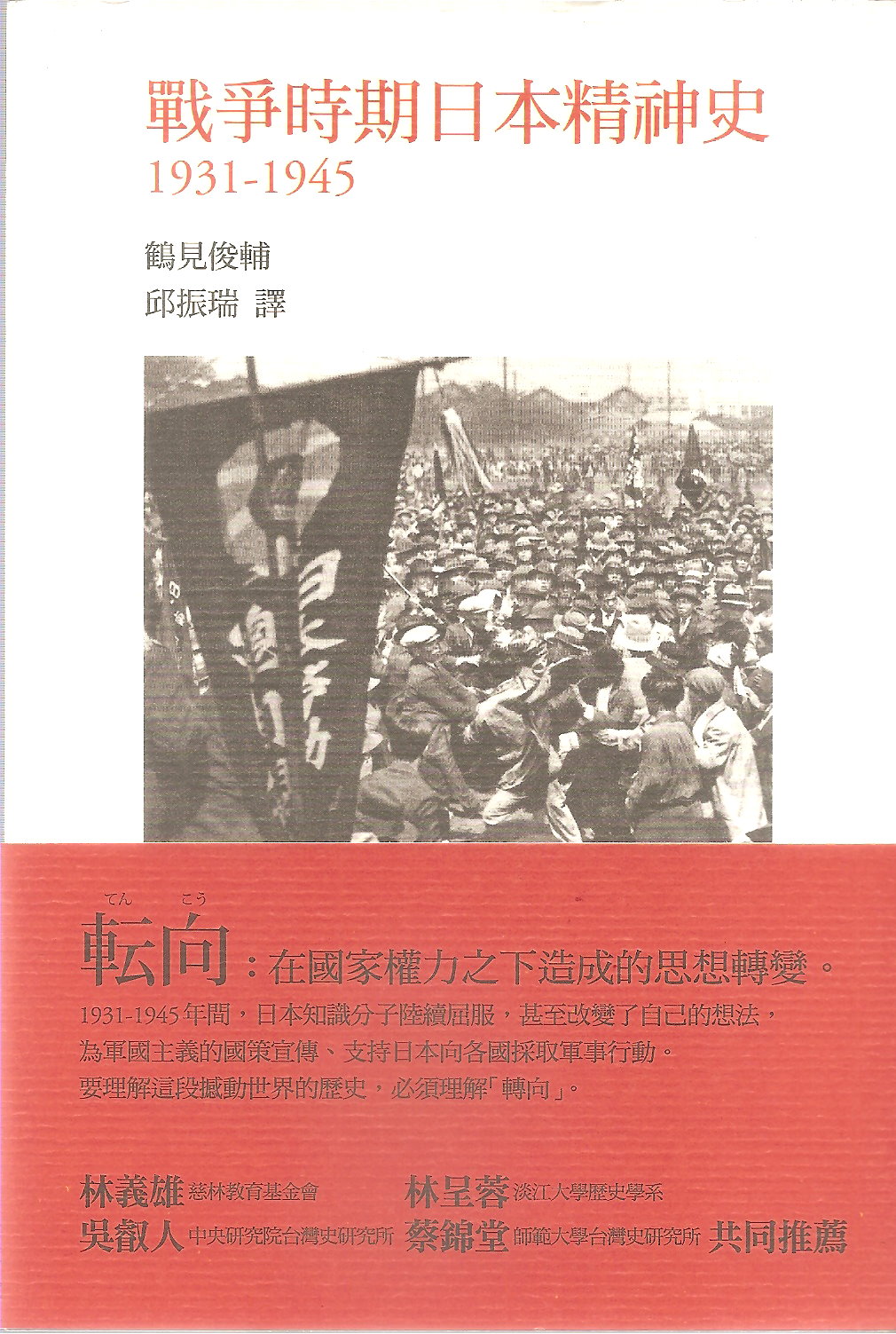
今夏(7月 20日)甫過世的自由派學者、行動家鶴見俊輔(後藤新平外孫)更值一提。他首揭「十五年戰爭」一詞,用以稱謂日本捲入戰爭係法西斯軍國主義系列行動之總合,所以不該祇談日本涉入與美國交戰的時期(不論叫「大東亞戰爭」或「太平洋戰爭」),這會淡化日本人的戰爭責任,如斯倡言若沒睿智與勇氣是做不來的。依循「十五年戰爭」史觀,鶴見關於戰爭/法西斯/國民精神的總批判,遂深化結晶為《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書。
鶴見獨樹一幟之處在於,他冷冽面對但擴展了「轉向」問題的思惟。日本從昭和年號開始,軍國氣焰始張揚,左翼勢力開始遭到清掃,1933年6月10日,日共委員長佐野學、中央委員鍋山貞親於獄中發表《致共同被告同志書》,撤回共產黨的主張,並肯認帝國出兵滿洲的方針。這一共同聲明發表後,三年內有74%的政治判刑者跟著「轉向」。這既是日本左翼的重挫,更是世界左翼史上的大驚奇。
鶴見解析「轉向」的成因包含國家強制力與個人的自發性,關於後者,鶴見靈光直指係源於日本的鎖國性。檢視當時的左翼被告和起訴者幾乎都來自「東大新人會」,封建意識形塑出的「想像共同體」,就讓多數共產黨人集體「轉向」。鶴見更拿江戶中期以來始終盛行不衰的《忠臣藏》(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故事)為例,說明日本人在鎖國狀態下,一切祇為最初的目標而思想、活動,絕不改易初衷,此種「忠臣藏症候群」不但可解釋日本盲目走向戰爭的集體心理,「轉向」於此也有了一番讓人拍案叫絕的詮解──改革必須立基於傳統,日本有「自我完結性」的能力,於是馬克思共產思想就被軍國法西斯之魂替代了。
「轉向」也和「國體」的建構與變易有關。鶴見指出明治維新以後的新政體,可分為顯教與密教兩部分。顯教係尊崇日本自古以來的天皇制,密教部分則取經於西方文明。可惜當法西斯軍國主義瀰漫全日本後,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思惟就被顯教的天皇制吞沒,「轉向」於焉產生。鶴見整部書就在探索「十五年戰爭」期間,以「轉向」為主軸的日本精神面。
如鶴見這般深思熟慮且具體投入社會改造運動的知識分子,在日本或仍為少數,其綻放的思想結晶卻絕非周邊仇日國家所能輕意頡頏。
再就打破向來對日人的刻板印象來說,大貫惠美子綰合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與歷史學成就的《被扭曲の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殊值一讀。若說潘乃德之書是外部取徑、捨異求同的西方主義立場,那大貫惠美子則深入肌理、多元發光。她以豐富的史料呈現櫻花的多義:遠古時代是和農耕文化的宇宙觀貼合,平安時代則透顯貴族文化的「物哀」之情,中世紀以迄江戶時代,櫻花演變成日本獨具的文化象徵;然而近代天皇制昂揚的過程中被人為的扭曲,由文化而政治,成為「為天皇即國家而犧牲」的意識形態,其極致就是神風特攻隊。
然而,大貫以特攻隊的學徒兵所留下的手記、日記為本,證明在人/工具、家庭/國家的辯證中,人性的可貴與複雜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年輕人將美的價值投射到自己的理想主義和愛國心之上,使自己的犧牲得以正當化,成為源於高尚動機、追求美好目標的行動者。最後,大貫惠美子該書的主題是要回應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的著作《枝幹被扭曲之木──人類》。伯林的主調在於:極權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有秩序的馴化」是要將人「矯正得毫無價值」,參與扭曲的除了首惡、幫凶,所有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這股邪惡力量中,這是戰爭給予人們最深層的反思功課。
在詳研大貫惠美子這部滿是碎鑽的大書後,若再閱讀百田尚樹的《永遠の○》(或觀賞由岡田准一主演,同名改編的電影),或會對深愛家人不輕易言死的主人翁宮部久藏,何以會在最後關頭尋死的心理歷程有另一番體觸。也就是說,今日看待日本人的戰爭態度,先理解而後批判可能才是正途。一逕地仇日、窮追猛打,除了凸顯自身的愚騃、狹隘,更嚴重的是仇日背後暗藏更多不敢自揭的醜陋面貌。
試問,將二戰性質化約成「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官僚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等),以及依附此說的左翼寄生者,有無思索過僅以德、義、日三個軸心國為對象,是否忘卻反帝才該是二戰本質,準此,戰後霸主美帝固然該批判,但紅色帝國也不該寬宥,看看紅軍以解放之名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小國,東歐、東南歐,以及入侵德國之後,俄軍的燒殺姦淫擄掠,可說罄竹難書;且不僅於歐洲,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後,俄軍開拔進入中國東北,對日本、中國女性的姦辱,根本是禽獸不如。所以不批判紅色帝國者,必是當下匍伏於天朝主義的軟骨者。防制日本軍國幽靈復生固然重要,但縱容天朝主義猖獗無度,恐怕更不可能全面止戰,於是二戰終結七十年的今日,歐洲全面和解共創和平樂音,東亞卻是噪音、鐵蹄聲再起,和平猶如海市蜃樓。更可悲者,迷霧中的台灣祇讓人絕望!
(原文刊於《文訊》359期(2015年9月),今再就新聞事件和細節深化作補述,重新登載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