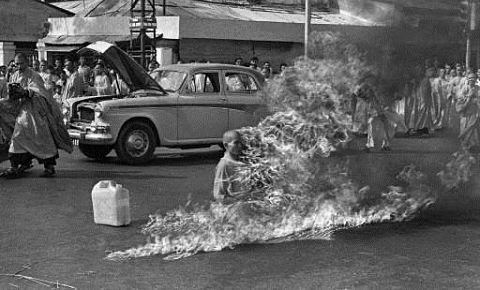也許年紀大了,容易感傷,也很輕易掉淚。元月16日下午參加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二任會長楊汝椿的公祭,深夜回家,讀了FB,看了前室友徐玫怡(知名的《交換日記》作者)有關鄭南榕自焚當天的回憶,哭了一場。
1990年左右,採訪聊天之餘,台北地檢署一名善於易術的主任檢察官,幫我卜了一卦說,晚年,我很容易傷懷掉淚,直到現在,我還不知真假。因為我寧可像我一位大學同學,那樣的早熟、那樣的浪漫。
那一年,在世新選修的「思想自由史」,大教室裡,滿滿的學生,一同上課的,還有「恰似你的溫柔」詞曲作者梁弘志,但我沒有崇拜他,反倒是被我一位同班同學感動。當年的老師,是被國民黨迫害,無處容身,而被世新專校創辦人成舍我收容的一位教授,當年我們並不知這樣因緣,只是被他上課的內容吸引、感動。
有一天上課,他談起了他的老師,新儒家學者徐復觀病逝的消息,老師談他的治學與思想啟蒙的生命歷程,同堂的張姓同學激動痛哭,從教室奔了出去,而我們,一群渾渾噩噩,不知所以的同學,完全不知發生何事,老師只說一句話︰「哪個同學跟他比較熟,出去安慰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