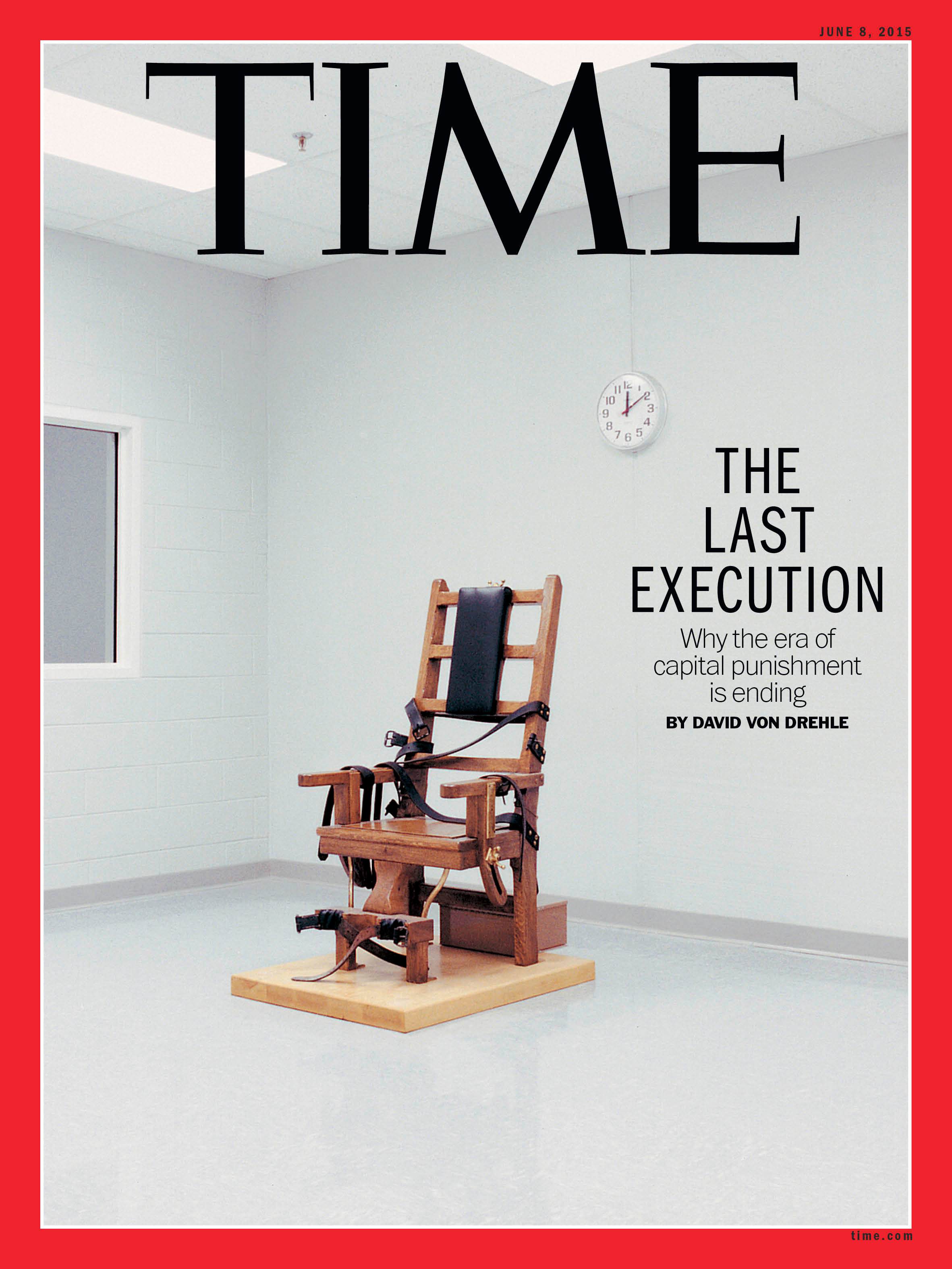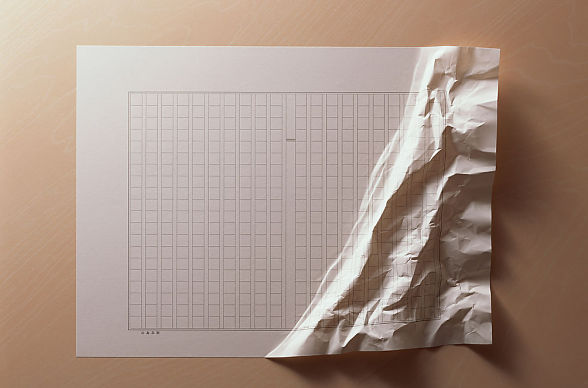有四個軍官兒子的劉桂秋伯伯,2007年在莒光新城去世,享年八十八歲。他是老爸最早認識的一位外省老芋仔,兩家也在光大一村鄰居數十年,交情頗深。
中日戰爭結束,中國「第三飛機製造廠」首批二十多人來台灣接收,劉伯伯是其中一員,任職台北新店辦事處。老爸以技工身分也被派往新店,兩人成為同事,後來一起調到大安辦事處,因此熟識起來。
劉伯伯年長老爸九歲,專長木工,原本從事飛機模型製作,不過來台接收工作,主要是將日軍所留財產及器具整理打包後,轉運至台中水湳。
位於四川的第三飛機製造廠遷來台灣建新廠,至1949年,雖然國共內戰情勢越來越不利,甫二十九歲的劉伯伯,還是趕回家鄉結婚,將十六歲新娘接來台中眷村。
劉伯伯後來在空軍「二區部」擔任國民黨書記,專責黨務工作,包括承辦每週莒光日活動、每月召開小組長會議等。雖然在軍中從事黨務,官階並未高人一等,後來以「上士」退伍,再以木工專長繼續到新成立的航發中心上班。
劉媽媽生了五男二女,前四個男孩長大都唸陸軍官校,部隊仕途順利,老大官拜上校,其他三人至少當到中校退伍。小兒子原本也是送往軍校,不過唸到一半覺得志趣不合,決定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