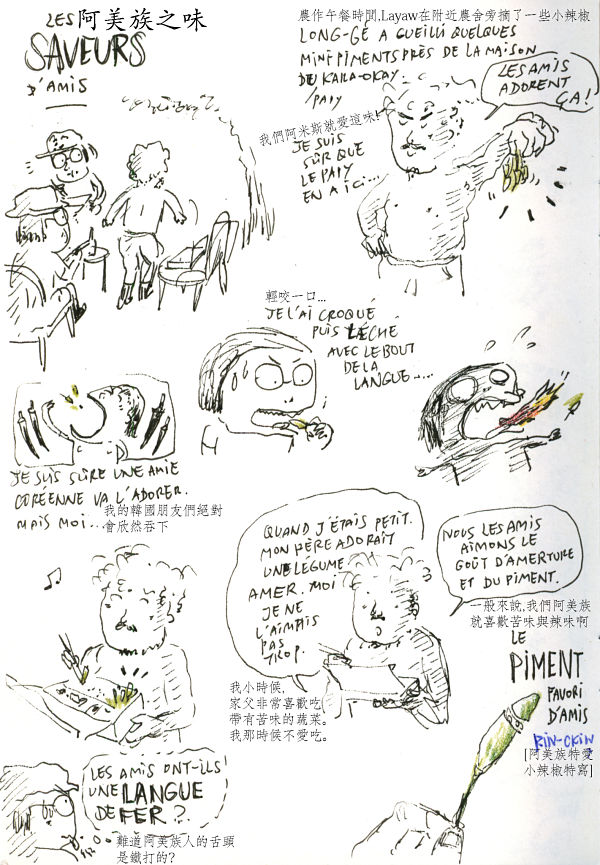在一個餐會上,認識了朋友的朋友,自我介紹之間,我告訴他我在研究教育與個人專業生涯規劃之間的關係。他問我用什麼樣的方法研究,我說,比較偏向個案分析。他聽了之後頗不以為然,詢問我:「你為什麼不用統計方法?」他認為,統計方法,才有精準的結果。
我認同,用統計方法常能產生精準的結果。但問題是,精準的結果是最有意義的結果嗎?
幾年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數量研究的重鎮)教授李維特 (Steven Levitt) 與專業作家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合作的著作:《蘋果橘子經濟學》,示範了如何用數據、統計方法研究各種有趣的問題。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章節,他整理了當時統計與數據分析在「教育」這項課題上,能找出什麼樣的結論。
在美國的教育研究領域,歷經多年,耗用大量資源、人力,時間的各種研究,已經能夠確認哪些因素和「考試成績」有高度相關性,例如:收入、社會地位、家中書籍數量、父母教育程度、母親第一胎生育年齡等。有一些因素,傳統上認為和孩子的成績表現可能有關,在這些研究中,幾乎能肯定其實無關,例如:體罰孩子、孩子看電視時間、住在地價高的區域、定期參觀博物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