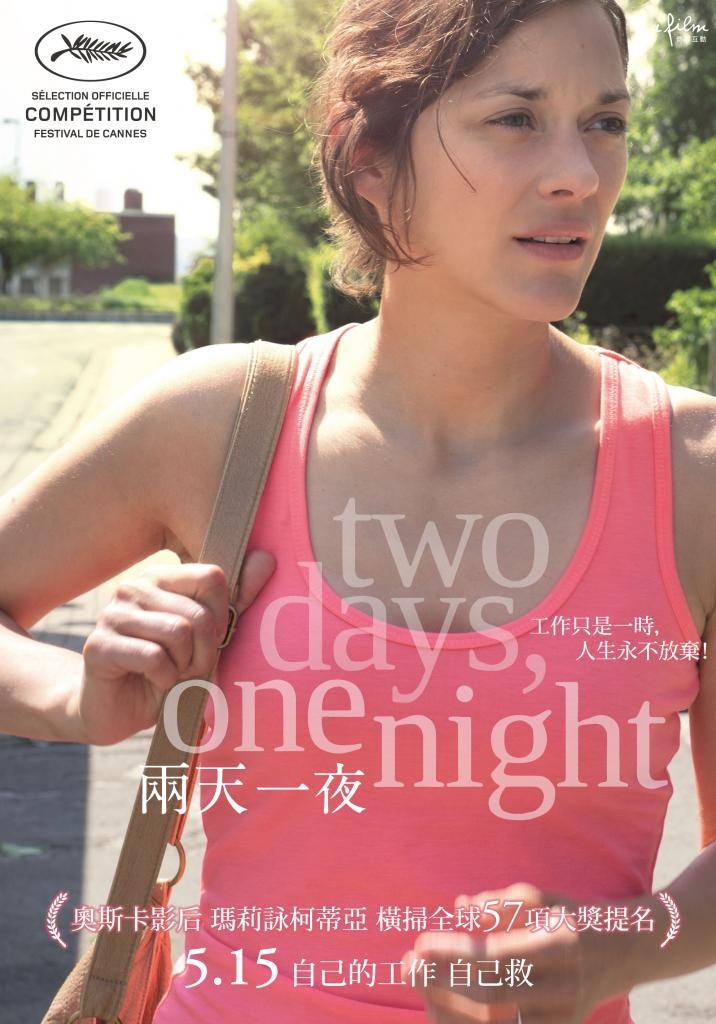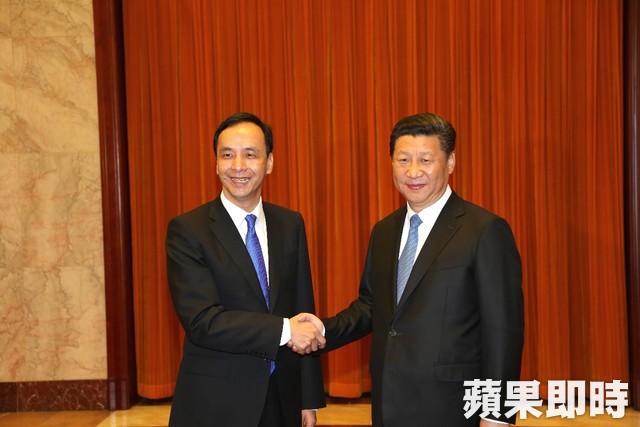三、
「北路番變」涉及的三個群體後代,應該要怎麼樣看待這段歷史呢?而我們又如何可能提供一種歷史文本,成為這三個群體後代可以共同接受的歷史呢?在這片充滿衝突、殖民與再殖民的土地上,這個問題應當是面對過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我們卻任憑各種權力與失憶的機制橫行,而鮮少慎重地面對這個問題。

標舉或忽略特定事件,並非只是——或者根本不是為了傳遞對某個特定事件的記憶與認識。更重要的,乃是事件的取捨、脈絡的交待所反映的,編寫者對事件所鑲嵌、依憑的的國家—社會—地理空間的大敘事有什麼樣的認識。教科書篇幅有限,特定事件是否存在於敘事之中,本可由編寫者自行取捨。而課綱一般性的描述,也留下了不少空間給編者處理,除非主事者有意在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的審核過程中加以阻擾,否則教科書本應呈現有限的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