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對於日本文學評論家而言,以現今的時點或者立場,去評價一名活躍於八十餘年前日本文壇的作家,必然存在著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嚴肅考驗。首先,論者必須冷靜自持看待其所有作品,尤其在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優缺點。其次就是,不因同情或支持其政治主張而放棄批判,更不能畏於已由其黨派樹立的文學權威地位,輕易隨之附言,因為任何預設性的既定評價,一開始就已經自失立場了。以《防雪林》、《蟹工船》、《在外地主》、《工廠細胞》《為黨生活的人》等小說聞名的小林多喜二(1903-1933),即是最佳的例證和挑戰,因為其作品有對於時代的控訴和對於弱勢底層者的同情,而這種描述又很容易將我們推向道德領域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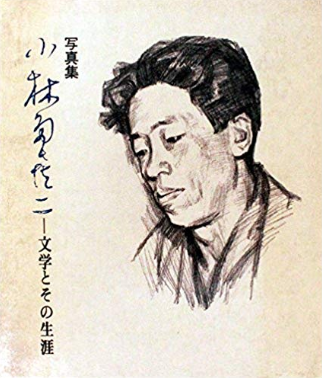
從文學啟蒙到憤怒青年
基本上,小林多喜二的文學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他於1918年就讀小樽市商業高校時,擔任校友會雜誌的編輯委員,已經開始發表和歌、新詩和小品文。1920年,他們編製手抄的傳閱雜誌《素描》,這個刊物即這些文藝青年的發表園地。他們同仁之間彼此約定,每月都要閱讀《文章世界》和《新潮》雜誌,並且鼓勵向這著名刊物投稿。他就曾向《小說俱樂部》《新興文學》等雜誌投稿。這個時期,日本的出版界已開始大量翻譯和介紹俄國和西歐的近代文學名著。譬如:俄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罪與罰》、屠格涅夫的《初戀》以及義大利詩人鄧南遮的《死的勝利》、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法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可謂迎向世界文學的時代。
在這文學思潮的刺激下,日本文壇亦催生出相應的作家和作品,如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秋田雨雀的〈國境之夜〉、江口渙的《惡靈》、小川未明的《紅色地平線》、有島武郎的《一則宣言》、倉田百三描寫親鸞和尚的劇本《出家及其弟子》、賀川豐彥描寫在神戶貧民窟富有傳教體驗的小說《越過死線》、島田清次郎的長篇小說《地上》,等等。毋庸說,這些作品自然成為當時文青們文學養份的來源。只不過,這些帶有感傷情調的作品,終究缺少深刻的思想性。
關於這個缺點,小林多喜二在〈新生的孩子〉一文中,亦有明確提及:「在這以後,我寫了不少拙劣的作品,只是在我心裡,總有一種要和過去作品訣別的心情。當然,這對我來說,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情,並不意味著在貶低以前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幼稚,但它是過去的我——至少是形成現在的我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希望諸位讀者能夠多加包涵。我期待讀過這兩篇小品之後,把您所感覺到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寫下來,因為不管好壞,它將成為我今後前進的路標(參見手塚英孝《小林多喜二傳》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眾所周知,小林多喜二非常仰慕志賀直哉(1883-1971)這位短篇小說之神的創作手法,並深受其文學影響,他們進而有書簡往返。其後,他陸續發表了〈龍介和乞丐〉(1922)、〈鑰匙〉(1923)和〈進入莽叢〉(1923)等作品。接著,他與脫離賣淫火坑的女子——田口瀧子互有愛意,寫了一系列戀愛題材的短篇小說。例如〈龍介的經驗〉(1925),描寫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婦女自主反抗的〈瀧子及其他〉(1928),即是以此為模型的作品。從寫作視點來看,這是他閱讀斯特林堡、杜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等作家作品,以及國內白樺派文學的影響延伸。
除了文學作品之外,彼時他亦開始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著作。他在日記中(1926年12月19日)寫道,他從圖書館借出小泉信三的《近代社會思想綱要》一書,還抄錄了全書目錄;翌年3月8日,他在日記中這樣提及:「馬克思《資本論》太難了,改讀《經濟學批判》,但不懂之處仍然不少……」進言之,在這個階段,小林多喜二已顯露出激進的思想,毫不掩飾要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企圖。他在1928年元旦的日記裡,這樣坦誠心跡:「啊,新的一年來到了,我們的時代來到了!……今後在思想上,一定要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前進。結識了古川、寺田等勞農黨的戰友,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正在燃燒的革命旗幟
第二期即1928年以後,小林多喜受到同陣營前輩作家葉山嘉樹的影響,在創作技巧上較為成熟的階段。不過這時候,他已是日共青年同盟的成員,為了徹底貫徹黨意和革命意志,他將文學創作視為鬥爭的武器,頻繁參與各種對抗性的社會活動。例如幫忙製作傳單、選舉海報或會計工作,這些事情後來成為他寫作的素材。
稍早之前,由於福本和夫的極左主張,造成了日共內部的分裂,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同盟就是在此條件成立的。1928年3月13日,以日本無產階級藝術同盟(簡稱「普羅藝」)、勞農藝術家同盟(簡稱「勞藝」)、前衛藝術家同盟(簡稱「普藝」)為主,建立了日本左翼文藝作家總聯合會,並召開了成立大會,旨在貫徹「文學應該成為黨的文學」、「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的馬列文藝思想。
然而,日本政府很早就察覺到這股危險思想的氣焰,是年3月15日,預審法官指揮警察展開了全國性的搜查逮捕,數千名日本共產黨員、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販售馬克思著作的書店、無產青年同盟本部、希望閣及其他50名相關人士均遭到了檢肅和拘留,其中有30名嫌疑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關押在市谷監獄。日共人士很頑強,他們遭到了逮捕卻並未停止地下活動。3月26日,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並創辦了「納普」的機關刊物《戰旗》。在他們看來,「文學」應當貫徹成為(日本共產)黨的文學,是其革命事業的組成部分。但可以看出,這個黨性大於作家的自由意志,蠻橫僵固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在抹煞創作者的主體性,這種做法必然走向為僵化的結局。
當時,小林多喜二還在北海道拓殖銀行上班,尚未轉戰到態勢森嚴的東京,他對於這起整肅日共的風潮這樣寫道:「彼時,普選剛剛結束,不久就發生3.15的鎮壓。我印象非常深刻,許多人從我的身邊被帶走了。那種衝擊的激烈程度,絕不是平常的事件相比。因為從不到15萬人口的北國小城中,就有將近200名工人、學生和工會幹部,逐個被警察押走了。」
在那以後,他以此事件為題材,寫作〈1928月3月15日〉這部中篇小說。他於該年6月初開始動筆,8月19日完稿。他曾經在日記裡記錄創作的過程:「由於我白天有工作,沒有完整的時間可使用,因此不管什麼時間、無論走到哪裡,我總是帶著紙和筆。通常我利用早晨上班前的時間,或下班以後同事們到經理那裡拍馬奉迎的時間,或者等候朋友見面的空檔,寫出五行十行的。換句話說,我沒有充分的時間伏案寫作,只能善用各種零碎的時間……。」就此而言,小林多喜二的寫作條件的確相當刻苦,這種精神卻能鼓勵其他的創作者。
另外,看得出來,他在其報導文學〈到東俱知安去〉中,同樣表現出可能遭受3.15事件波及的恐懼:「……自從選舉開始以來,工會人手不足,每天晚上,我們一下班就從公司(拓殖銀行)跑到二樓公會幫忙。由於職種不同的關係,我們不可能做那些前台的工作,所以做些後台的事務。盡可能地讓工會成員都上『前線』。話說回來,我可是賭上自己的飯碗,天天到工會來的。因為這件事如被公司知道,僅只這個理由,立即就可以把我開除了。即使這樣,只要我能力所及,必定盡力而為。每天深夜一點多鐘,我走在刺骨的寒風中,艱難步行一兩公里,才能回到郊外的住處。我曾經在狂風大雪的夜裡,一時不察,半個身子陷入雪堆裡而動彈不得,甚至因為過度疲累,一邊走著一邊睡覺,直到重重地撞上垃圾箱,才猛然地驚醒起來。」
正如上述,小林多喜二作為一名無產階級作家,平時很注重寫作材料的蒐集,擅長運用寫實主義的技法,《蟹工船》和《在外地主》(1929)兩部小說,就是這種條件下寫就出來的。必須指出,《在外地主》是根據《防雪林》為底本改寫,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方面,做了大幅修改。這部作品取材自磯野農場租佃戶與地主之間的抗爭。為了寫作這部小說,他曾經以外出調查的名義溜班,到附近的茶館寫作。那家茶館白天客人很少,他一坐下來,旋即埋頭寫上幾個小時。9月11日晚上,他完成《在外地主》初稿,經過修改和謄寫,於9月29日,將稿子寄給《中央公論》雜誌的編輯,並附上一信,寫明自己的創作意圖。出於他的寫作習慣,他將《蟹工船》寄給了評論家藏原惟人時,同樣附上信文說明,頗有強調其作品的戰鬥意志:他跟平林泰子和黑島傳治同為無產階級作家,但是他比他們描寫封建的或過渡時期的農村景象更具尖銳的批判。同年,他與初戀情人田口瀧子重逢,最後仍然無疾而終。11月,他投身工農運動的行動曝光,而遭到拓殖銀行的解雇。這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如同宣告其寫作和激進的革命之路,將從嚴寒北國轉向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東京。
餘溫能否繼續灼人
第三期就是1930年3月小林多喜二從小樽來到東京之後,受到日共作家藏原惟人倡導的「納普作家的新任務——共產主義藝術」的啟迪,更加確定了創作方向的時期。此時,小林多喜二主張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面投身於大眾革命運動,一面以文學作為武器,目的要喚醒在他認為需要被拯救的無產階級群眾們。這一時期主要作品:〈工廠黨支部〉(1930)、〈組織者〉、〈牢房〉等等。
但就在此時,刑求拷問的陰影終於降臨在他的面前了。同年,他參與《戰旗》防衛關西巡回演講,被依涉嫌金援日本共產黨的罪名遭到逮捕和拷問。其後,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以「不敬罪」被起訴,關押在豐多摩監獄。他關在獨居房,因各種條件限制,只能閱讀經濟方面的書籍和外國文學名著。例如,他讀了大內兵衛的《財政學大綱》和《經濟學》;在文學方面,他讀過托爾斯泰的《復活》、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群魔》、巴爾扎克的《鄉下醫生》、《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以及法國作家《菲利浦全集》、狄更斯的《雙城記》等。那時候,儘管他身在牢獄中仍然透過管道發表了中篇小說《工廠細胞》。
翌年1月,小林多喜二保釋出獄了,他的弟弟三吾和齋藤次郎以及女作家壺井榮等人,在監獄大門口迎接他。其後,他擔任作家同盟的書記長,正式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發表了黨性明顯的小說《組織者》,並在《都新聞》上連載長篇小說《新女性的氣質》(後來改名為《安子》),奇怪的是,這部小說只寫了上篇,再也沒有繼續寫下去。9月,他閱讀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之後,深受啟發感動,進而開始創作長篇小說《轉折時期的人們》,於《納普》刊物上連載,不過,這部小說仍然沒有寫完。文學評論家江口渙在〈小林多喜二的生平和業績〉一文中指出:「因為小林多喜二組織活動繁忙,不能把全部精神貫注在這部作品裡,又由於他遭到虐殺(指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捕後於築地警局遭到刑求致死的事件),使他精心之作終於未能完成。後來從其祕密住處的皮箱裡發現了30枚左右的殘稿,這真是令人痛心至極的事情!」
或許小林多喜二很早就預知到,投身於反政府的革命活動(自己又坐過牢獄),隨時死亡不足為怪,1931年11月初,他特地前往奈良拜訪他仰慕的白樺派小說家——志賀直哉。那次探訪給志賀直哉留下極佳的印象:「……我感到他為人誠實,使我改變了自己過去對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成見。」由此可見,這場如師徒般的對談所散發的融洽氣氛。1932年,日本政府正加緊對無產階級社會運動的壓制,這個措施使得宮本顯治與小林多喜二等共黨人士,紛紛轉入地下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小林多喜二沒有中斷小說創作,完成短篇小說〈失業貨車〉和中篇小說《沼尾村》,其後,又完成了《為黨生活的人》這部小說。只不過,這部作品意識形態過於尖銳,直接刊出可能遭致查禁,所以題名改為《轉換時代》以避其鋒頭。這部小說正是小林多喜二陣營裡極力推崇的作品,他們將它視為其無產階級文學的史詩,亦是日共人士心目中的墓誌銘。

然而,這終究是來自同溫層的讚頌,二戰以後,日本評論界對於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展開了以「政治與文學」的論戰。平野謙就批評道:「這是共產黨人的樣板文章,一種僵化的『制度』;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壓倒一切的技法。直言之,多喜二的文學過於標舉『政治主張』,反而失去應有的文學性……」而平野謙的主要論敵中野重治則撰文回應,論者應當全面考量小林多喜二所處的境況,不應忽略其作品為無產階級文學做出的貢獻……。的確,這場論戰風暴已經消隱在歷史深處多年了,但換個角度來看,正因為我們作為論戰風暴之外的讀者,反而多了些清醒的目光來看待他的作品。在《防雪林》中,我們讀到貧農們在北國酷寒的大地上掙扎求存的生命姿態,不由得份外感動起來。在《為黨生活的人》裡,主人公為失業勞工們奔走轉下地下活動,其最後突顯共黨青年的政治修辭,卻令人不予苟同。儘管不久前,電影版《蟹工船》成功喚醒人們對於日本失業問題的關注,贏得許多支持的聲音。畢竟,文學應該歸於文學園地,因為當共產國家取得政權,開始追逐經濟利益趁機淘空國家資產的同時,工農兵文學就得被掃地出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