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說到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以及翻譯作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武器,我們有必要討論慶應義塾大學英文系教授戶川秋骨(1870-1933)的翻譯論,以及《賣文社》堺利彥(1871—1933)與幸德秋水(1871-1911)這兩個獨特的異端者,因為他們有足夠激進的思想,擅長於戰鬥性的檄文,並透過極佳文筆的思想渲染,使之形成一種試圖撬動社會內部的力量,強烈地吸納更多的讀者參與實現自身設定的政治目標,儘管他們對語詞和翻譯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具體而言,他們對於自己有何本領知之甚深,又非常了解自身當下的戰鬥位置,因而能夠在詭譎多變的時代中,開啟一片奇異的天地來。

堺利彥與思想覺醒
1889年初春,堺利彥前往東京遊學失敗(他1889年夏至1895年住在大阪),回到故鄉,僅僅帶了一冊尾崎紅葉的小說《兩個比丘尼》。然而,這個遊歷與機遇,對於他日後思考和解決「言文一致」的問題,成為其文體改革的驅動力。他於自傳中坦承,在他尚未接觸社會主義期間,其文體受到硯友社的文言文風格的很大影響。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這種主流的影響是絕對性的,幾乎只有追隨而無可抵抗。硯友社是日本近代第一個文學團體,1885年由山田美妙、尾崎紅葉、石橋思案等以鑽研文學為目的於東京所創建。其後成員還有巖谷小波、川上眉山、永井荷風、廣津柳浪、泉鏡花、德田秋聲等,出版同仁雜誌《我樂多文庫》。
1888年,山田美妙退出硯友社,其後成員曾達二百餘名,仍然是文學界的主要力量。他們採取寫實主義寫法,最初大多模仿井原西鶴的寫作風格描繪市井瑣事具有江戶戲作文學的色彩,後來發展為「觀念小說」和「深刻小說」。硯友社的貢獻很大,它促進文學的大眾化,又為自然主義運動奠定基礎。不過,1903年10月伴隨尾崎紅葉的去世,這個團體亦告解散。
堺利彥嶄露頭角的時刻。當時,堺利彥在同仁刊物《浪華文學會》上發表小說、評論、隨筆等,使用的是硯友社風格的文言體,直到1889年進入《万朝報》為止,他的大多數文章都以這種文體寫作。儘管在此期間,他在兒童刊物《少年世界》(1895年1月創刊)上發表口語體的文章,但那只是例外。他在1900年下半年以後,才真正開始以言文一致體寫作,他的日記裡還保留這些痕跡。
事實上,這個時間點頗具代表性,因為此時他出版了《言文一致普通文》一書,這是一本寫作指南,目的在於幫助讀者掌握該文體寫作的竅門。這本書寫道:「在此20世紀第一年(即明治34年),若問日本社會所面臨機遇中最大之改良事業為何?必先回答『言文一致』吧。」在堺利彥的言語觀看來,所謂「言文一致」旨在將口語和書面統一起來,而未必是要將書面語歸向口語。換言之,它是要讓書面語向口語靠攏、口語向書面語趨近,藉由雙方互相靠攏而變得一致。進言之,「言文一致」有幾重概念:不只是將說話的語言移植到書寫的語言中,而是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整齊完備的語言」,用這種語言寫成「言文一致」的文章,可以原封不動作為演說講稿,同時不需修改作成演講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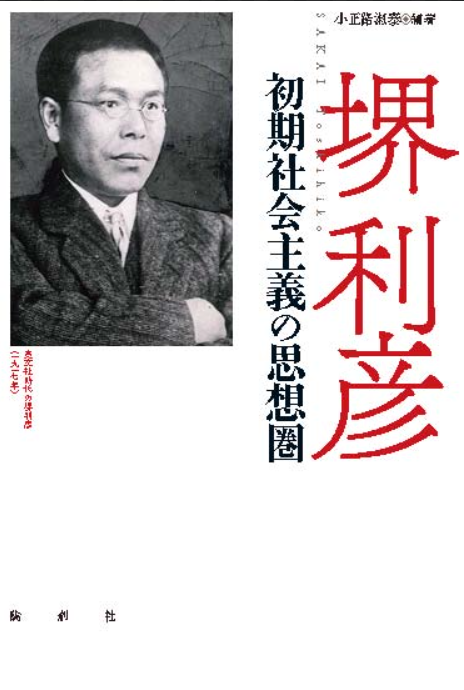
對言文一致的辯證
從這裡可以看出,堺利彥對這「整齊完備的語言」的追求過程,漸漸展現出超越名師(自創品牌)的決心來。1901年8月,他一反謙恭的態度,發表了〈言文一致事業與小說家〉一文,嚴厲批判了尾崎紅葉的文體。他認為尾崎紅葉及其文學派別在遣詞用字方面,「賣弄怪異的漢字漢語,還具體列舉出29個尾崎紅葉筆下常見的「流弊(病句)」。
接著,在這篇文章中,堺利彥對尾崎採用這種文體歸納出幾個原因:一、僅用日語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借用漢語以補其不足。二、頻繁借用假名難以閱讀。三、耳朵不容易辨別漢字的讀音,還必須讓讀者的視覺感受到,若用假名就無趣味可言。四、如果選用日語和漢語完全相同的字詞,聽覺和視覺就會協調起來,並產生一種特殊的美感。五、如果選用日語和漢語(或者漢字)中發音相似、意思相同的詞語加以並列,會產生謎語般的趣味性。六、一般人只看假名,有學問者可以同時並讀假名和漢字,這樣就可以讓人們根據自己的閱讀能力感受文章的魅力。七、藉由漢字可以促進人們對東京的方言的了解……。總而言之,在這個階段上,他對尾崎紅葉採取「避而遠之」的態度,如同在宣告一樣,他的文體正棄舊更新。
從實際面來講,日本帝國很早就倡議言文一致的必要性與急迫性。1901年,帝國教育會已經明確指出,「言文一致是與西歐列强相競爭時的語言武器」、「歐洲各國在三百年前從拉丁語的支配中脱離出來,實行了言文一致,因此踏上了文明開化、富國强兵」之路。然而,要實現此一理想,並不能一步到位,它必須克服幾個嚴峻的事實:其一是「言」(各地方言,各個階層的用語)不一致。其二是「文」也不一致,有「和文體、漢文歐文直譯體、方言體、漢文體共四種文體。其三是,究竟是讓「言」與「文」一致,還是「文」與「言」一致亦爭論不休。
同樣的,幸德秋水作為社會主義者的自覺過程中,他與堺利彥一樣,非常積極參與「言文一致」運動之中。1901年,他對當時報紙所用文體的混亂狀況甚為不滿,因而在《新文》雜誌上發表了〈言文一致與報紙〉一文,表示「我等希望全國的報紙改用言文一致體……。鮮有文體多樣雜亂如今日之時代。漢文、和文、洋文直譯體、雅俗共賞體,悉數存在於同一張報紙,非通曉上述所有文體不能卒讀,令人不堪其煩。」
在他看來,如果報紙的版面統一使用「言文一致」體例,即可結束這種混亂的狀況,而且讀者會「成倍」增長,社會效益也會「成倍」增加,並給報紙(報社)本身帶來巨大利益。確切地說,他強烈主張「實行主動、及時、迅速採用言文一致的方針」。由此可見,後來因「大逆事件」被判死刑的幸德秋水與其直接行動論思想的緊密連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方法
再舉一例。1903年,幸德秋水《社會主義神髓》一書出版,立即引起了社會評論家的關注。他在該書第二章「貧困的原因」指出,英美兩國的產業甚為進步與興盛,為世界各國所讚美和羨慕,但他們財富分配的情況卻令人為之鼻酸。兩個的貧民依靠救濟金生活的高達百萬人之多。他進而說道,這種情況並不限於英美兩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也是如此,因為大部分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似乎成了世界各國的共同趨勢,日本也概莫能外。在歐洲,以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表達社會主義,也許是作為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動而產生的最重要的抗議運動。更直白地說,他要抨擊的是,少數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將沒有生產資料的平民百姓推向了飢寒交迫的境地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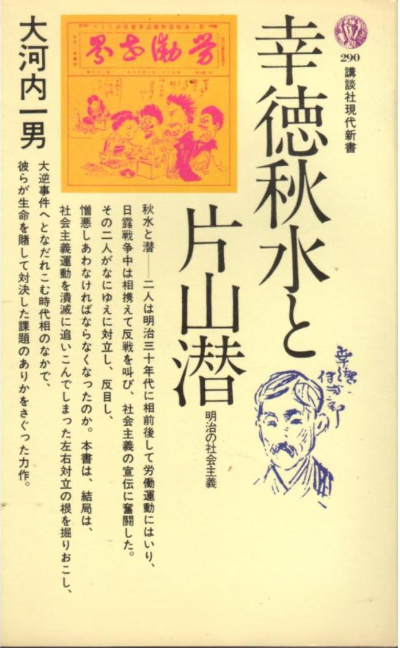
這種充滿正義感為貧窮者伸出援手的言辭有著不可估量的渲染力。一個評論者寫道:「幸德秋水乃能文之士,社會主義之熱心家,於一代人中享有盛名,此書乃其就熟悉之題目、以自由之筆墨揮灑而成,其價值自不待言。」小笠原譽至夫的書評:「幸德秋水近日著《社會主義神髓》一書,文筆雄健,結構規整,而且敘學簡明、闡釋透徹,誠乃爾來之佳作。」(《評論之評論》第59號,1903年7月20日)
在此,需要突顯的是,幸德秋水的非戰論和直接行論立場,一直是歷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1903年11月,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為了貫徹非戰(反對日俄開戰)的立場,辭去《万朝報》工作,同共組成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宗旨的「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周刊。當時,日本國內反俄的聲浪高漲,日俄兩國戰爭一觸即發。然而,万朝報社傾向於主戰論,他們又無法改變其立場,只能掛冠而去。兩年前,他出版《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一書,就是反映其非戰思想的代表作。在這本書中,他從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出發,極力說明軍國主義和戰爭帶來的災難:「好戰之心是動物的天性,軍國主義不利於社會文明的進步,而且嚴重殘害文明甚深。」
在《平民新聞》明治37年(1904年8月21日)上,幸德秋水〈社會黨的戰爭觀〉一文,這樣寫道:「戰爭永遠是為政治家和資本家的利益而戰的;領土和市場總是為政治家和資本家而開拓的。而戰爭給多數國民、工人和窮人帶來的卻是災難。……他們對幾百萬同胞流離失所、飢渴凍餓視若無睹,只管拚命向海外擴張領土市場,立刻造成了各國經濟的動蕩。這群愛國者的所謂「帝國主義」政策,其實質就如此。」
必須說,我們現今讀到這篇近110年前的文章,對照著2022年2月24日由普丁發動的併吞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同樣能感受到強烈的恐懼感和壓迫感,因為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不管以任何名義發動侵略戰爭,他們都已犯下不公不義和反人類的罪行。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斷言,我們同意激進的社會改革者以嶄新的文體來改造國民思想的作為,但絕不容許假冒神聖之名卻作惡禍國殃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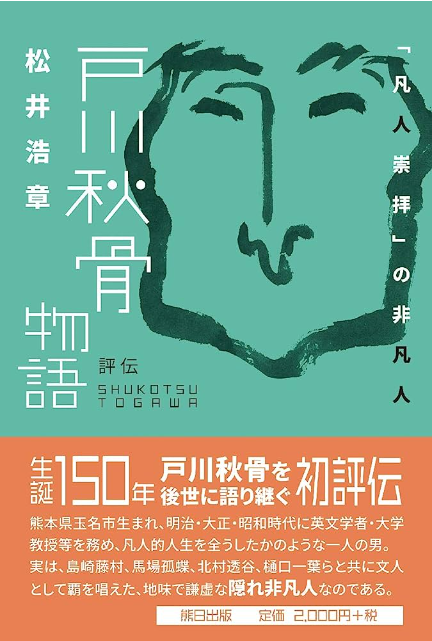
戶川秋骨的翻譯觀點
乍看去,上述開篇處提及戶川秋骨的翻譯論,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但他的見解是否站得住腳不相互矛盾,仍然需要透過其教學生涯及其文章來佐證。他是小說家島崎藤村和馬場孤蝶的同學,1893年參與《文學界》創刊,並在此刊物介紹和評論外國文學。此外,他曾經與平田禿木合譯《愛默生全集》(1916-1925)、隨筆文集《英文學雜記簿》(1926)、《能樂禮讚》(1930)、《都市情景》(1933)、《自畫像》(1935)等等,可謂著述翻譯豐富。在這些論述當中,以〈翻譯製造株式會社〉(1927)一文,最能突顯其翻譯者的立場。他帶有貶義的批評:大體而言,翻譯公司生產的翻譯文件都存在問題和瑕疵。
例如,譯文艱澀難懂、語意模糊不清,但只要稍為加以潤飾,它們最後總能過關的。在他們看來,所謂「翻譯不忠實原文」、「違背作者原意」等都是無稽之談,而且不需對此顧慮,過多顧及不但無益反而有害阻礙文化的普及。戶川進而提到,以前從事翻譯的是貧困文人或教師的副業,現在被大資本家改變成大量生產了。然而,這種大量生產模式的翻譯不僅給資本家和文人帶來好處,也使世界的偉大思想、文藝以其低廉的價格廣傳世界,對文化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貢獻。接著,戶川借用莎士比亞「天授恩惠總是具有正反兩面」的說法,以諷刺「快速翻譯」的現象,那時新聞報刊除了賣藥的廣告之外,幾乎都是翻譯社的廣告,無疑這給報刊帶來了收益。
戶川秋骨進而援引了翻譯在歷史中的作用。他說,英國伊莉莎白王朝時期引進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思潮,德國在感嘆模仿法國之際,日本已敞開胸襟積極地接受引進外國文學了。那些被稱為「一圓書」備受世人歡迎的大半都是翻譯文學。什麼世界文學、世界大文學、近代戲劇、近代某某……幾乎全是翻譯過來的,有些書籍沒有標注翻譯,但其內容多半翻譯或改編改寫,換句話說,翻譯外國語文根本不必高談闊論,因為所謂文藝作品原本即是商品。
然而,他從翻譯局限論的角度來看,隨著翻譯作品大量湧入,確實給日本文化在接受與轉化的過程中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外國成語或慣用語句屬於說明性質,文體也不是感性的,而是具有高度的理性,但在日本語中往往找不到相應的詞語。基於這眼見為憑的弊端,他的反對立場得到了強化,甚至嚴厲批評當時頗受好評的新潮社,說他們出版的翻譯作品都是粗製濫造,他才不相信這些鬼話。在他的隨興翻譯論看來,譯者進行翻譯之際,不需拘泥於原文可隨意翻譯,原文為左也可以翻譯成右,無需顧忌太多,文章情節不通,按自己的想法翻譯,因為讀者們只能被動接受。此外,他指出逐句翻譯(所謂的硬譯)的弊病,這種一字一句都不忽略,完全照搬原文語序,沒有轉化為日文語序的翻譯,自然造成語意的模糊,讓讀者們無法理解,恐怕譯者對原文也一知半解。
有趣的是,戶川秋骨措辭尖銳地指出當時翻譯的亂象,儘管他讚許將日本文學翻譯到西方的做法,對外國人翻譯卓越的日本文學也沒有異議,但他反對日本人自行翻譯本國作品輸往西方為此還沾沾自喜,在他看來,這不但滑稽而且是自我羞辱。具體而言,他持這觀點旨在表明優質的譯文必須由掌握母語的譯者來實現的。
在該文最後,他又對(當時)劣品橫生的日本翻譯界,毫不猶豫地施予重擊:日本所有的東西都是翻譯來的,放諸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這種(以譯代寫)的國家了。正因如此,才會冒出這麼多翻譯製造公司來。所以,翻譯這種東西極不可靠,希望日本國民不要閱讀翻譯的作品。有人依靠翻譯作品來解釋歐洲文學,那必然帶來許多錯謬的看法。如果做不出好的翻譯作品,他寧願主張翻譯有害論,與其吸收訛誤甚多的外譯書籍,不如多讀些優質的日本作品受益更多。
幸德秋水與翻譯的苦心
相較於大學英文系教授戶川秋骨的不可翻譯論,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看待翻譯方面比前者更具有策略性。他們的做法是,同樣透過外國語文轉化為日本語,它除了傳輸文化意義之外,其實還能把它武器化,也就是,把翻譯當成一種武器和強大的媒介用來宣揚自己的信仰主張,不致於淪為按字計酬的平凡譯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在這方面都是佼佼者,而且留下具體的業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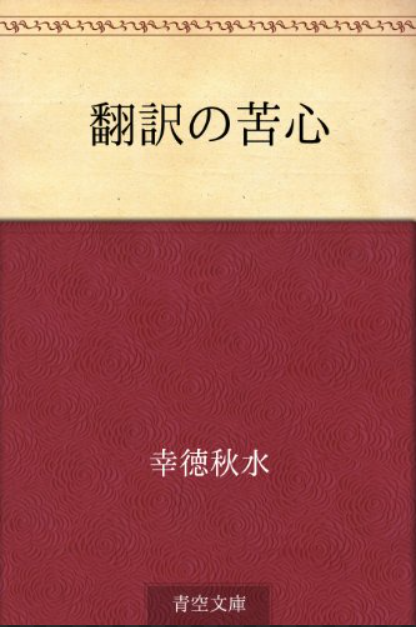
幸德秋水在〈翻譯的苦心〉一文指出:就文章寫作而言,翻譯比寫文章困難得多,稍有責任感的譯者,對原作者和讀者所耗費的苦心非同尋常。翻譯首先必須明確理解原文的意思,這是非常困難的一項工作。因此,即使非常有學問的學者,也會遇到吃不透原文的挫折。儘管通讀的時候自視可以理解的文章,一旦逐字逐句翻譯,仍會遇見語義含混而無法翻譯。事實上,以逐字逐句毫無錯誤地翻譯大型書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儘管如此,譯者不能把這個當成錯譯的理由,而應當盡力不出現謬誤。有時候,我們看似理解原文,可以像對待本國文字似的咀嚼,但一下筆就會遇到詞不達意的窘境,找不出與之相應的詞語,這份苦心與古詩人(尋章摘句似的)思索推敲並沒有不同。嘴硬不想認輸的人把它怪罪為這是日本語和漢字缺乏合適的對應詞所致。
針對這個問題,幸德秋水援引他的啟蒙老師中江兆民的觀點,其實譯文受阻並非缺乏詞彙,如果譯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們就能夠翻譯自如又可作為有力的武器。接著,他提及翻譯過幾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弄得焦頭爛額。在此數年前,他與堺利彥合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1904)時,因譯文佶屈聱牙譬而羞愧萬分(出版後旋即遭到查禁)。譬如,那時經常出現「資產階級」一詞,他就無法將社會主義理論中所謂資產階級概念完全表達出來,經過反覆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將它翻譯成「紳士閥」。實際上,所謂的「紳士」並非英文「gentleman」所指的風采奕奕的紳士。在日語中所謂的「紳士」老爺,相對於勞動者即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
此外,還包括階級(由經濟作用而產生的個人身分)自覺性、平民或勞動者(後來譯為無產階級)、剝削等具有特殊含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範疇用詞,都必須分別創造對譯詞來。幸好,如明治初年的箕作麟祥、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文化奠基者,煞費苦心創造了許多翻譯用語(如權利、義務、歷史、哲學、物理化學、醫學)等等。
在他看來,完美的翻譯不僅需要傳遞文章的思想,還必須仿傚原作的風格,如果原文輕快就必須輕鬆活潑,流暢的地方就需要行文通暢,雅健的地方必須典雅剛健,滑稽之處還得詼諧幽默。確切而言,他反對按照原文逐字逐句翻譯,這樣將造成譯文阻滯喪失活力,必要的時候,甚至要調動語序和倒置前後。
在西方翻譯理論中,有翻譯即背叛的說法,但是他認為,譯文出現晦澀不通或任意扭曲原文的意思,才是對原作真正的背叛。正如前述,幸德秋水極為敬慕中江兆民的思想與譯筆(他23歲時在其門下《自由新聞》擔任翻譯,翻譯路透社每月的電報新聞),因而他將中江兆民的理想翻譯付諸行動,也就是說,要將原文翻譯得極好,必須具備比原作者更好的文筆,不僅不留下斧鑿的痕跡,同時又需忠於原文。他引述中江的翻譯觀點,如果對原文的理解不夠透徹,只能說明譯者學而不精能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他都會在書上留下記號,絕對不會隨意處置。這是翻譯家應盡的義務,亦是當時賣弄筆墨的才子們無法達到的境界。
幸德秋水表示,他每次翻譯都會將原文反覆閱讀數十次,以加深對原著的理解,因此自己的閱讀能力迅速提高,有益於俢煉文章的寫作。不過,他從對社會公益的角度來看,為了普及文藝、學術和政治經濟及其他各種世界知識,當務之急即翻譯更多的書籍,而高水準的翻譯家,也是當今時勢所需要的。進言之,在思想混沌不清的年代,試圖改造社會差序並引領思潮的激進者,他們無時無刻都在尋思將語言和翻譯作為一種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