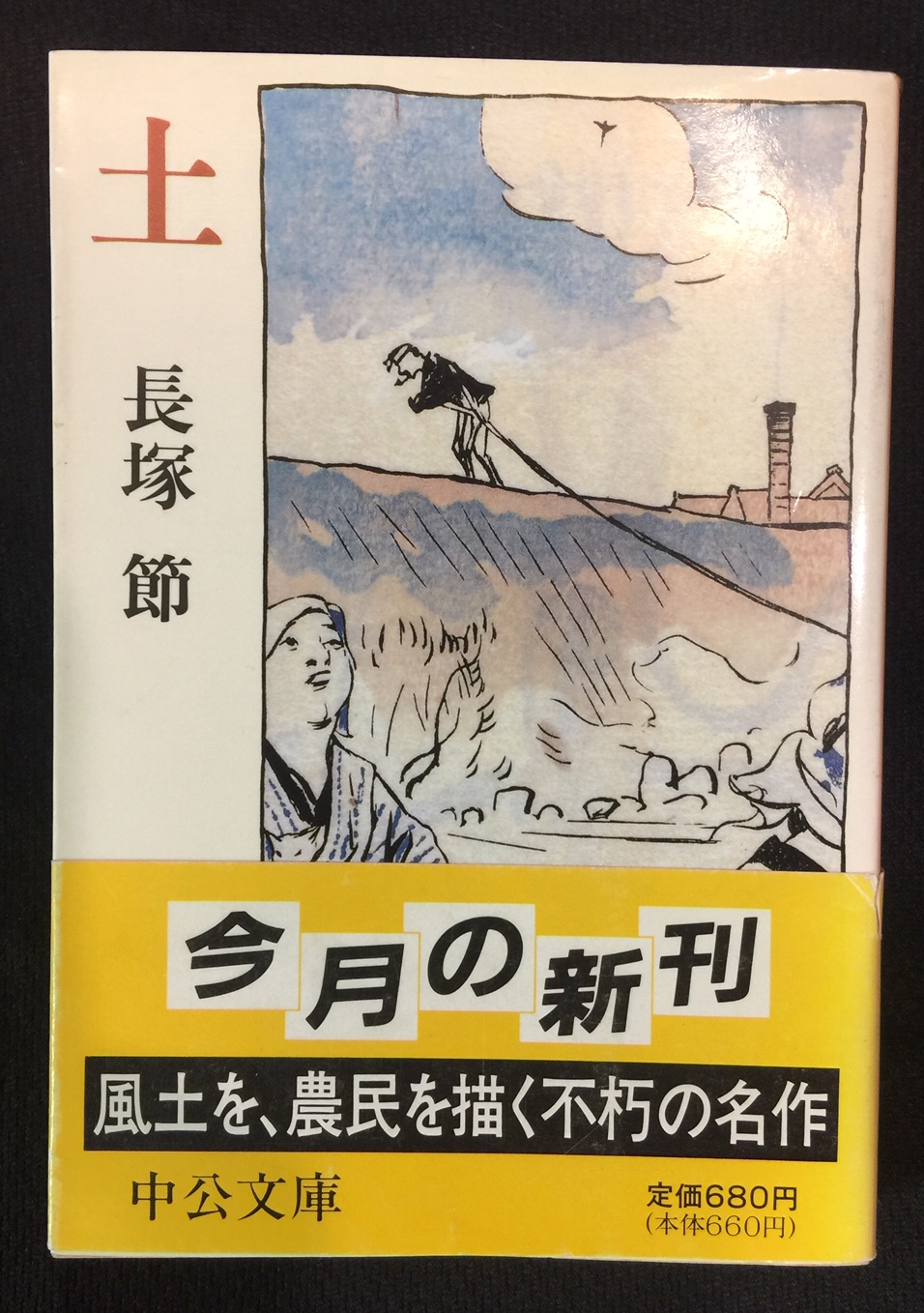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總括而言,在日本農民文學的譜系中,尤其在小說反映近代史現實方面,黑島傳治(1898-1943)的存在可謂相當突出。他的作品核心訴求明確,大多描寫故鄉貧苦農民的生活磨難,以及他們被地主欺凌壓榨最後掉進人財兩失的困局裡。這種寫作風格似乎比同時代作家更早呼應了卡夫卡(1883-1924)小說中的荒謬性。

必須指出,自日俄戰爭(1904-1905)以後,日本產生了許多戰爭文學,在那以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1918)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黑島傳治並沒有缺席,並以親歷者的視角寫出了日本兵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的死與生。他以蘸滿感情的筆觸描繪屍骨殘破的日本士兵——〈盤旋的鴉群〉,挖掘他們與死亡交會的恐怖體驗——〈風雪西伯利亞〉,而這些如戰場日記般的紀錄,經由他的小說妙筆提煉為擲地有聲的反戰小說。要言之,讀者若透過黑島傳治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兼容的現實主義小說,都能某種程度掌握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變遷的概貌。
小說家的人生履歷
黑島傳治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啟蒙很獨特。他出生於香川縣小豆島(現內海町)苗羽村一個自耕農家庭。父親兼吉依靠種田、捕魚和打零工維持生計。1911年,他入內海町實業補習學校,1914年畢業後進入醬油工廠,當了一年左右的釀造工人。
1917年秋天,他前往東京闖蕩,任職於三河島建築公司,上班期間已開始練習寫作小說。這段時間他開始接觸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人的作品,1919年在早稻田文學社文學講座上,結識了同鄉作家壺井繁治並成為至交。同年,辭去建築公司的工作,進入曉聲社《養雞之友》編輯部。是年春天,經由壺井繁治的推薦,他花錢雇人代考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注: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也是雇人代考,可參閱《大杉榮自敘傳——「母の憶い出」》進入順天中學就讀)。
他於該年年底被徵兵入伍,當時,正值日本帝國出兵干涉俄國十月革命之際,1921年,他跟隨部隊從福井的敦賀港乘輪船前往了戰地西伯利亞。不料,他原本就身體不佳,踏入嚴寒的異國土地,沒多久,就染上了肺病,翌年免除兵役(注:二戰期間三島由紀夫因肺部浸潤而免除兵役)被遣送回國,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返回家鄉以後,他並沒有因此荒廢,一面養病一面創作。1926年,他先後在無產階級雜誌《文藝戰線》上發表著名短篇小說〈兩分硬幣〉(1925)和〈豬群〉(1926),並成該雜誌的同仁。
順便一提,日治時期台灣屏東縣作家楊華的作品與黑島傳治有相似之處。楊華於1927年2月5日,因涉嫌違反《治安維持法》屢次被傳喚和拘捕,其短篇小說〈一個勞動者之死〉(《台灣文藝》1935年2月1日)、〈薄命〉(《台灣文藝》1935年8月4日)同樣勇於為底層人物發出不平之聲。
翌年6月,全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分裂,黑島傳治選擇投入工農藝術家聯盟。然而,同溫層的文學團體成員們自主意識極強,相處起來並非一派和睦,同年11月,該聯盟閙內訌再次分裂了。不過,面對這種必然的內部喧囂,他始終堅持「文藝戰線」派的立場,仍舊保持著旺盛的戰門力。
在暴風雪中見證人性

在短篇小說〈風雪西伯利亞〉開篇處,作者即道出日本士兵的苦悶處境:「送走了回國的同年兵(注:士兵在入伍時稱一年兵,第二年新兵入伍時升為二年兵。老兵有絕對的權力欺壓新兵,可以任意毆打辱罵),他們從車站回來,便躺在營房裡的床上,好長一陣子,一言不發,只是嘆氣,因為他們得熬上一年,才能回國。回想起一年來在西伯利亞的生活,是多麼無聊而漫長。他們當上二年兵,在衛戍醫院做了不久,就被派到西伯利亞來。當時,一起從敦賀港乘輪船來的同年兵有一百多人。到了西伯利亞,原本駐紮在這裡的四年兵和一部分三年兵,就回國了。
西伯利亞被雪覆蓋著,一眼望不到邊際。河水結了冰,馬兒拖著雪橇在上面駛行。為了防止滑倒,他們穿著靴內釘上絨毡的棉靴和皮大衣,戴著皮帽,朝著野外進發。白嘴的烏鴉群集在雪原上,啄個不停。化雪以後,到處顯露出非常單調的荒野。馬群和牛群開始嘶鳴呻吟著到處徘徊。不久,路旁的枯草吐出嫩芽,遠處的原野和近處的山丘,也都緊跟著生出一片片青草。不到一個星期的光景,原本是荒涼的原野,變成綠洲、草長、樹長出新枝了,鵝鴨到處開始春遊。夏天,他們和步兵一起轉移到中俄邊境的地方,十月和紅軍之間發生了遭遇戰。之後,他們便乘著裝甲列車撤離了第一線。
小說故事進入了重點所在。待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士兵,遲遲看不到返國的希望,心理受到了重挫,滿腔烈火噴油似的,必須找到發洩的出口。一個姓屋島的士兵,就是那種極端的人。他膽子很大酷嗜砍殺,平是總是揮動刺刀,刺殺俄國人,找不到對手的時候,就刺殺徘徊在原野上的牛和豬取樂。在他看來,回到日本可不能這樣撒野了,得趁此機會在沒有法律管轄的西伯利亞盡情享點樂趣。屋島經常頂撞軍醫和護士長,不服從上級命令,有一次,他惱羞成怒發飆起來,竟然拿著手槍把軍醫追得到處逃竄,混亂之中還開了一槍。
幸好,他沒有瞄準對象,子彈只射穿了一面雙層玻璃窗。事實上,屋島這種暴行是有目的性的,因為他試圖以這種暴力方式,逼使害怕挨子彈的長官盡早將他列入歸國的名單。相反,老實聽話盡忠職守的吉田和小村卻得不到好處,他們必須在西伯利亞再待上一年,與那些出沒無常的俄國游擊隊作戰。因此,他們覺得似乎受了欺騙,很想發洩胸中的怒火。某日,在等載運歸國士兵的火車進站時,屋島取笑他們簡直是個傻瓜,想早點回國就得像他一樣使壞。他們倆聽到這些話,心情更加沮喪了。火車一進站,回國的士兵們提著裝滿珍奇土產的背包,爭先恐後地擠上火車去,占好了座位,脫掉皮帽,將臉湊近車窗。那些士兵們在車窗裡笑嘻嘻向他們說著什麼。他們倆原本想用微笑來回答他們,但不知怎的,臉上的肌肉卻痙攣起來,一副欲哭無淚的模樣。
為了排遣鬱悶的情緒,吉田向小村提議到附近的山丘打獵兔子,視力較佳的吉田說,他經常看見兔子一下子悄悄地從草叢中跑出來,馬上又消逝在白雪中,片刻又從別的地方悄悄出現。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兔子的長耳朵,但牠與白雪同一個顏色,不仔細看,就看不清。吉田自豪地說,他在國內時經常去獵鹿,很會操作獵槍,端起槍來馬上就能射擊,而且是百發百中。當他這麼說時,隨即開了一槍,只見一隻兔子竄起五六尺高,在空中劃了一道孤線向前方跳了過去。
吉田向身後的小村遞了個眼色,便向前奔去。那隻兔子的內臟都被打了出來,鮮血染紅了雪地,牠像似是一具死嬰。這種可怕的狩獵來得太容易,因而助長了吉田的衝動與氣焰。上等兵護士長看他們不值勤,卻熱中於打獵,就叮嚀他們不要亂跑,因為俄國的游擊隊經常在這一帶祕密活動,有潛在的危險性。
然而,這番提醒他們並不領情。雪原上的獵物越來越少了,有時候大半天,只能打到一隻兔子。每在這樣的時候,兩人為了發洩怨氣,便在歸途的山上,將剩餘的子彈盲目地對著天空亂放。那天,他們鑽過聯隊架設的鐵絲網,走下了峽谷。峽谷間是沼澤地帶,浮著一層薄冰,沼澤對面有二三間民房,它們埋在深雪中,小村看到這幾間詭異的民房,頓時覺得有點駭然,於是,催促著吉田就此止步不可前進。問題是,他們好不容易才打中了一隻兔子,正要提著血淋淋的獵物走下山時,不遠處出現了一個穿著毛皮大衣,滿臉棕色鬍鬚手上提著槍的俄國人,一直盯著他們。
這時候,小村嚇得兩腿發軟連站立都倍感困難。吉田也神色慌張很想逃出去,卻見一群俄國人把他們包圍起來,一步一步逼近。吉田端起槍朝俄國人開了一槍,由於太過緊張,持槍的手還在發抖,射了十發子彈全沒打中。霎時,他們被幾名身強力壯的俄國年輕人給壓制在地。一個強壯的老人閃爍著逼人的目光,執拗地用俄語逼問吉田和小村二人,彷彿要他們交待什麼情況。他們都不懂俄語。
不過,從老人的目光和動作看得出他懷疑他們二人是來偵察情況的,並想從他們口中得知鎮上現在駐紮著多少日本兵。從老人的神情看來,他似乎在提防日本兵立刻會從山上攻下來。不無諷刺的是,吉田重複地說,自己實在不知情,幾乎哀求的口吻,那帶頭的老人及青年們,開始把他們身上的防寒大衣、軍服、襯衣、褲子、皮靴和襪子等剝扯下來。他們就這樣赤裸裸地站在雪地上,並意識到死期已在面前。吉田心想,那幫俄國人一定會把他們打死的,頓時想起聽來的一句俄語:「救命!」。
不過,他的發音不正確,將「救命」說成了「謝謝!」。俄國人似乎並不想可憐他們,兩個小伙子走到稍遠的地方,把手中的槍舉起來。剛才,老實安分地站在雪地上的吉田立刻往前奔去,接著小村也跟在後面向前奔跑,用力喊著「救命!救命!救命!」但他們的發音,在俄國人聽來卻是「謝謝!謝謝!謝謝!」沒多久,峽谷裡傳來了兩聲槍響。
俄國老人把從他們身上剝下來的防寒大衣、軍服和皮靴捆起來,朝埋在深雪的民房走去。第三天,吉田所屬的聯隊動員兩個中隊的官兵,搜尋這二人的行蹤,當官兵們找到他們時,屍體已經凍僵,只是膚色還跟活著時一樣,僅僅在背上有一處小指粗的傷口而已,臉上似乎還帶著喊叫時的表情,眼睛睜著,不再閃動。上等兵護士長站在被一群士兵圍著的屍首面說,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然而,護士長是否想過倘若讓他們和其他的三年兵一起回國,也就不會發生這類事情了。現在,他正尋思該怎樣製作一份遺失武器和裝備的報告。嚴格說來,黑島傳治在〈風雪西伯利亞〉中,所展現日本士兵死於西伯利亞的暴虐性的和非人的荒誕命運,就是對日本帝國擴張領土和發動戰爭的強烈控訴,而且,那些被徵召至嚴寒之地的日本士兵,更多是來自農村的青年。
在家鄉,他們沒能逃出地主的欺詐,後來,又遇上了戰爭時局,彷彿一開始就注定無法擺脫苦澀命運的輪迴。這時候,為多數農民發聲充當反抗武器的文學小說,不但成為表達人民心聲的重要載體,並吸引前後世代作家與思想家關注這個議題,從文化層面、政治結構、經濟面向和社會變化切入,逐漸豐富了農民文學的底蘊。
農民文學能否承載文化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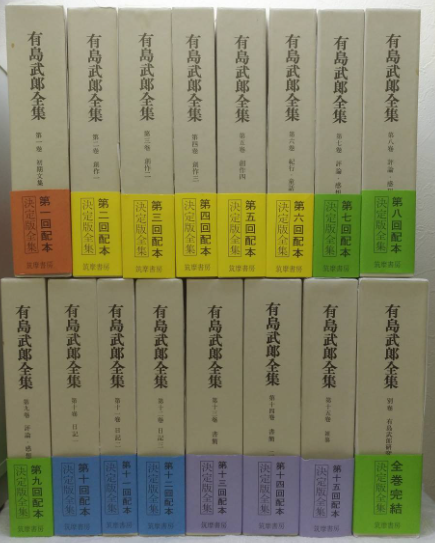
以托爾斯泰為師的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他作為人道主義文學的代表,在北海道擁有大片田地,為了改善農民的生活,自行解放(釋出)農地,提供貧窮的佃農耕種,還創建了共生農園,可謂身體力行的最佳範例。有島武郎在〈所謂農民文化〉(《文化生活的基礎》,1923年6月)一文中,這樣總結他長期以來與農民打交道的感悟:
「我對文化這個詞有一定的懷疑,因為今天所謂的文化,只有極少數人喜歡,對大多數人沒有影響。特別是在談到農民的文化時,我必須說它向來不受關注。在現今,農民所處的悲慘條件下,怎麼會有文化的空間?然而,我說農民沒有文化,並不等於說農民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因為真正的文化必須普及和普遍性,但它卻遭到部分壟斷了。因此,我們有必要傳播真正的文化,儘管這並非一夜之間可完成的任務。我們走得越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越困難,因為走到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當前社會制度和生活的諸種缺陷。本應自然共享的資本(土地)變成了私人所有,這就造成了各種不良影響,因此,應當自然地以人道方式推進的文化,卻呈現出今天這種變態的形式。換言之,如果我們不改變這種制度,即使我們費盡千言萬語,我們終將無法傳播文化。當然,不因應時代的變化來處理農民文化的問題,未免不切實際。」
但應該指出,畢竟有島武郎對共產主義虛擬的烏托邦世界抱有一定的幻想,否則他不會如此斷言:
「第一步就是擺脫這種私有財產制度。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從私有財產制度中解放出來?在我看來,我們必須從機械化的生活中恢復自由,許多學者和實踐者至今為解決這個問題而努力,而我們這些局外人,就更難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了。總而言之,我們必須摧毀今天的私有制體系。我認為,消滅私有制度有兩個方法,漸進式的解放和激進式的革命手段,無論是漸進式還是激進式,自由都不是憑空就能贏得的,而是在把握其主體才能得到。蒙恩受惠的地方沒有自由可言,只有在自己掌握自由的地方,才有真正的自由。激進派很明白這一點,但是在漸進派中有一些人沒有看出來,所以,他們經常採取徒勞無益的政策,如溫情主義和合作主義等等。話說回來,縱使我們採取漸進式的方法也要認識到我們不應強行給予他們自由的覺醒,而是喚醒他們對自由的追求,以他們真正的力量來實現文化或自由。我們只有摧毀了私有制度之後,才能實現人類文化,到那時,我們才能建立真正的農民文化。」
石川三四郎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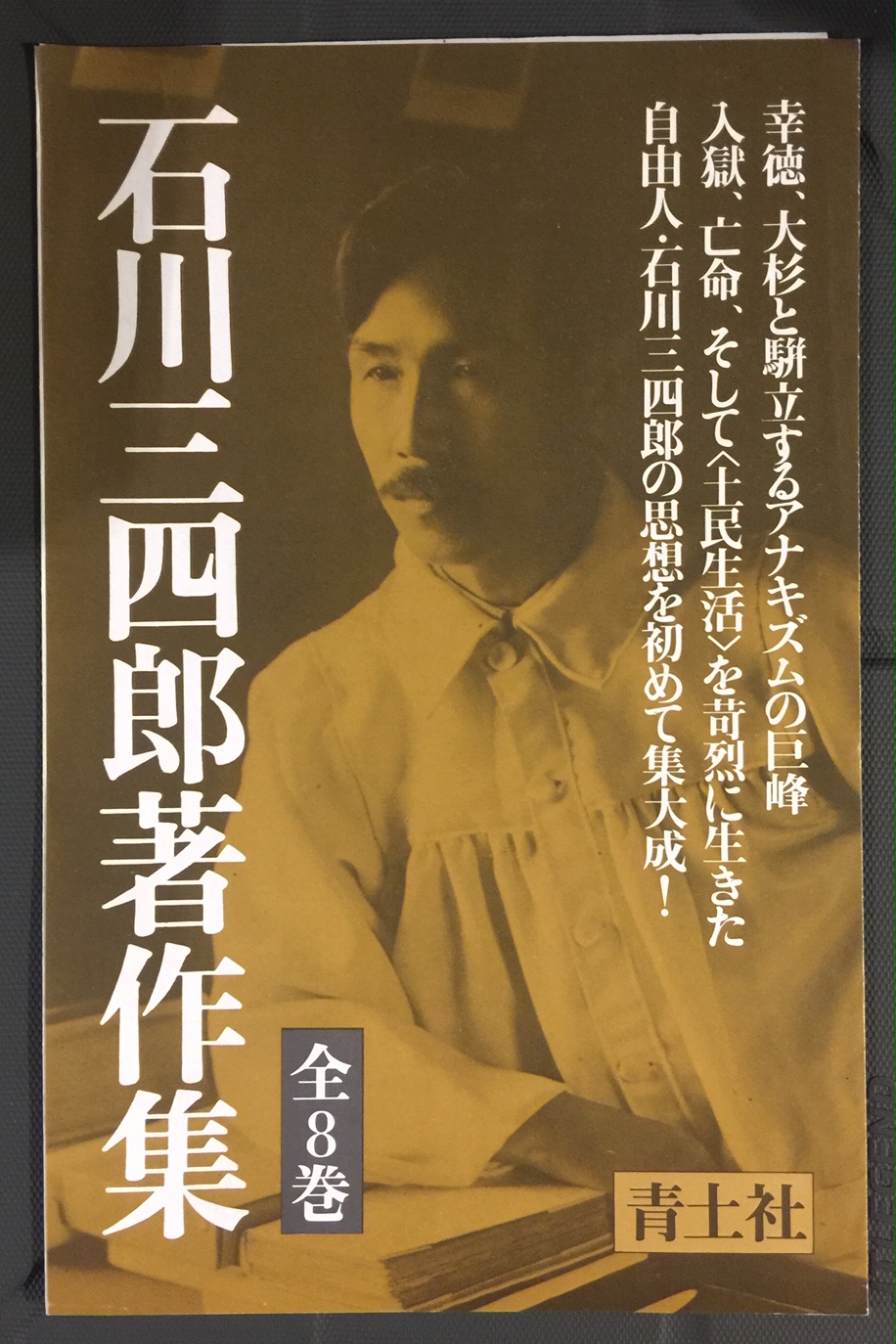
這是文學小說家的觀點。革命家又是怎麼看待?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石川三四郎(1876-1956),他的〈農民自治理論與實踐〉,用口語形態顯露出另一種激進的光芒:
「我要說的不是政治演講,也不是關於勞工運動的講座,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首先,我要談一談農民自治的理論,然後再談其實踐。在理論上,我先說明自治的意義,其次談支配體制和政治制度的荒謬性,第三點,我要說明土地與人類的關係。自治最終是一種本土生活,沒有本土人民就沒有自治制度,而本土人民的生活就是農民自治的生活。在實踐中,為了說明落實這一理論和實踐的步驟,我把我的談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社會方法,第二,個人方法。進化論者強調適者生存的主張,但比起生存競爭法則,我們更應該發揮相互扶助的精神,如同蘋果樹和梨樹一樣。如各位所知,在樹皮下含有一種白色的汁液。如果這種汁液過於活躍,從底部上升到頂部,樹就不會開花。樹身只會越長越大,葉子越來越茂盛。現在,如果你稍微彎曲樹枝,使其枝條伸展,它就會開花結出更多的水果。這是因為光線和汁液取得和諧。這時候,掉落的花朵並不是因為它們在競爭中敗下陣來,而是因為它們與太陽的光線更加和諧而綻放,為後來的結果而犧牲的。它們開花如此之多全是為了調節產量。以在戰爭前線英勇打仗獲得金鵄勳章的人為例,並不是只有他們擔負著國防的任務,在後方履行必要職責的電信隊、運輸員、農民和其他人員,同樣在保家衛國。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只有前線作戰的人才是勇者,而在不為人知中彈身亡的人就不是勇敢的。然而,目前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生存競爭的基礎上,所以,才會出現這種錯誤的思維方式和扭曲的事實。」
石川三四郎進而提到:
「在日俄戰爭時期,我因為某件事情(錦輝館事件)被關進了監獄。那時候,有個獄警對我們這樣說:你們真幸運呀。我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每兩小時只能坐下休息20分鐘。我們若在這時打瞌睡哪怕是片刻,就會被扣薪三天工資。但是你們可以每天看書,太令人羨慕了。儘管他們語帶調侃地說,還是對我們很照顧的。對他們來說,我們就像各種商品一樣,因為法務部長來這裡視察,他們若稍有怠忽職守,就會被懲罰扣減薪資。
有一天,監獄高層下達命令:因戰爭時期,必需撙節開銷,監獄官員們相互協商,但他們無法減少囚犯的伙食,別無選擇之下,只能減少獄警人員,於是,他們從原有150人減少至100人。獄警們在困倦中堅持不懈,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但只有典獄長一人受到了表揚,其他獄警都沒有得到任何獎賞。
事實上,典獄長是一個好人。他曾把我和當時隔壁牢房的大杉(榮)叫來旁邊,非常客氣地說:你們是可敬的人,你們為社會做了先鋒,做出了崇高的犧牲。因此,典獄長受到表揚,我是真心為他高興的,但那些說『我們從未在陽光下讀過報紙』的獄警們卻得不到任何獎賞,又是什麼原因?的確,那些沒有得到獎賞的獄警也是在為國家服務,但在一個以生存競爭為基礎組織的世界裡,只有長官才能得到獎金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說完監獄與囚犯之間的關係,石川三四郎進而提及何謂真正的自治。他說,真正的自治必須與本地人民的生活徹底融合,人類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安納托爾.佛朗士在他一本書中寫道:「人類就像地球表面的一條蛆蟲」。人類是一種出生在地球上的生物,生活在地球上,並被埋葬在地球上。人不僅不能離開地球而生存,而且還在許多方面受到地球的啟發和滋養。當人離開地球(土地)時,真正的美和道德以及經濟就會失去。從地理上講,人們顯然受到他們的環境制約。在體型上山民與平原的人有所不同。山民因為空氣較稀薄胸部較寬,經常行走斜坡,腿型自然較為彎曲個子較矮。而平原上的人則有較長的腿和較高的身材。體型是這樣,自然也會影響他們的精神特質。眾所周知,出生在美麗地方的人,較容易富有詩意成為詩人和畫家。
我昨天晚上已說過,如果你出生在御牧村,那裡可以看到淺間山和烏帽子嶽的壯麗景色,你若成不了一個詩人,一定是毫無才華的人。不過,這並不限於所謂的詩歌寫作,在當今的社會中,這個願望已越來越難實現了,因為無論你出生的自然環境有多美,你都必須離鄉背井到城市和工廠工作才能維持生計。有些人就算無此需要也要去城市賺錢,或者與城市人合夥做生意。可想而知,大家越來越背離美的生活。以前的詩人曾經歌頌田園風光的農村所在,現在卻越來越難找到詩意遍在的地方了。從這般抒情式的概括,可以讀出主張行動改造社會的石川三四郎,在面對大環境改變農村面貌時仍有力之未逮的落寞感。
農民文學的問題
就農民文學漸漸被邊緣化而言,黑島傳治在理論與實踐方面有所建樹,自然能看到問題的癥結,並帶有那個時代普羅文學的激進性與政治意識形態掛帥。他在〈農民文學的問題〉一文表明,近年來,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陣營中,越加關注農民文學的發展與成效。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聯盟中,有必要特別設立農民文學研究會,但是必須將它置於無產階級藝術聯盟之下來管控。
此外,在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召開的擴大革命作家國際影響的決議中,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必須對這些建議進行討論並將其具體化,這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紮根群眾並與國際關係取得進展的重要提案。他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並非在吃高價糕點的少數階級手上,而是奠基於因飢餓為麵包而戰的工人和農民群眾,他們不受邊界海洋或群山的阻礙,必須在國際上團結往前發展。
至於,在處理農民生活這一題材時,無產階級文學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立場,以及應該發揮什麼樣的效果,這在原則上是可以理解的。從一開始,這就與無政府主義農本派等人的立場不同,他們認為農民可以藉由自己的力量,透過農村與城市的對立,運用「本土藝術」或「農村文化」的力量來實現農民解放。問題在於,即使採取農民生活為題材,他們主要的文學訴求與無產階級文學的方向必須保持一致。
然而,畢竟農民和無產階級工人屬於不同的階級。無產階級文學的基本方針——「從前衛的立場來考察和描寫事物」,在一年前已確立起來,並邁出實質飛躍性的第一步時,無產階級文學如何從不同於工人屬性的農民的特殊生活條件、地理環境、習俗、保守性等等,以及他們受制於各種條件下的需求和慾望表現出來,仍然是個巨大挑戰。目前,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沒得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無論是資產階級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他們對農民的生活不夠重視,甚至瞧不起農民。然而,在無產階級文學中,仍然有幾部作品涉及農民的生活,描繪了佃農和地主之間的衝突和鄉村農會成員活動情況,譬如立野信之、細野孝二郎、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等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中都以清晰生動恰如其分把農民的生活展現了出來,並帶有極高的藝術性和普世格局。
在中野重治的《鐵的故事(之一)》中,作者巧妙而具體呈現著X標舉的政治口號。他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學中這些問題必須得到重視,尤其涉及農民生活時,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突顯出來。在小林多喜二的中篇小說〈在外地主〉中,已顯露出工人和農民相互合作的文學性的描寫,而這被視為一種有意義的初探。平林泰子和金子洋文,他們各自透過描繪信州(長野)和秋田的農民生活,由此可見他們已掌握到其核心所在了。
然而,這些作家迄今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僅從數量上看,與占日本人口大部分的龐大農民相比,不但不多而是很少的。當然,乍看之下,其文學面貌是這樣,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還沒有充分呈現出隱藏在農民生活中的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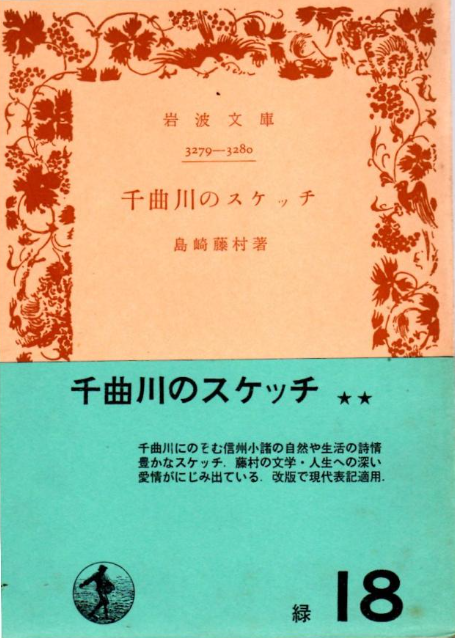
黑島傳治指出,資產階級的文學觀向來看不起所謂的農民文學,除了島崎藤村的散文集《千曲川素描》和其他作品中部分提到農民,以及任何人在討論農民文學時總是引用的唯一版本長塚節的長篇小說《土》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作品。如果真要談點農民文學,出現在真山青果〈南小泉村〉中的農民,也只是被當成污穢的野獸般嗤之以鼻。
其後,在資產階級文學中,有幾部以農民為題材的作品,但是幾乎偏重在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身上,對農民只是側目而過。不用說,這是資產階級文學向來的偏見,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文學與苦求一碗麥飯拚命掙扎的農民、與那些生產稻米供其食用的農民毫無關聯。他們的文學只為那些細白嫩肉養尊處優的少數人而寫,與小資產階級作家相互應和而已,而這個價值取向正意味著他們對農民的漠視和無動於衷,更遑論去挖掘這樣的題材了。
綜上所論,黑島傳治的文學關懷是鮮明獨立而尖銳的,在為多數被壓制的勞苦大眾發聲,卻又無可避免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僵固政治意識形態的氣息。對於當今的讀者而言,農民文學又有什麼意義?當年,黑島傳治極欲批判的「勝者一無所獲(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歷史教訓,並沒有就此煙消雲散,歷史反而以最諷刺的方式重新登場,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霸權行徑就是最大的歷史反諷!進一步說,文學小說寫得多麼精到,和平主義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地,它們都阻止不了霸權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槍炮與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