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探討馬克思主義對歐洲革命的影響,是賈德(Tony Judt)和史奈德(Timothy Snyder)這兩位研究東歐的歷史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段對話提到馬克思主義對群眾的魅力,以及兩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詮釋者:恩格斯與列寧。
賈德:馬克思主義當時是歐洲激進思想的深層結構。馬克思並沒有完全意識到,他自己便綜合了十九世紀早期許多社會批判和經濟理論的潮流:比方說,他很了解法國政治小冊子的那一套,對英國古典經濟學也略通虛實。因此,這位黑格爾形上學的德國學生留給歐洲左派的只是他的思想中能與當地眾多激憤傳統相容不悖的版本,而且這個版本還提供了一個能夠超越這些傳統的說法。
在英國,舉個例子來說:十八世紀那些激進的手藝工匠或者被剝奪繼承權的農民所主張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藉由堅稱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創造力和所到之處帶給人類災難的核心論述,直接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背景思想。在此,就像馬克思主義本身一樣,我們接觸到一個已經失去但或許能夠重新尋回往日世界的故事。當然,在更早的(而且經過道德化的)眾多版本中——例如在理查.柯貝筆下——強調「破壞」,尤其是人際關係所受到的腐蝕;可是馬克思卻從另一個觀點,將這種破壞轉變成優點,在他看來,一種人類經驗的更高形式可以從資本主義的瓦礫中出現。
至少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末世論本身,相對於工業化早期所帶來的深切失落感與混亂感,只不過是次要的附加反應。於是,也因為如此,馬克思自己並不知道,他為這個世界提供了一個模板,讓群眾可以在其中陳述同時辨認出他們已經說了好一陣子的那個故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魅力來源。但如果這種情緒的根源沒有被呈現出來,僅憑著對資本主義運作有其弊病的描述,再加上三言兩語地斷言未來會有什麼結果,本身並不足以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讓四塊不同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工人、政治機會主義者和社會運動分子都為之心生嚮往。
史奈德:但這其實是黑格爾的魔力,不是嗎,東尼?因為按照你所說的,馬克思其實是把一個本質上保守的觀點,與一種對於過去的精神見解,再加上所謂「對我們不利的東西實際上對我們有益」的辯證論點,給整併起來。例如,想想看恩格斯關於家庭的論述,還有馬克思筆下對人性在被財物所有權腐化之前的看法:在這些篇章裡你看到史前或歷史未記載的過去當中,人性的正直與融洽和諧,多虧他們寫得這麼充滿熱情,如今讀來還是不禁愕然。透過黑格爾的辯證法,懷舊之情與不僅是接受甚至於還歡迎正在毀滅過去所有美好的那種能耐居然還結合了起來。你能夠擁抱城市,你也能夠擁抱工廠:兩者都代表了創造性的破壞。資本主義看起來似乎是在壓迫我們,以及異化我們,並且無疑會讓我們變得一無所有,然而即使如此,其中自有美妙之處,同時也是一項客觀的成就,稍後待我們回復自己的天性,就能夠加以運用。
賈德:不要忘了,就是辯證法的相互對抗,賦予馬克思主義者獨特的優勢。對那些堅持應該聽天由命的自由主義者和進步論者來說,馬克思對受苦與損失、惡化與毀滅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敘述。在保守分子當中,有些人贊同這樣的敘述,但卻準此更加堅定原本主張的過去的優越性,馬克思當然看不起這樣的反應:這些變化,無論在中間的過程裡看起來多麼不吸引人,卻是必不可少,而且無論如何,為了更好的未來,難以避免需要付出的代價。事情就是如此,但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
史奈德:馬克思主義的魅力也跟基督教與達爾文思想這兩者有關:到十九世紀末年,兩者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被哲學性和政治性的觀點所超越。我想這樣講下去我們都會同意,社會主義者把這兩者拋在腦後,只是為了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加以徹底改造。想想看基督教和耶穌受難所蘊含的意義:我們活在這個不完美的塵世中,目的只是為了等待來世的救贖。至於那些致力把達爾文思想推廣於世的人來說(同時也將之庸俗化,這些人裡面包括了恩格斯):演化,他們堅決認為,不僅跟某種對政治變革的憧憬相容,而且隨著演化就一定會衍生政治變革——物種出現,然後相互競爭。生命就跟自然界一樣是相當血腥的,齒間爪上都是一片紅通通,而物種之所以會滅絕,無論在道德上或者科學上,都並非無理(階級的滅絕也是如此)。由更優越的物種出線存活,時至今日造就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現狀,同理,萬事萬物也演化出最佳的可能性。
賈德:到了二十世紀初,恩格斯所詮釋的達爾文思想影響力要遠大於原典。恩格斯在馬克思身故之後繼續活了十三年,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把他自己的解讀嵌入通行於世的馬克思主義文本之中。他的寫作風格比他的朋友清楚。而且他有幸投入寫作的時間正逢科普思想被引進政治與教育主流之後,這一切要歸功於赫伯特.史賓塞等人的努力。例如,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十四歲男孩都讀得懂。不過,當然那也是問題所在。恩格斯對十九世紀的演化論隨意刪改,使得達爾文思想被簡化成一個針對日常生活的警世故事。馬克思主義搖身一變成為可以用來理解萬事萬物的說法:不再只是一種政治敘事、經濟分析甚或社會批評,而是幾乎不亞於一套宇宙如何生成的理論。
馬克思所帶來的這股新的宗教情緒,在其最初的形式當中伴隨著一個終極目的,一個使整篇故事都顯得有意義的終點:這套思想確知自己的去向。到了恩格斯手裡,這一整套被壓縮成一個簡單的本體論:生命與歷史由來處來、往去處去,然而即使這其中存在著可以辨識的意義,也肯定不是源自未來的展望。儘管恩格斯有許多優點,但在這一點上,他與史賓塞非常相似:抱持著機械論,過度野心的主張,極目四望無所遺漏,能把原本組不起來的材料拼裝成一個適用於萬事萬物的故事,從各種時鐘的歷史到每根手指的生理學無所不包。這套萬能的說辭被證明是極為管用的:人人都能理解,同時又能補救公務菁英階層在解釋權上的專擅排他。沒有這套思想,列寧那種獨特的政黨模式是無法想像的。而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們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荒謬歸罪於恩格斯。
史奈德:讓我們回到你先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天主教國家比在新教國家更容易引發共鳴,這是因為使用語言與環境布置的種種儀軌有暗合之處。我們能不能套用這個論點來解釋猶太教與激進政治之間的關聯?
賈德: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世俗的宗教,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不過到底因循的是哪一種宗教呢?這點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其中包含了大量傳統基督教的末世論:人的墮落,彌賽亞,祂的受難與人類的代行贖罪,獲得拯救,復活重生等相關概念。也不乏一些猶太教的成分,但比較少在實質上而更多是在作風上。在馬克思和其後一些更為有趣的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或者萊昂.布魯姆),以及當年在德國《新時代》雜誌上沒完沒了的社會主義論戰中,我們無疑能夠輕易辨認出各式各樣的「皮爾普爾」(pilpul),也就是在拉比裁決糾紛與講述傳統猶太道德規範與過往故事時,心裡頭略帶戲謔的那種辯證性質的自我耽溺。
如果你有興趣,不妨想想看他們在這些哲學範疇裡有多機靈:馬克思主義者對世界的詮釋如果與事情的演變不相符,他們居然還可以顛來倒去,悄悄落跑,然後過一陣子再改頭換面捲土重來。破壞被他們說成是創造性的,而維護既有反而變成消極無益。偉大的東西將會變為渺小,而眼前現存的真理註定將腐朽化為過眼雲煙。那些自己研究過馬克思甚至寫過關於他的文章的人,當我跟他們提起馬克思的意圖與師承當中有這些相當明顯的面向時,他們聽了之後常常會煩躁起來。這些人本身是猶太人的情況屢見不鮮,而且在我強調馬克思的猶太背景時,他們會顯得侷促不安,就好像是他們的家庭私事被人家拿出來品頭論足。
這讓我想起了豪爾赫.塞姆普魯恩那本自傳性的小說《週日何其美》當中的一幕。在他們全家被西班牙驅逐流亡之後,二十歲的他加入了「法國抵抗運動」,隨後被當作共產黨員逮捕起來。當年被遞解至布亨瓦德集中營,在那裡受到一位德國老共產黨員的照顧——無怪乎他竟然能從那邊倖免於難。當年有一回塞姆普魯恩問這位長輩能不能跟他解釋一下何為「辯證法」。於是長輩就給他如下的答案:C’est l’art et la manière de toujours retomber sur ses pattes, mon vieux(永遠都能讓你雙腳著地安全降落的藝術與技巧)。這套根本就是猶太教士的修辭法:所謂讓你雙腳著地安全降落的藝術與技巧——尤其是藝術——幫助你能站穩權威和堅信的立場。要成為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把自己的無根狀態變成一種優點,其中沒有宗教羈絆尤為關鍵,同時要牢牢守住那種每一個希伯來語學校的學生都非常熟悉的論理方式(即使只是一知半解也無妨)。
史奈德:大家都忘記了,在舊俄帝國裡,猶太社會主義者比其他政治勢力都組織得更早也更好。「本特聯盟」實際上比其他組織都出現得早,而且一度讓當年其他圖謀在俄國創立政黨的嘗試都相形見絀。確實,列寧為了要將他的立場定義清楚,只好把他的追隨者從「本特聯盟」分離出來——這項分裂的重要性更甚於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廣為人知的分裂。
你怎麼看列寧在這一整代人當中,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當中,在第二國際當中的運作?
賈德:當年在第二國際當中,俄國人的存在讓大家相當不安。第二國際是由許多馬克思主義政黨聯合組成,比起在沙皇專制統治下的俄國激進分子,這些政黨一般而言都能夠更好地被整合到各國的政治體制裡。各國共產黨人要不要加入當地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在一次大戰前夕是第二國際中最首要的議題,但俄羅斯這個專制帝國的臣民對如此的議題卻毫無興趣。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可以分為屬於唯物主義傾向的德國式社會民主派多數——以比較年長的普列漢諾夫為其中代表人物——以及比較年輕的列寧所領導的少數激進派,兩派人之間的歧見相當深。你仔細推敲不難發現,這是所有威權社會裡敵對雙方之間照例常見的分歧不合:其中一方對威權統治者的微幅改善樂觀其成,另一方則視這種改善為最大威脅,認為反而只是削弱與分化尋求激進變革的各方力量。
透過描繪馬克思主義,列寧重新詮釋、修改並因此激活了祖國俄羅斯的革命傳統。在他之前的那一代,搞革命的斯拉夫派沉浸在一種令人愉快的想法裡面,認為俄羅斯有自己獨特的故事,這個國家無論走向任何激進的行動都會有其獨特的軌道。他們當中有些人贊同恐怖主義,將之視為一種暗中顛覆專制獨裁但同時又能夠保留俄羅斯美好特色的手段。雖然列寧對長久以來俄羅斯積極從事革命、大搞虛無主義與暗殺之類的積習感到不耐,但他還是堅持認為要繼續強調自願的行動力。不過他這種強調自願的看法是伴隨著馬克思主義者憧憬各種革命即將到來的想像。
然而列寧對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沒有比較不輕視,儘管在厭惡無意義的暴力這件事情上他們看法其實一致。在俄羅斯的傳統裡,斯拉夫派的對手是西化派,基本上西化派是相信,俄羅斯的問題在於心態落後不前。俄羅斯本身沒有什麼獨特的長處,俄羅斯人的目標應該是要把國家帶往西邊歐洲國家已經走出來的發展道路上。西化派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從馬克思和政改論者的見解中推論出,西方已經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一切都應該以更純粹的形式在俄羅斯促其儘速實現。資本主義、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先進國家都已經先經歷過了;在俄羅斯出現的時間會來得比較慢,也會比較晚,但等那麼長時間還是值得的——西化派的這種態度曾經惹來列寧多次出言表示不屑。因此,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終究還是把西方式的時局分析跟傳統的俄羅斯激進主義給結合起來。
過去大家都認為這只是顯示出列寧在理論上的卓越才華,但我對這個看法不是那麼確定。列寧是一位出色的謀士,但除此之外也無甚可觀,而在第二國際中,除非你在理論上有所建樹,否則不可能成為重要人物,因此列寧才把自己呈現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天才,他的擁護者也以此形象大肆宣傳。
史奈德:我很想知道列寧的成功是不是也跟他對於未來的大膽無恥有點關係。列寧視馬克思為一名決定論者、歷史的科學家。幾位那個時代更加聰明的馬克思主義者,諸如葛蘭西、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史坦尼斯勞.柏左卓夫斯基和格奧爾格.盧卡奇都拒絕接受他這個看法(不過盧卡奇後來改變了心意)。但在這方面,列寧對馬克思的闡釋繼恩格斯之後居於主導地位。
接著列寧又判定「歷史的科學家」不僅可以觀察眼前的實驗,還可以介入其中,稍微把事情往前推動。畢竟,如果我們已經事先知道結果為何,為什麼不儘快到位呢,尤其是在我們明明就非常渴望如此結果的情況之下。不過有了列寧的這個看法,心裡一旦相信了他這個偉大的主意,你就能更有把握地面對眼前那些渺小、瑣碎又乏味的事實所呈現出來的意涵。
而這反過來駁斥了當年仍為顯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康德形式」(Kantian forms of Marxism):這種思潮試圖賦予馬克思主義一套獨有自足的道德規範。對列寧而言,道德規範只是回溯性質的工具。小小的謊言、輕微的詭計、無足輕重的背叛與一晃而過的掩飾,等到結果出來全部都會顯得有意義,同時在道德上可以接受。在這些小事上真切的道理,運用在大事上也同樣有效。
賈德:你甚至於也不用對未來抱持什麼信心。問題在於,究竟原則上你是同意所有付出都容許留待未來再予以清償,還是你相信應該即時就得到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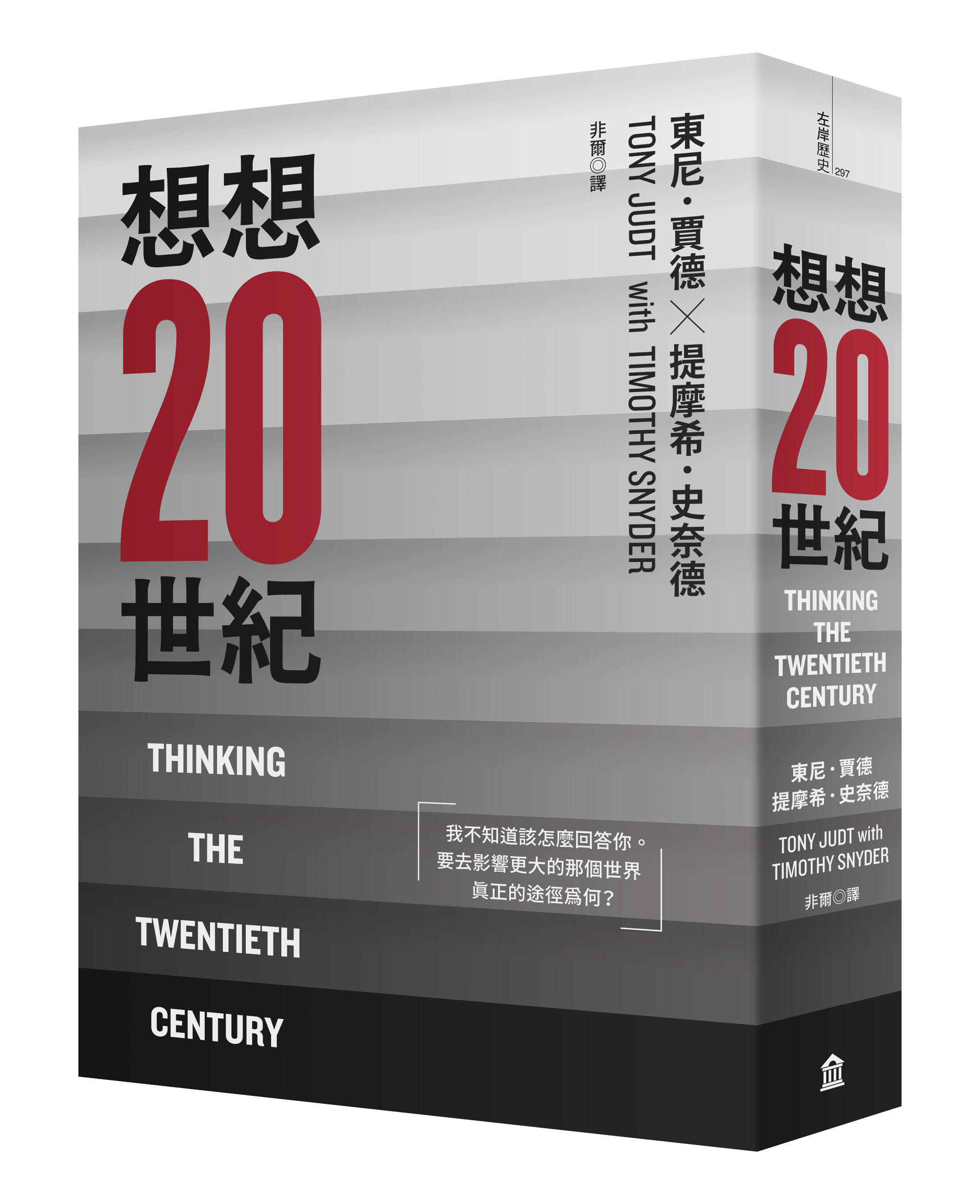
書名:《想想20世紀》(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3523)
作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