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日本近現代作家在文壇上聲名鵲起,很大程度藉助於同仁雜誌的刊發,年輕作家們在這個園地上磨練文筆,相互激盪相互批評,以此求取進步的文藝力量,最終自我證成時代的代言人,而文藝雜誌《白樺》正是催生出白樺派作家群像的母體。
它1910年4月創刊,直至1923年停刊,共出版了160期。該團體重要成員:木下利玄、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正親町公和、里見弴、兒島喜久雄、長與善郎、高村光太郎、柳宗悅、有島武郎、有島生馬等。這些成員大多為學習院出身的貴族和富豪世家的子弟,他們都擁有各自的文學觀。
白樺派活動可分為三期。初期(1910-1914)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倡導個性解放與自由主義;中期(1914-191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進一步宣揚人道主義,吸引眾多的支持者;後期(1918-1923)文學藝術觀轉變,從醉心於歐洲美術轉向關注東方美術,1923年以悼念有島武郎特輯終刊。要言之,大正時期文壇的主流正是由白樺派作家們推波助瀾而成。

性苦悶共同體的形成
文評家川西政明指出,明治四十年代(1907)日本年輕男子有個特徵,他們甚少與普通家庭的女性有密切接觸(有點像現今的草食男性),也就是說,他們積壓性事得不到適時的排解。因此,他們不是去吉原遊廓(現日本橋人形町)找藝妓,就是到洲崎(現東京江東區)招妓來疏通性慾。如果這個方法行不通,多半就與家中女傭發生性關係。
在白樺派作家中,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實篤、里見弴、有島生馬等,都與家中女傭有過性關係,並將這些刻骨銘心的過程,以私小說或心境小說表現出來。根據志賀直哉的年譜,1907年他就讀東京帝大英文科期間,翌年轉入國文科,因愛上家中女傭(千代),許諾要將對方娶進家門,但因家庭身分地位相差懸殊,他的父親強烈反對,進而導致父子嚴重失和的局面。志賀直哉是個固執的人,他不打算服軟,是年,他發表中篇小說〈大津順吉:上/下篇〉,藉由主角(即他本人)做另種形式的申辯。主角順吉一直以來沒有女朋友,之前有過類似的男性情誼,但不曾談過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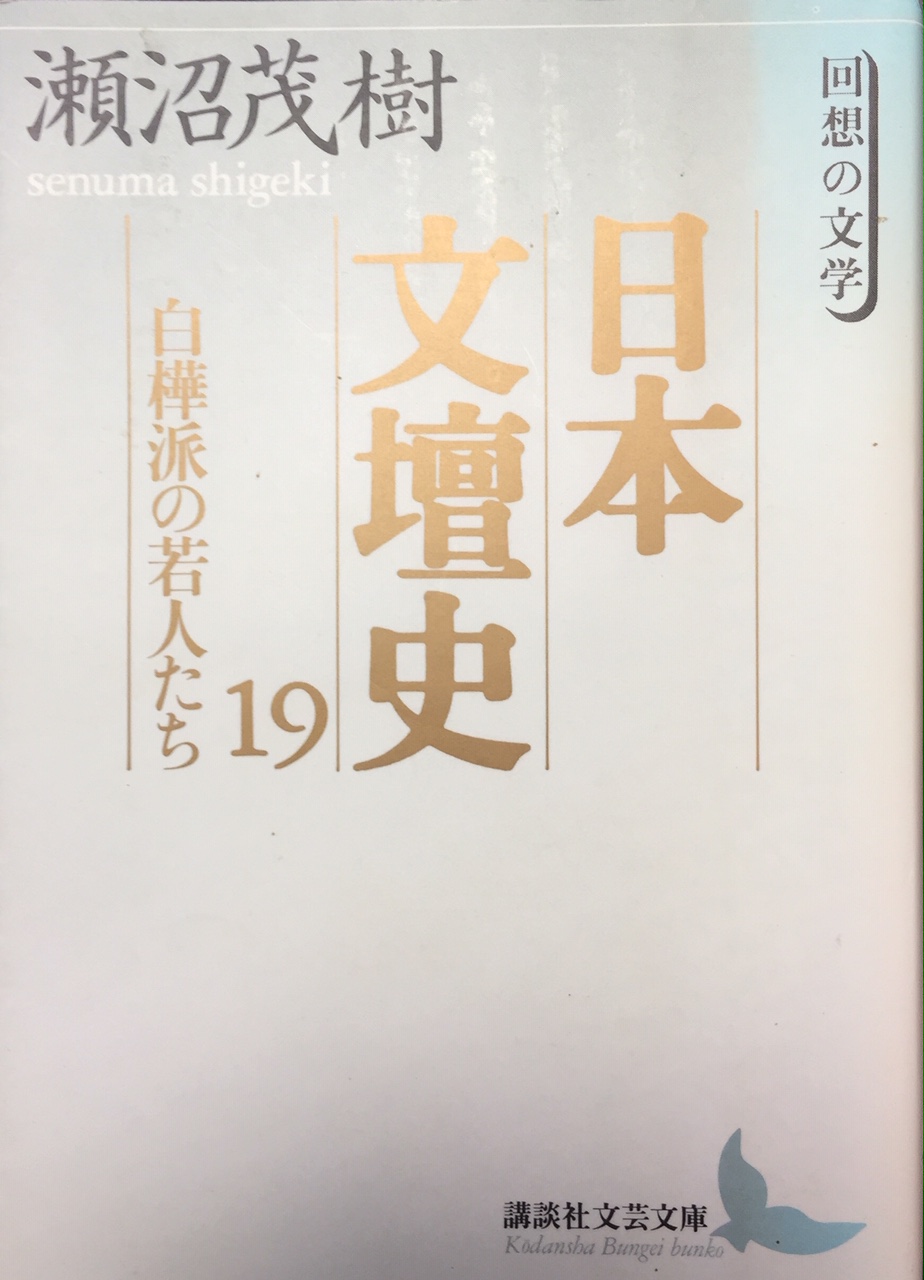
他在上篇開頭說道:「在我的生命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一想到『這輩子愛情終究不會向我走來』,就感到寂寞難耐,對工作也完全喪失信心,根本無法理直氣壯地大吼一聲:去你的吧,戀愛!於是我的生活逐漸走向與女人無緣的境地。十七歲那年夏天,我成了一名基督徒。過了二十歲以後,我對女人的慾求越來越強烈了。」然而,在他想到倡導無教會主義的思想家內村鑑三的訓誡「要嚮往正義,憎惡虛偽」時,又湧生出深深的苦惱。
順便一提,志賀師事內村鑑三七年之久,受其思想很大影響,有一次,志賀到新宿角筈教會所聆聽內村的演說,內村嚴厲批判「足尾銅山礦毒事件」,他為此深感震驚,計劃到現場視察一番。然而,其父直溫以其祖父志道曾與古河市兵衛共同經營「足尾銅山」為由悍然反對,父子倆為此發生嚴重衝突,數年來冰火不容。
回到志賀直哉如何面對性慾的問題上。正如中村光夫〈論志賀直哉〉指出那樣,志賀直哉受到內村鑑三的思想影響,但他最終依然為追求忠實的自我,為自己開闢新的活路:「我們要想理想化地戰勝一切情慾,完全地保住肉體的聖潔。要拋棄頭以下的部分,僅僅保留頭部。」換句話說,直哉只是把「逃避淫行」當成座右銘,表面上激烈詛咒自己的肉體,在屢次詛咒肉體當中,他將它視為是對來世的憧憬。
在順吉(志賀)被性慾折磨到痛苦難當之際,竟然對放在房間裡的維納斯石膏頭像產生了一種愛的情感,在無法克制的衝動下,他甚至親吻那冰冷而堅硬的嘴唇,兩個鼻子相互摩擦,漸漸變成了淺黑色。有一次,他還把石膏頭像帶進浴場,用肥皂把她洗得乾乾淨淨。
不僅如此,他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關子和真三〉來探討何謂奸淫。在他看來,已婚夫妻之間有時也會構成奸淫罪,而相愛的未婚男女的性交很多時候並未如此。正巧這時候,有朋友邀他參加了一場外國人舉辦的舞會,鼓勵他開拓社交關係。在這場舞會中,順吉再次袒露自己的感官世界,他看到一名十六七歲的美麗少女在其附近走動,那名少女面容白皙身材高挑,一身和服配著紫色的褲裙,但仔細一看,她的神情有點憂傷身姿顯得倦怠纖弱,置身在眾人自我陶醉與故作姿態的氣氛中,顯得格格不入,這情景使得他興起了憐惜的情感。事實上,他在意的是,少女在緊身衣的束縛下顯得更加纖細的腰部,以及在腰帶上那鬆軟豐滿的前胸。

他承認道,「以我的性情和興趣來說,這些原本都是我所喜愛的。不過,我的禁慾思想以及由此塑造的第二性情和興趣,超出了原本的克制並明確地支配起我的意識。久而久之,我不得不把它看成是順乎情理的事了。我有意向那些漲紅了臉來回炫耀舞姿的人投去輕蔑的目光,如今的我,為當時怯懦的內心感到羞愧……」
自然主義與小說家妙筆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志賀直哉在描寫情境動態方面尤為出色,譬如,他去澀谷拜訪朋友,朋友不在家,他走到朋友家後面寬廣的平地,逕自躺在樹蔭下的草地上。他看見白雲靜靜浮動於清澄而高遠的天空。烏鴉時而從空中飛過。不知不覺間,他睡著了。醒來時,太陽落了下去,周圍的景色都蒙上了青色,成群的烏鴉急急地從天空這邊飛向那邊。
在〈大津順吉〉下篇,這樣寫道:「每年的春末到夏初,我的大腦總有些不太正常(後來志賀把它寫成短篇小說〈渾濁的頭腦〉,狀況一年不如一年。那段時期我心情彷彿浮在泥水上的金魚,焦慮的情緒使我承受著比金魚更痛苦的煎熬。在那樣一個午後,我獨自在二樓的房間躺著。這時候,隔壁西洋人住家的草地上傳來鸚鵡的鳴叫。我眼前浮現出鸚鵡伸出淺黑的圓圓的舌頭,拍擊著翅膀,一邊搖動腦袋一邊高聲鳴叫的發怒模樣。過了一會兒,鸚鵡開始不斷喊出各種各樣的號令,雖然吐字不清,但語調頗像那麼回事:齊步-----走!立正……。究明其中因由,原來那戶人家對面鄰居就是旅團司令部,所以鸚鵡自然地記住了這些號令。
接著,十七八歲的女傭千代登上了樓梯,跪在地上對順吉說,茶水準備好了。他起身來到簷廊上,望著鄰家寂靜的庭院。這時候,筆觸又回到那隻鸚鵡身上。鸚鵡正拚命地伸著短脖頸全神貫注趇啃咬籠子上的鐵絲。寫完了鸚鵡的情態,他家小白狗跟著登場了。他這樣描寫與狗的互動:天雨剛一停歇,小白的爪子沾滿泥水跑進客廳裡亂竄。
有時候,他揮舞著竹掃帚大聲呵斥,滿院子追著牠跑,最後,小白走投無路,翹起屁股將肚子貼在地上,眼睛瞇成一條縫,服服帖帖的,但一不小心就撒出尿來。儘管如此,他很快就原諒了小白,牠見狀立刻在他腳下又磨蹭著的,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多次。有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正要走去簷廊,旋即看見小白垂著尾巴朝他飛奔過來。他停下看了看,只見千代像他那樣拿著竹掃帚從倉庫一角衝了出來,一看見順吉少爺,就急忙笑著轉過身去,從耳朵到脖頸泛起了一片紅暈。然而,好景不常,一天下午,他正在樓上房間看書,忽然聽見街上傳來淒厲的狗吠,接著,聽到類似棍棒捶打皮肉的沉悶響聲。絕望的哀號和擊打聲交混在一起。不久後,狗吠漸漸微弱下去,擊打聲依然持續著,最終什麼都聽不到了。後來,小白突然失蹤了,他到街上拚命尋找。

結果,三天後,他家裡另一名女傭在雜物間的木炭袋後面的縫隙裡,發現了小白的屍體。他這樣描寫小白的死狀:雪白的狗毛沾著炭灰,顯得有點髒污。牠前腿向前後腿向後伸展著,全身軟綿綿緊貼地面,就那樣沒了氣息。確切地說,從這個對於日常生活的描述,亦反映出順吉(志賀)的性格來。所謂知子莫若父,他父親這樣批評他,「你孤癖、傲慢、易怒、懶惰、沒有獨立精神,怎麼看都像個社會主義者……」對順吉而言,儘管他在某個時期投稿賺點稿費,但他清潔認識到以此文筆產能並不能維持生計。
一切事情總有諸種原因
志賀直哉由於母親早逝的緣故,受到祖父母的百般竉溺,自然養成貴公子和高等遊民的習氣,正如上述,他缺乏與女性接觸的機會,不由得愛上自家女傭千代,更激進的是,他想娶千代進門。然而,在階級森嚴的明治時代,有華族身份的家族姑且不說(可參閱森茉莉的小說《戀人們的森林》),家境富裕的志賀家絕不可能答應。而志賀並不掩飾這段不對等的戀情,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從我愛上了千代,我對傭人產生了一種至今沒有過的同情。第一次想著他們在廚房裡吃著什麼樣的食物,也第一次注意到他們在受雇期間,不曾享受過我每天洗澡時用的沒有半點污垢的清澈的浴池。我昨晚和千代聊天,談到她從小和我一樣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中長大。在家裡,她深得父母和哥哥的寵愛,就像祖父母愛我那樣。聽她說這些話,我心裡有種異樣的感覺。……那時候,我整個人已經處在興奮之中,起身從小櫥櫃的抽屜裡取出去世母親留下的金戒指,套進千代的手指,緊緊地摟抱著她親吻起來。千代的身體突然失去重心似的重重地壓在我的身上。我稍一避開,她的脖子就無力地向前垂下去,像昏過去了一樣,不論問她什麼都不回應。這時候,我的腦際閃過一個邪惡的臆測,千代或許害怕我對她做出比接吻更激烈的事來,並認為我在虛假的演戲。她俯臥在榻榻米上,脖頸沾著汗濕的鬢髮。
不用說,志賀直哉這件試圖強渡關山的婚事失敗告終,向來對他竉愛有加只為他而活的祖母也不支持,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不得不深切感嘆,「我被祖母這個敵人(祖母苛刻志賀的生母阿銀)所愛,我也愛著這個敵人,同時又不得不憎恨她。」事情到此還沒結束,當初,把介紹千代來此的村井夫人(其丈夫是直哉之父的部下),聽聞這等大事急忙趕來欲將千代帶回去,為此險些與志賀少爺爭吵起來。經過各種大大小小衝突,千代最終被辭退趕出了志賀家。志賀做出的反制就是將此經過寫成〈大津順吉〉,權充對絕對父權的抵抗。
諷刺的是,他這部以此為題材的中篇小說刊登在《白樺》雜誌,獲得生平第一筆稿費100圓,後來找上洛陽堂談出版事宜,原先父親答應支付出版費用,當直哉向其父要求給付時,父親當面斥責他,「你寫小說將來能出息嗎?小說家是什麼東西?」不過,直哉大為光火出言反駁,爭吵到最後,他於10月25日離家出走,在東京銀座木挽町的旅館投宿兩星期左右,就搬到廣島縣尾道租屋了。
從志賀直哉作品編年史來看,短篇小說〈他與年長六歲的女子〉(原本題目為〈一個青年〉,後來改為〈渾濁的頭腦〉),頗能體現出他名符其實的風流情史。當時,小林秀雄和有島生馬批評這部小說為失敗之作,但相當肯定志賀直哉的寫作態度,他毫不避諱地呈現青年的性苦悶。這部小說中的女子阿峰,確有其人,她是吉原的角海老樓的娼妓。
根據志賀直哉的日記指出,明治42(1909)年9月20日,他初次到吉原狎妓,認識了阿峰。數年前,他與家中女傭談戀愛,對方是年輕處女,不知道「如何發揮愛的感覺」,讓他覺得備感壓抑。他正是透過阿峰才深刻認識「何謂女人」,認真探討「性慾的本質」。在那以後,他經常找阿峰體驗,以此深化這方面的思索。明治43年元旦,他珍惜每寸光陰,找上阿峰敘情。元月5日,他從箱根回來旋即又去找阿峰,並在日記中寫下幽微的感想。
一月九日----「最近,因阿峰之事讓我備感苦惱,我甚至懷疑是否自己與她談戀愛。我覺得此痛苦乃無益之事。為了擺脫此痛苦,我甚至想過以自我調整方式解決,向其他女子投懷送抱。我將此事告知阿峰,阿峰說了聲「對不住」面露慍色。結果,(我們)很不情願地交纏了一回。」
二月十八日----「阿峰所說的話,對一個不循規蹈矩的女人並不尋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尊重她的。阿峰對我並沒有愛意,是我(一廂情願)想獲得她的情愫。然而,這是徒勞之舉。阿峰完全抹煞我的好意,向(啊,那樣的女人)索求更多是我的愚蠢。我從她身上學到很多事情,與她交往並非毫無意義。
四月十二日----「十一點左右抵達,已有兩個客人。我有點不高興,一見到(阿峰),果真被敷衍對待。阿峰覺得我很神經質有時故意對我冷淡,我反駁說,阿峰不是個好女人,她有看透人心世事的本領,但未免太強勢了,其實她還不能看透更深層次的人心。下午五點許,我離開此地……」
四月十九日----「我告訴阿峰她不能滿足我,今後兩三個月或半年不上這裡來。我不知為何說出這種話。阿峰斷言我做不到。我不甘示弱說,我對你的感情,與對阿峰這種特種行業的女人的心情不同,倘若我真的迷戀上你,你必定逃避。然而,我不由得敬佩一個從未接觸過當今新文學的女性(阿峰),卻能從實際經驗中了解如此多的事物。
五月九日----「三個星期左右,我找上其他女人,完全沒有跟阿峰說話。」進入明治四十三年後半,志賀直哉探究女人的心理,漸漸產生了不同的感想。
九月九日----「下午,去阿峰那裡,阿峰也老了。我覺得她是一個骯髒的女人,只是外在環境使她看起來尚有價值而已。」
九月十九日----「去年九月二十日,是我出生以來接觸那種女人的第三百六十五天,我初次患了那種病,度過不愉快的一夜。」
十月二日「不知怎的,我對阿峰並不感到不舒服。不過,我說不覺得不舒服,又覺得好像在說謊。或許,阿峰在工作上如此對待我是正常的舉措,但想到這裡,要我佯裝無事說不想這件事卻是言不由衷。因此,除非有特別的事情,我不去阿峰那裡。總之,我儘可能保持這種感情態度。……」
十月九日----「下午,(睽違三個星期)去了阿峰那裡。先治療心中塊壘。」
二月二日----「阿峰這個女人,不能為我滿足些什麼,我對娼妓阿峰也毫不期待。或許,這女人離開那個環境,我們再次見面時,我又能從她身上學到東西。」
二月九日----「阿峰說,這個月內不做這個行當了。換言之,對阿峰而言,我只是個逢場作戲中的過客,至少從今以後我與她毫不相干了。阿峰是個愛恨分明、做事機靈的女人,有許多優點,同時很多地方又令人討厭。……儘管如此,她是個身體健康和性慾極強的女人。不過,這種type的女人很多,當我需要的時候,阿峰就會出現在我面前。接下來,我想去菊川家找美如蝴蝶的女人。」
果然,二月十八日,阿峰離開了妓院開始從良的新生活。兩天前,志賀直哉就在角海老樓投宿,寫作〈他與年長六歲的女人〉時,品嚐著無從想像的別離滋味。志賀直哉與妓女阿峰交往了將近一年半,隨著阿峰離開風月場所,他們自然形同陌路,也可以說,直哉少爺毫無眷戀從阿峰大學那裡畢業了。
然而,小說文本以外的志賀直哉,對女人(性慾)有著不知疲勞的探究,是年四月九日,吉原發生了火災,角海老樓燒毀後,直哉照樣進出吉原妓院區,繼續研究未竟的性學課程。因此,後來志賀直哉更直接表態,「我渴望有健康的身體,因為健康的身體,才有旺盛的性慾。我希望自己的性慾強而不淫亂。高爾基寫過一個國王因性慾強烈被女人愛戀的故事。我不希求年邁時仍有性慾,但不希望四五十歲之前,性慾就衰竭下來,否則就不生出健壯的子孫。」
通往和解的道路
正如前述,自志賀直哉欲娶家中女傭未果,與父親的關係閙得很僵,他亦數度搬遷以抵抗對父權的疏離。1915年(大正4年)9月,他迎來了一個新契機。白樺派成員柳宗悅規勸直哉搬回千葉縣我孫子市的手賀沼畔居住,他接受這個建議,同時期還有白樺派大將武者小路實篤搬來此地。翌年,武者小說介紹了表妹康子與直哉結婚。1916年12月,國民作家夏目漱石溘然長逝,直哉聞訊後深感悲痛,「為了報答漱石的提攜之情,他會努力寫出好作品,只刊載於《朝日新聞》,恕不在其他媒體發表。」
另外,武者小路實篤給予直哉很大的精神支持,〈在城崎〉、〈好人夫妻〉、〈赤西蠣太〉等短篇小說,都是他在這時期完成的作品,進一步說,他(直哉)主動與父親重修舊好,才是促成他們父子和解的關鍵因素。他發表於1917年的中篇小說〈和解〉,即是這段折衝過程的最佳註解。在這部小說中,直哉的繼母起著架橋的作用,因為那時直哉返回老家探望,父親依然不讓他進家門,不與他照面說話,整個家裡氣氛凝重。這時候,善良的繼母含著眼淚對直哉說:今天,我大清早向佛祖祈求,請佛祖保佑我們,你不要因一時之氣,再說什麼激烈的話。哪怕閉上眼睛,跟向你父親說句道歉的話,承認自己錯了就行。你父親年紀越來越大,和你的這種關係讓他心裡很痛苦。你若能道個歉,你父親就滿足了。
和解的場面是這樣建構的。那天,直哉走向父親的書房,書房的門敞開著。他看見父親面向他這邊,神情溫和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他一走進書房,父親一邊把頭轉向窗旁的椅子,一邊指著他前方的地板說,你把椅子搬過來。他將椅子搬到父親對面坐下,沉默不語。父親開頭說道,先聽你說吧。然後,起身去按牆壁上的電鈴(吩咐女傭),回到椅子上。直哉終於開口說,「我覺得您和我的關係這樣僵持下去沒有任何意義。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知道那些事讓您很傷心。我覺得有些事是我做得不對。」話畢,父親「嗯」了一聲,點點頭,問道:「好。那你的意思是?是說奶奶健在的時候,還是以後一直如此?」直哉終於忍不住淚水說,「直到今天和您見面之前,我都沒有考慮長久以後的事,只想在奶奶身體健康的時候,您能允許我自由進出這個家。如果真能奢望以後,就再好不過了。作為父親的鐵石心腸軟化了。他說了聲「是嗎」,雙唇緊閉,眼裡噙滿了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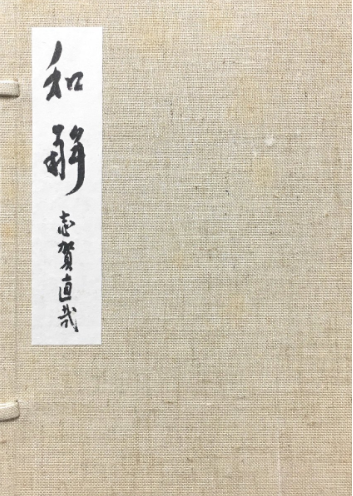
片刻以後,父親帶著哭聲說,「我當然也怨過你,但前幾年你突然說要搬出去住,再三勸說也不聽。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作罷。我從來沒有要把你趕出去的想法……」,兩個男人說出心中的原委,惹得在場的叔父和繼母都喜極而哭了。志賀家的父子就此共同完成了破冰之旅。半個月後,直哉收到叔父從京都返回鎌倉的來信,在信文最末處引述了《碧巖錄》兩行詩句:「東西南北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岩雪。」似乎為這由悲轉喜的人生境遇送來深邃的禪意。人之人之間的衝突矛盾在所難免,就算不能即時放下它,的確也應當努力尋求對話與和解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