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在同屬日本普羅文學作家陣營中,尤其面對反戰和支持戰爭的良心時刻,無論是其從作品探討或者思想立場來看,宮本百合子和林芙美子都比佐多稻子更多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讓研究者重返於那個歷史時空下,置於客觀性的歷史舞台進行評價。只不過,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何佐多稻子的作家經歷較少被提及和檢視呢?這是否意味著作為愛好文學的讀者公眾,從其生涯和文學經歷做實證性的考察?又或者我們可以從中看見戰爭時期特有的歷史鏡像,進而找到如康德所言「人性這根曲木絕對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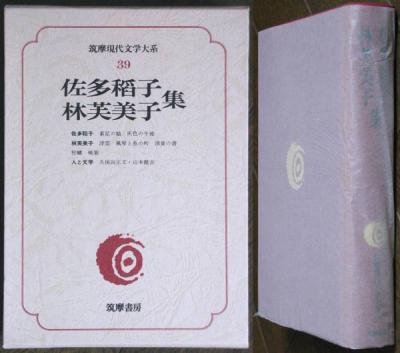
命運流轉
小說家佐多稻子1904年出生於長崎市,由於父親島田正文母親高柳由紀在中學生時期偷嚐禁果,使她提早來到人世間報到,但亦因為這個緣故,她出生後不久,被送往祖母之弟家裡作為養女。1911年4月,她就讀長崎市勝山普通小學,8月母親去世。1915年10月,其父親辭掉在長崎三菱造船的工作,舉家搬到東京的本所向島與表叔佐田秀實同住。當時,佐田秀實正在早稻田大學讀書,是一個頗有才氣的文學青年,參與過島村抱月的「藝術座」劇團。問題是,其父親始終沒有工作,家境陷入困頓。
後來,她轉學到向島的牛島小學(與詩人堀辰雄同校),不到兩個月即休學,只念到小學五年級,即到和泉橋一家牛奶糖工廠當童工。在那之後,她做過許多差事:淺草的蕎麥麵店、上野的高級料亭,以及丸善百貨洋貨部的店員,可謂經歷過各種生活磨難。1924年,他與富豪的獨生子結婚,婚姻生活維持不到一年關係破裂,為此一度自殺未遂,最終以離婚收場。其後,她為了維持生計,一度在本鄉動坂的「紅綠咖啡館」當過女侍。但正是在這個地方(如位於臺北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廳)和機緣,促成了一個年輕女性的文學願景,因為創辦文學刊物的青年詩人都聚集在「紅綠咖啡館」,在此編織屬於他們時代的文學夢想。

文學機緣
事實上,佐多稻子比同儕者更早獲得了文學方面的啟蒙,就讀小學期間,當過班長又熱愛閱讀,經常進出圖書館閱讀西洋童話故事或雜誌小說等,無形中奠定了小說寫作的基礎。1926年4月,文學刊物《驢馬》雜誌創刊,如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堀辰雄(代表作《起風了》)、西澤隆二等,都是其重要成員。佐多稻子因為這個機會,成為《驢馬》雜誌的同仁,並受到他們的文藝思想的熏染。不僅如此,她結識了菊池寬、久米正雄和江口渙等知名作家,得到詩人室生犀星和芥川龍之介的精神奧援。
確切地說,《驢馬》的成員們有著高尚的文學抱負,追求至高的藝術性。1922年,22歲的佐多稻子與該雜誌成員窪川鶴次郎結婚了,並開始在《驢馬》上發表抒情詩歌。1927年前後,《驢馬》的同仁除了堀辰雄以外,幾乎全部投入當時興起的普羅文學運動,佐多稻子也受到影響,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述,相信無產階級文學足以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夢想。1928年2月,她根據親身經歷創作了首部短篇小說〈牛奶糖工廠的女童工〉,在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的鼓勵下,是年4月發表在《普羅》雜誌上。這篇作品問世後,獲得文學界的好評,其後被收錄改造社出版的《新銳作家叢書》,進而奠定其新進作家的地位。順便一提,作家黑島傳治所加入的普羅作家聯盟之後,其作品發表在《戰旗》雜誌上,吸引諸多讀者閱讀,該雜誌發行印量高達2萬6千部,形成了另一波奇特的文學高潮。
日本共產黨的作家們
在那以後,佐多稻子與中條(宮本百合子的舊姓)百合子等女作家,擔任日本普羅作家同盟婦委會委員,以及《勞動婦女》雜誌編輯委員,有了更多刊物編輯的歷練。1932年4月,佐多稻子正式加入了日本共產黨,與此同時,又與轉入地下工作的小說家小林多喜二、作家宮本顯治(日共領袖)等開展組織活動。在此期間,佐多稻子在《文學新聞》發表短篇小說〈千人針(護身符)〉,反戰立場極為鮮明,仍然創作不輟,繼續發表了五部作品:〈幹部女工之淚〉、〈祈禱〉、〈小幹部〉、〈怎麼辦?〉、〈強制歸國〉,刊載於《改造》、《文藝春秋》和《中央公論》雜誌上,這些作品取材於東京的棉紗紡織廠的勞資爭議,反映出當時勞資對立和寫實主義作品的圖景。然而,從1932年3月至4月,隨著文化聯盟的運動遭到政府鎮壓,許多左派作家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究責,如中野重治、蔵原惟人、中條百合子都遭到檢舉拘留,而這些因素造成其內部(路線)意見分歧。

轉向的季節
從日本文學的發展史來看,1933年之後可說是極為關鍵的年份,許多激進的左派作家紛紛遭到當局逮捕,其中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思想警察刑求致死的事件震撼社會。此外,日共領導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引來了言論思想界的軒然大波。
佐野和鍋山是日共中的實力派人物,但就在那年秋天即將舉行上訴審判之以前,他們二人卻突然宣布轉向,這突兀的舉動給日共的群眾運動留下了巨大的謎團。
有關作家轉向的消息,各家報紙都予大幅披露。譬如1933年10月,《都新聞》即以「片岡鐵兵假釋」為題報導說:「片岡鐵兵是著名左派文壇中的寵兒、新感覺派的健將,與橫光利一齊名的小說家。他因受到1930年2月事件牽連,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進言之,類似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的思想轉向聲明,不僅在政治領域上引發震盪,還直接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學趨向。在昭和文學史當中,這些現象被歸納為「轉向文學」,等同於作家在面對國家權力壓迫下,自己所做出的思想姿態立場。
研究者普遍認為,初期的轉向小說,多半採取私小說的形式來表現,透過隱微「告白」的方式,點出小說人物思想轉向的身不由己,較為缺乏實質性的內容,這種餘白成為私小說的特徵。例如,島木健作的《癩病》、《盲目》、村山知義的《白夜》、窪川鶴次郎的《風雲》、林房雄的《青年》、武田麟太郎的《銀座八丁》、高見順的《應該忘故舊》等作品,都作為轉向文學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正如鶴見俊輔在《共同研究 転向》(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中指出的,「轉向」這個詞是司法當局首先使用的,這意味著當局將個人思想傾向改變到當局認為正確的方向。」顯然的,政府當局運用國家權力施壓左派作家產生了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同陣營意識型態的分裂。
以作家德永直(著有《沒有太陽的街》)為例,他即表明不希望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要專注寫作而決定離開作家同盟。接著,幾位主要作家紛紛求去,作家同盟失去了運作功能。1934年2月,當時日本普羅作家同盟的書記長鹿地亘決定解散該團體,於22日發表了「納普解散聲明」。

但話說回來,佐多稻子加入日共的文學陣營以後,其激進思想和機關刊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為她們帶來了牢獄之災。1935年5月11日,她們遭到檢舉「加入普羅文化聯盟,擔任《勞動婦女》編輯,與宮本百合子等左派作家聲息相通,在各種雜誌發表帶有激進思想的作品,」因而被拘禁兩個月。之後,風波尚未停住。尤其,1937年爆發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全面進入「泥沼化」的第四個年頭,使得日本國內的政治情勢更為緊繃,任何可能危及軍部士氣的文字論述,或者激進的思想領域都受到極大的壓制。
是年月18日,佐多稻子因違反《治安維持法》判處兩年徒刑緩行三年。有些原本反戰的左派作家,基於時代的大潮或生命安全著想,開始轉向支持政府當局的立場,甚至當起從軍記者到戰場採訪,撰寫激勵日本士兵的文章。這包括出身於日共作家文學陣營的佐多稻子。1937年10月,她在《戰爭與女性》發表了〈女性們的變化〉,即可視為明顯的轉變。
作家們的殖民地之旅
時序進入了1938年8月,佐多稻子發表了一篇隨筆〈婦女在戰時體制下的作為〉,旨在回應當局的政令:「由於戰爭時期物資短缺,家庭婦女應該節約用度……」。其後,她發表的〈從和平產業到戰時體制〉的文章,進一步地迎合當時的國家政策:「亦即日本男性工人被徵召上戰場打仗,留守大後方的婦女們,尤其是那些經濟自立的職業婦女,願意到軍需工廠工作精神令人可佩。」換言之,佐多稻子這種曖昧的言論傾向,當局更有理據地邀請她前往戰地慰勞士兵。但是,同陣營的宮本百合子和中野顯治則不同,他們拒絕了這個愛國主義捎來的請柬。在佐多稻子尚未前往戰場之前,1940年6至7月,任職於朝鮮總督府鐵道局的濱本浩就邀請佐多稻子和壺井榮到朝鮮旅遊。
此行結束後,同年9月16日至29日,佐多稻子隨同大佛次郎、林芙美子、橫山隆一等作家,以「紀念滿洲國建國十周年 朝日新聞社派遣、關東軍報導部後援、大後方文藝奉公隊」的成員身份,前往了滿洲各地勞軍旅行。翌年,5月6日,紀念支那事變五周年,以新潮社《日之出》特派記者的身份,與真杉靜枝前往中國中部勞軍。同年8月,佐多稻子「受到軍部徵召,與林芙美子、小山系子和水木洋子等女作家,前往了新加坡和蘇門達臘。」
作家到殖民地旅遊和隨著軍隊前往戰場報導所見所聞,意外地為時代留下某種史實的梗概。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作家筆下的人物事情,仍然有其時空的制約。1942年以後,佐多稻子傾向報導的寫實風格,好比在〈飛往天空的雄心〉的隨筆中,她毫不掩飾地說,「我們的士兵正在中支戰鬥啊!」、「如果日本全國的婦都能乘坐飛機的話,那該是多美好的事呀!我相信那些在戰地艱苦戰鬥的士兵們,也想讓他們的日本婦女同胞看見他們的英姿吧」。
佐多稻子除了撰寫鼓勵日本士兵的隨筆之外,在這個時期,其兩部小說《年輕的妻子們》和《台灣之旅》,同樣反映其個人經驗和帶有歷史修正主義的痕跡。《年輕的妻子們》這部小說最初於1943年9月至11月《婦人公論》上連載,翌年6月,出版了單行本。只不過,這部小說出版時內容重新改寫,如她在該書的前言表示,「所幸,我去了南方(南太平洋),作品的舞台得以延伸到那個地方。在所羅門方面,日本軍取得巨大的戰果,讓全體國民的情感為之沸騰起來;隨著日本軍在南方的戰事告捷,日本人的希望也因此延伸到了南方。」
《台灣之旅》這部小說共分四次,在《台灣公論》上刊載(1943年9月至1944年1月),1948年10月收錄入《我的長崎地圖》一書裡。佐多稻子在這部小說裡,這樣描繪懷抱理想的普羅小說作家:「藤田先生以優異的成績自帝大畢業,但其家庭好像發生了許多變故。因此,他辭掉醫院安定的差事,選擇來到街坊診所看病。藤田先生經常自嘲,他來到台灣以後,友善地與台灣人交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慰藉。」接著,其筆鋒指向另一名作家,「……我記得台灣有個為底層人物發聲的普羅作家。現在,他以經營園藝維持生計,一面熱情地投入創作,我深深被其精神感動。原來,在這小鎮上,竟然有那樣聰明而善於種植花卉的普羅作家。」然而,佐多稻子在《台灣之旅》中,幾處偏向同情左派作家處境的描寫卻遭到刪除,改為其他敘述。根據版本學專家指出,這種因時代制約下的書寫,不僅出現在佐多稻子的作品中,台灣作家楊逵其名作小說〈送報伕〉的結尾處,同樣出現過被迫改動的無奈。

作家的功過
二戰以後,佐多稻子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但因其在戰爭時期支持當局的戰爭立場,一度被指責立場搖擺並受到嚴厲批判。1946年1月,在新日本文學會的「創立大會報告」中,得出了堅定反戰(與帝國主義戰爭對抗)的作家名單:秋田雨雀、江口渙、藏原惟人、窪川鶴次郎、壺井繁治、德永直、中野重治、宮本百合子等等」,佐多稻子就被排除在名單之外。當然,這份名單的呈示,未必就取得與會人士贊同。以壺井繁治為例,他於戰爭期間雖然有所抗拒,但仍然有若干支持戰爭的言論。更準確地說,日本作家在戰爭期間因國家權力的壓迫因而思想轉向,寫出迎合統治當局的言論、順應大潮當個歌德派文人,亦是眾多軟弱人性中的真實反映。在生死交關的叉路上,他們所謂的愛國主義及其政治信仰,終究取決於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或者可以坦言,我們作為那個時代的旁觀者,有時很難測量那些愛國主義者與戰爭之間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