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邏輯與科學哲學
開場白:人和哲學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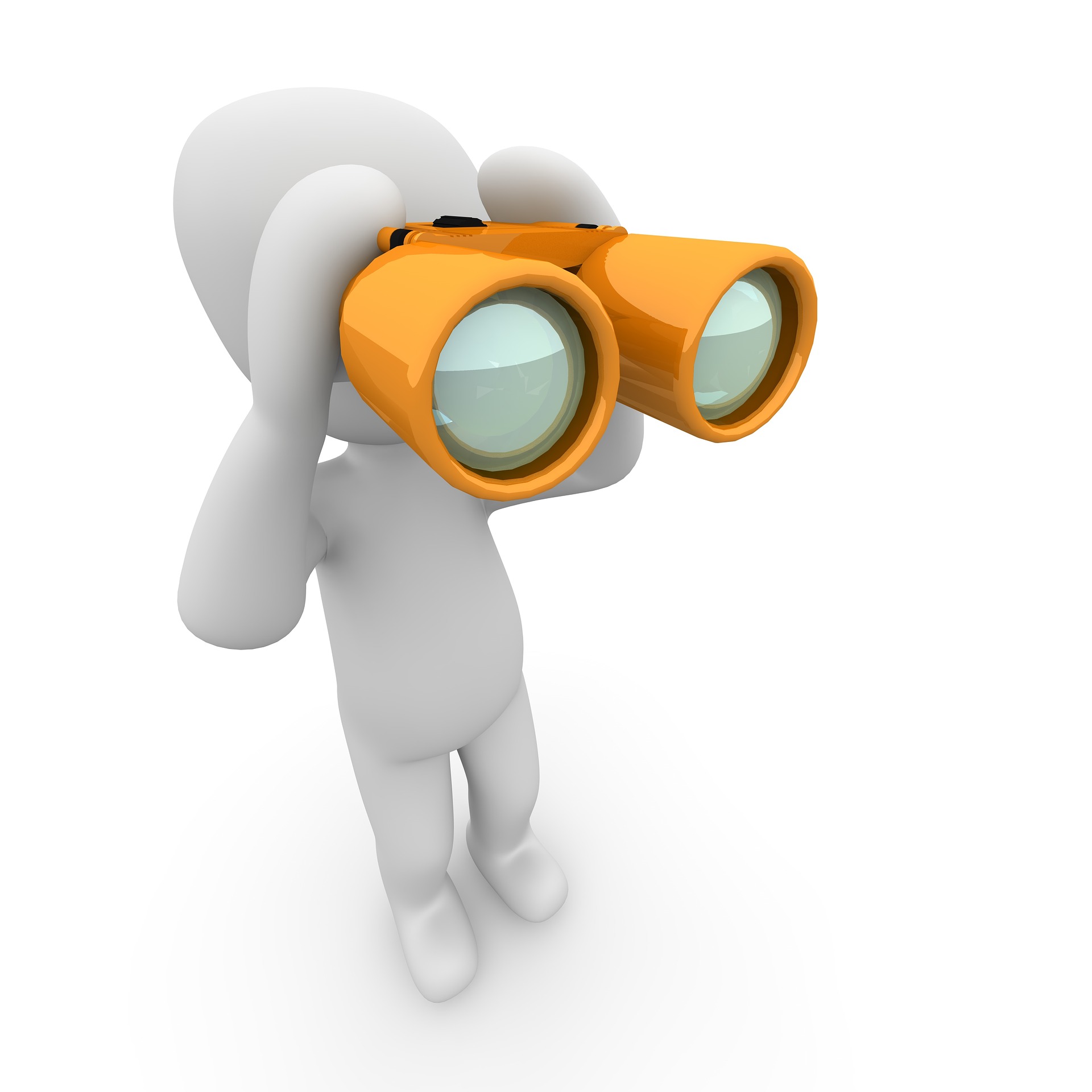
這個世界有兩種東西會不斷地被追問它自己存在的功用、目的、價值和意義。一個是人,另一個是哲學。
也只有這兩種東西會不斷地自問自己存在的功用、目的、價值和意義。
任何一個人,不管多麼地位高權重或微不足道,從現任總統蔡英文、前總統馬英九到街上的路人甲,在某時某刻、某種心理或社會狀態下,就有可能被問或自問:此時此刻,我有什麼用(我能做什麼)?我要達成什麼目的?我要達成的目的真是我存在的目的嗎?我又是為了什麼要去追求它們?我如何知道我追求的一切是有所指(有意義的),而不是荒謬的(無意義的)?問這些就是在問哲學問題。
世人(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都會問哲學問題,奇怪的是,多數人卻認為哲學沒有用。因此,有人常用哲學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多數人們常用哲學卻認為哲學沒有用。正是這個現象使得哲學也不得不努力向世人證明自己存在的功用、目的、價值和意義。可是,如果一個東西有用,它為何要不斷地去證明自己有用?哲學就這樣陷入一個弔詭的困局了。逃出這個困局的出路恰恰是向世人證明:正是哲學在不斷地證明它自己有用的時候,它才能展現它的功用、目的、價值和意義。哲學正是這樣一個特殊之物,它不是靠沉默有效率地達成目的來證明自己(如電腦、法律、公共汽車或任何其它工具),它是靠不斷地追問自己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在這一點上,人不也是一樣嗎?如果一個人在活著的時候,始終沉默而被世人遺忘,他甚至不曾自己追問過自己的功用、目的、價值和意義,他真的有用嗎?——他可能活得像工具。「工具人」恰恰是無用的,之所以無用不是因為他不能達到某個目的,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展現自己可以有其他目的並賦予其它東西目的,他的目的是被別人賦予的——他只是工具。
工具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能達成別人賦予它的目的,當它已達成目的而不再能重複地達成相同目的或朝向其它新的目的時,它就會被廢棄而無用了。人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人可以設立並賦予工具目的來證明自己有用;如果人像工具,從不曾設立目的並證明自己能設立目的而因此有用,那麼人就變成無用了。當人在設立目的並證明自己有用、有目的、有價值和有意義時,他就是在做哲學。所以,一個曾做或在做哲學的人,恰恰證明了自己身為人的功用,從而也證明了哲學的功用。一個從不曾做過哲學(問上述的哲學問題並給出自己的答案)的人,只是活得像工具,他也許是有用的工具,卻是無用的人。
人也就是哲學的存有者。或者更精確地說,人是追問哲學的存有者,或者說,人是不斷地透過追問哲學問題來證明自己有用的存有者。哲學的功用就在這裏得到證明:它是人用來證明自己之所以有用、之所以是人的必要工具。可是,現代社會是這樣一個讓人們異化的環境,使得哲學也不得不時時向世人證明自己有用來提醒世人:不要讓你身為人的存有者被異化成工具。
科學哲學有什麼用?

有些科學家會對科學哲學感到好奇。比較善意的會問:科學哲學有什麼用?能不能幫助科學研究?大多數科學家的態度是置之不理,當科學哲學不存在似的。科學哲學當然是哲學,它也面臨一般哲學的命運:要不斷地向世人證明它有用。可是,我想說:科學哲學也是科學(的一部分),這句話卻需要證明。
科學哲學包含科學方法論、知識論和形上學,也可以把科學倫理學納入,一個可能和現行倫理學或應用倫理學大異其趣的科學倫理學是可能被發展出來的。科學哲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從方法論和知識論的特殊性提供一個「科學的形象」(the image of science)。當科學家發現某個科哲理論提供的科學形象(例如波柏的「科學就是可否證性」)可以幫助他們區隔社會的魚目混珠者、或對抗異議的攻擊者時,此一科哲理論對他們來說就非常有用——但也僅止於此。又如社會科學家(例如STS學者,也企圖提供另一種科技形象)認為某些科哲理論(如借用維根斯坦哲學的孔恩理論、Mary Hesse的意義有限論等)對於支持某些社會科學或STS理論有用,因此也承認科哲有價值。但是,當其他科哲家質疑或反對那些科學形象,並提出競爭性的觀點時,科學家就會覺得科哲反而是製造紛亂的來源而敬謝不敏了。換言之,不是「科學哲學」做為一個學術領域而有用,而是其中的特定的科哲理論被用來支持特定的觀點、並對抗不同的觀點而有用,它們產生的功用是工具性的。
特定的科哲理論當然可以有工具性的效用,但那不是科哲做為一門領域的真正價值。科哲領域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認知知識與世界」的探討態度,應該被「召回」科學自身。之所以說「召回」是因為科哲和科學的近代歷史根源,這裏先不討論這個歷史根源。「認知知識與世界」是科哲在問問題時展現的一種探討態度:它的認知目的指向「世界」與「知識」本身,它想問:科學已提供我們認知世界的「知識表徵」是不是就是能提供我們想認知這世界的最恰當知識?這正是前文所謂的「科學知識論(含方法論)和「科學形上學」。
對我來說,孔恩的科哲理論最大的貢獻不是「科學革命三部曲模式」也不是「常態科學」的概念,而是孔恩透過科學史證明了科學哲學是科學的一部分。他主張,一方面在構成一個典範的訓練要素中包含「知識表徵形式」(如通則和模型)、以及「形上學的許諾」和「從共享價值」(做為方法學的判準);二來在科學危機時期,方法論、知識論和形上學會成為科學家爭議的焦點。也就是說,不同的典範,不只包含不同的科學主張和答案,也包含了不同的科學哲學觀點。可是,孔恩有誤的地方是他相信不同科學領域的常態科學時期,大多數科學家共享單一個典範,也就意謂共享單一套科學哲學觀點。如果現在沒有科學危機,也不是科學革命時期,那科學家就不會在意科學哲學,而將焦點轉向常態科學知識的累積。這樣的觀點有「實然」和「應然」(規範)兩種閲讀,這兩種閲讀都被費耶阿本所批評:實際上,許多科學領域在所謂「常態科學時期」不會只有單一典範,而是同時有多典範互相競爭;就「應該如何發展科學」的應然面而言,費耶阿本也主張科學家應該應用「增生原則」,以增加原典範理論的困難,發掘新又有價值的科學問題。我已經在我的2007年論文〈科學哲學在「科技與社會」中的角色與挑戰〉中作了相關的論述。我建議把費耶阿本的「理論增生」改成「理論版本增生」,把常態科學理解成「理論版本家族」的發展,如此一來,在同一個時期,會有多個「常態科學」(理論版本家族)同時發展。要如何增生和發展理論版本和理論版本家族呢?要從事科學哲學(方法論、知識論和形上學)的探討。從這個觀點來看,科學哲學當然是科學的一部分。
以上只是一種科學哲學家的一廂情願的想像嗎?不是。有太多太多歷史實例證明上述觀點。舉十七世紀笛卡兒機械論和牛頓的力學理論的競爭為例。固然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和重力定律使科學家可以精確預測天體位置,但是「重力」是個超距作用卻一直威脅牛頓的理論,因為當時大多數科學家相信作用一定要有接觸(亦即接受笛卡兒的形上學信念),牛頓後來解決此一問題的辦法是提出「歸納法」的方法論,堅稱他的定律是從經驗事實上歸納得到的通則(但實際上根本不是),而把笛卡兒的機械世界觀(形上學信念)打為無根基的「假設」。在十八、十九世紀這兩百年間,天文學和力學都是牛頓典範在主導嗎?不是,笛卡兒的思想在歐洲大陸有非常深遠的影響,雖然歐陸數學家不得不用牛頓的公式,但是一直在尋求如何規避「力」(含重力)這個似乎無法從感官經驗中歸納出來的概念,歐陸數學力學家使用光學發展出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最後發展出完全使用能量概念的漢彌爾頓原理,其間力學家不同的方法學和形上學信念交鋒歷歷在目。(參看我2004年的著作《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
很多人都同意文化會影響科學的發展。我也同意。我的看法是:「科學內部的文化」差異會使科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而「科學內部文化」又會受到「科學外部文化」的影響。從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科學哲學家的研究來看,西方科學確實有一種科學哲學式的探討文化——亦即他們會去思考和反省他們接受為「典範理論」的方法論、知識論和形上學問題——這是西方科學內部文化的一部分。如果這樣的文化真地有利於科學的多元化發展,台灣要不要學習?讓這種「科學哲學式的探討」內化為科學探討的一部分?這麼說當然不是要科學家去寫科學哲學論文或作科學哲學,而是說,台灣的科學家應該在養成過程中,被培養出一種思索「科學哲學問題」的好奇心,這有可能幫助他們(至少在「概念面」小幅地)修正典範理論,發展出不同的理論版本,而不是一昧只作「純實證的科學工作」。
「認知世界與知識」的態度、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科哲理論,才是我認為科學哲學(做為一個領域)最有(基本)價值、最有用的地方。
本文原載於「陳瑞麟的科哲絮語」,經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