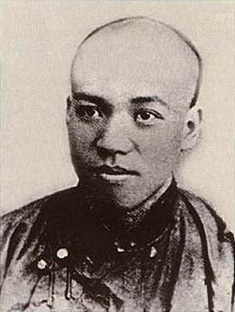薑餅人。曾經在溪州鄉公所服務,台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沒有畢業。志願是推廣台灣文學與文化。
簡單回顧一下白話文(註)與文言文的愛恨情仇。
中國在20世紀初發生了巨大的思維革命,而革命必須要有便利而具體的書寫文體,白話文就這樣登場了。
文言文在古代,則是一種書面體,也就是古人講話雖然和我們日常生活一樣嘰嘰喳喳的,但寫出來的文字就是有一定的規矩,例如「之乎者也」,以方便不同口語的人交流。
中華帝國疆域遼闊,透過一種既成的書面體來溝通,就可以建立起統一的官僚體系與穩定的文化思想。這套書面語,傳播到鄰居的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型構成了主流的東亞文化圈。
但是到了20世紀初期,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人被迫開始學習西方的知識,他們一方面設法翻譯西方的概念,比方說德膜克拉西(直譯漢語)或「共和主義」(和製漢語)之類的新詞彙。這些詞彙也強迫中國人要打開腦洞,去接受一個自己從沒想過的新世界,例如「外國的總統竟然是人民選出來的?」
創造新詞之外,當時的知識份子也開始試圖改造書面文體,為什麼要改造文體呢?因為過去古文有固定的套路,加上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大家寫起論文都很八股,一定要破題、承題,引經據典,所以在翻譯西方概念的時候,無論是辯論或者教學,使用文言文這種書面語就會很累、很累。
後來梁啟超等人在報紙上寫社論的時候,刻意突破這些傳統規則,放棄古文的抽象語法,加入大量西方語彙,讓文言文體例更具體、更流暢、更好閱讀,於是20世紀初期,梁辦了《新民報》,以流暢的新式文言文寫作,引發知識份子的模仿、學習的潮流,「新民體」就誕生了。
而新民體風行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愛上這種跳脫古文限制的文體,加上革命思潮趨近,在1910年代,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強調「我手寫我口」。在革命的風潮之下,白話文代表啟蒙思想,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新的書面文體。
所以白話文的誕生,並不是因為胡適厭倦了唐宋八大家,也不是不明白文學教育的重要。相反的,是為了「學習」的具體需求,就是為了傳播新的知識系統。
當時甚至有很多知識份子,如錢玄同等人,覺得改革文體還不能夠救國,必須「廢除漢字」才能真正的普及教育。當然這又是另外一題了。
台灣在日本統治初期,漢人知識份子也都是寫文言文的,甚至仕紳一開始不懂日語,都是寫文言文跟日本官員溝通,因為日本士族也都會寫漢語的文言文。但到了1918年後,有些接觸到中國五四思潮的年輕知識份子,例如賴和、張我軍等人,覺得「舊文人」思想保守、觀念反動,就開始嘗試用新的文體來寫文章。
但對於1920年代的台灣人來說,白話文也是另一種很陌生的書面語,所以寫起來都很古怪,還夾雜許多台語跟日語的語法在裡面,可以說是另一種生澀的書面語。有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提倡「台灣話文」,蔡培火提倡「台灣羅馬字」,但都沒有成為主流。
1930年代之後,對當時台灣年輕人來說,若要學習、交流新的知識,還不如用日語最快,所以日本時代中後期的知識份子,用日語來書寫思辯,是比用中國白話文更簡單的。
到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又被迫重新學習「白話文」,於是很多人像是小學生一樣重新用很簡單的「國語」語法來寫作,鍾肇政就是其中之一。
綜上所述,書面語演變的過程,是人們不斷想要找出比更方便的溝通方式。語言結構會自然調整以適應當代社會,而不是社會要去適應語言結構。語言第一要務就是實用價值,沒有符合當代實用價值的「語法」,本來就會逐漸被大眾捨棄。
目前文言文教育的需求,並不是為了學習新知與交流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民族情感及美學傳統這兩方面。
要把文言文視為美學傳統來討論也可以。那麼以這樣的美學論來說,同樣我們也要平等接受各種嚴肅的美學傳統,例如原住民族理應可以擁有自身的語文教材(課綱),大量納入自身的神話與族群文學等等。
我們要能接受原住民讀自己的「國文課本」?能接受各種美學傳統平行並立在學生面前嗎?屆時問題不再只是文言跟白話的比例,而是不同美學系統如何平等地傳遞給每位學生了。
附註:宋朝以後就有大量的話本出現,都是以方言來創作,算是白話的一種,但我這邊說的白話文,是取代文言文,藉由白話體例作為學術、新聞或正式文書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