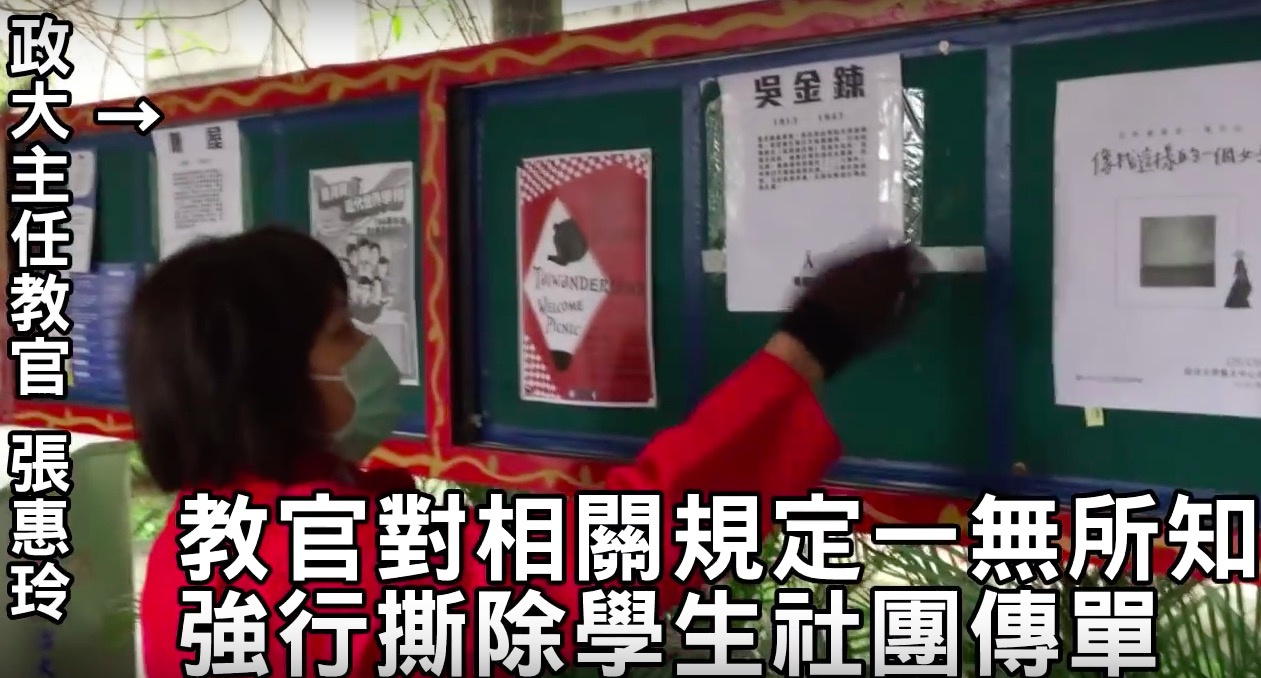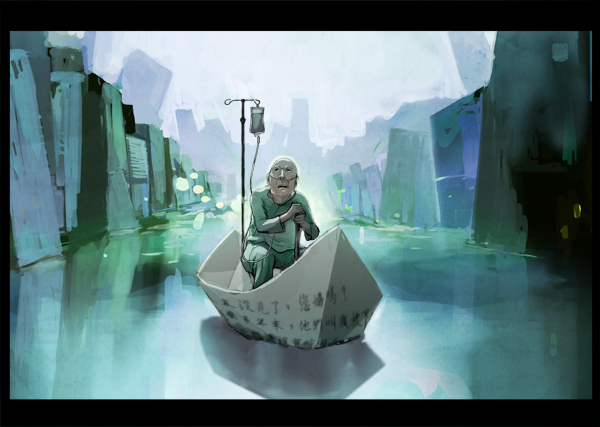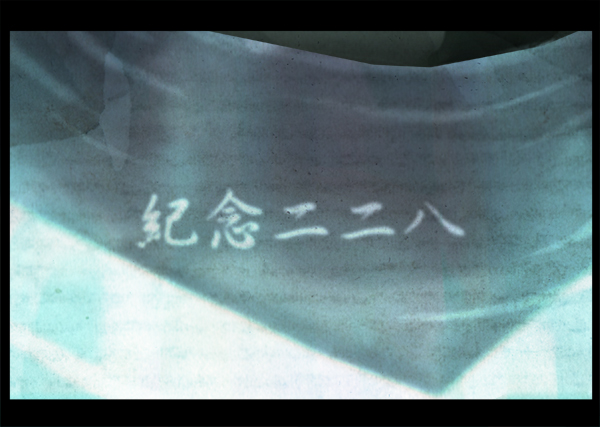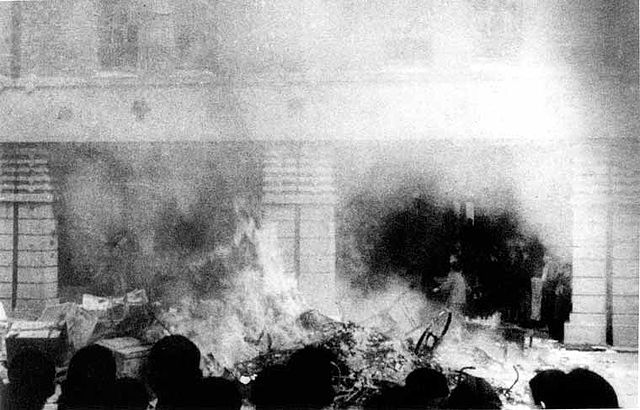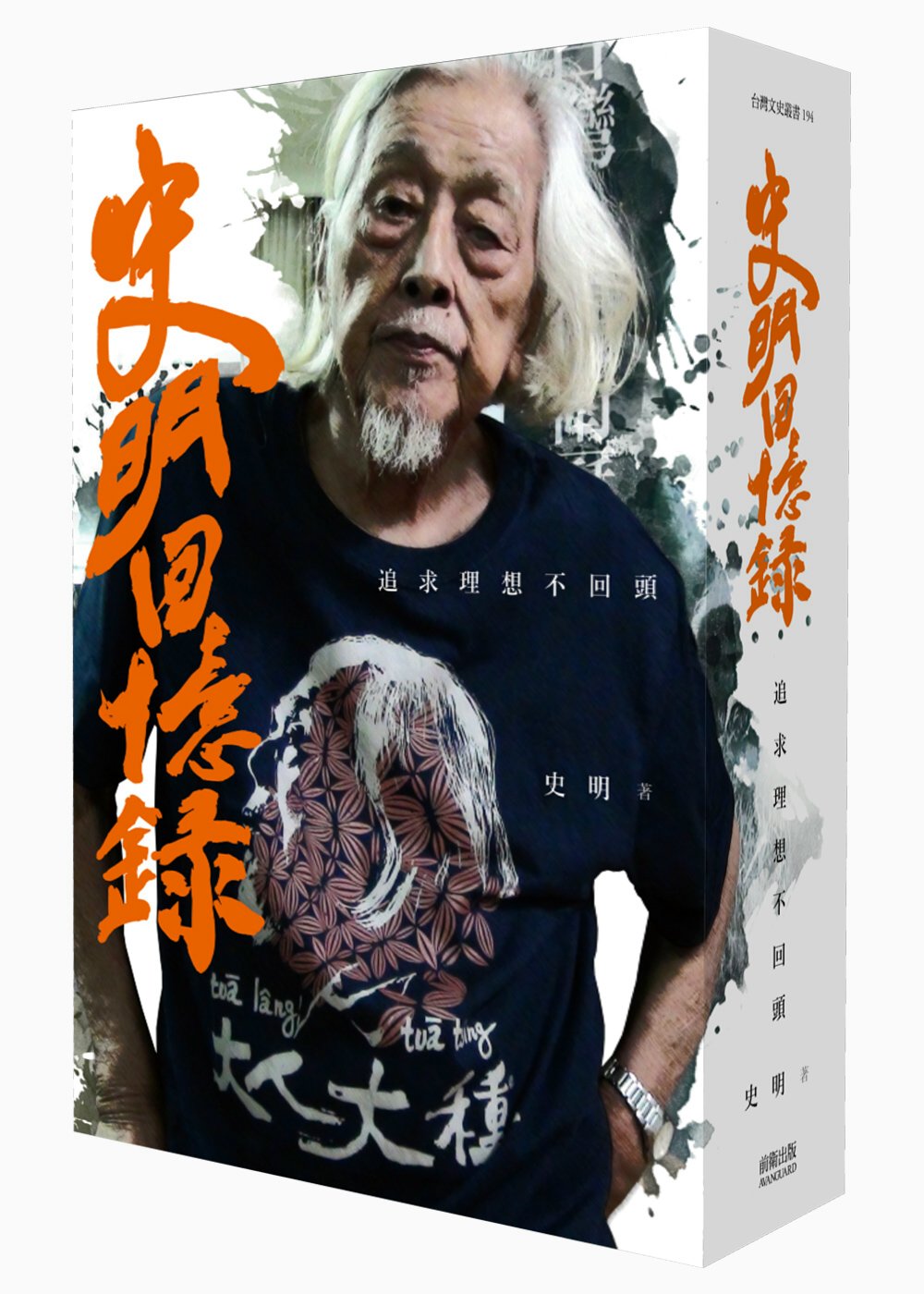很多人可能上了大學就沒有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經驗,但其實在台大像是校運開幕典禮,因為司令台上有國父遺像,在升完旗後向遺像行禮仍然是既定程序之一;或者像在總統府接受全國大專優青表揚,也是要先拜一拜才能領到當選證書。

碰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去年11月校運,當聽到司儀喊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決定看看法律學院領隊教授怎麼做就跟著做(其實心裡是有點偷偷期待他大概不會鞠躬),後來我就跟教授一樣以大約5度的角度微微欠身了事,這個動作與其說是對國父的崇敬,不如說是對大會的尊重。我想這還涉及一種從眾心理,當大家都不假思索的行禮如儀時,除非立場特別堅定,否則很少有人會選擇「跟別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