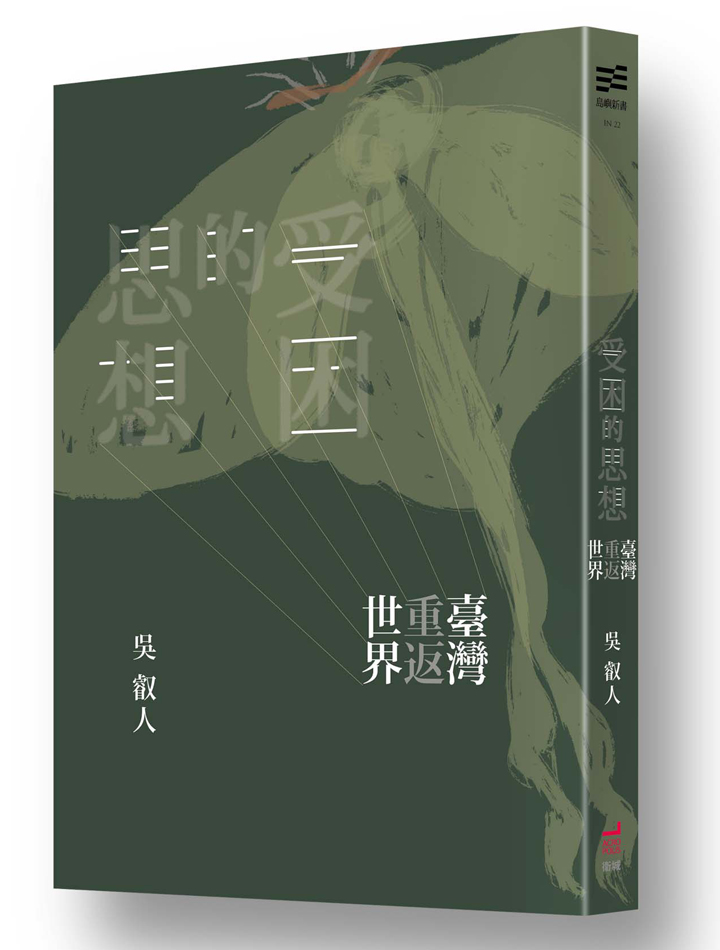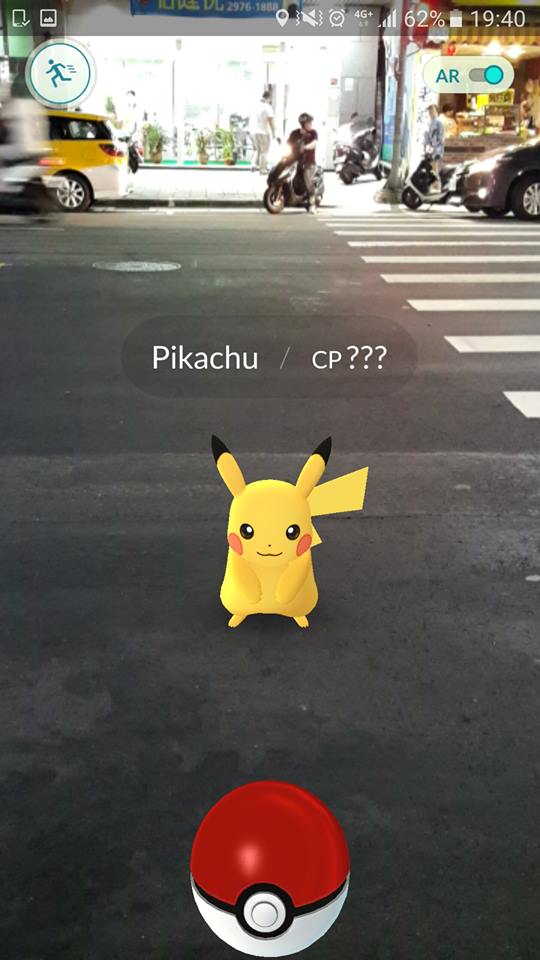《受》書彈奏的不是悲情哭調,因此不會耽溺於「亞細亞孤兒」影像。它尋求國際對話,首先是反省向來關於日本的「記憶政治」。吳叡人對「殖民地肯定論」是大搖其頭,卻深刻剖析臺灣右翼親日的歷史─心理淵源,據以批判仇日論者(包括自詡進步的文化研究者)的無識──過剩的歷史意識,過少的歷史知識。(頁115)
棄記憶政治,尋溝通理性
吳叡人深以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為念,希望台灣有識者能重返90年代臺灣民主高潮之際(甚至是1977年日臺人權運動聯手)為起點,期「被虐待者的解放,沈淪者的上升,以及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結合」成為日臺共識。準此,吳叡人肯定1995年〈村山談話〉的普世主義,而臺灣則可以賤民困境,用康德式的語言對抗國際無政府秩序的現實主義困厄──要求日本設立「日本和平基金會」,進行全面的歷史和解。由之,更不應低估中國公民社會網絡的崛起,於是康德永久和平論可以民主、普世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