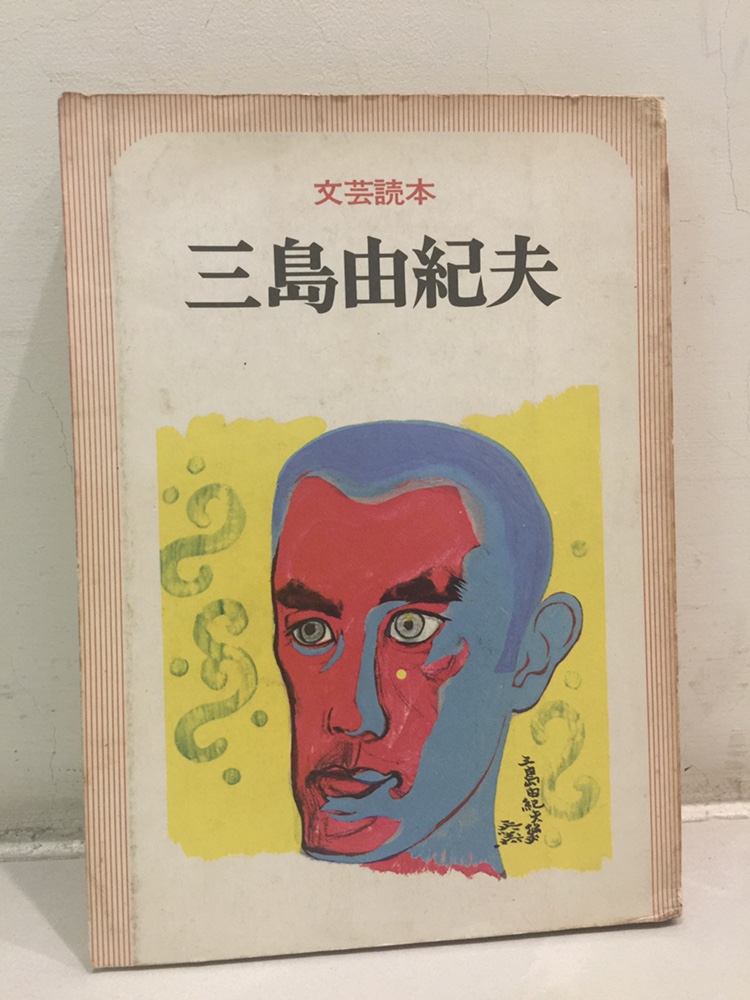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眾所周知,三島由紀夫於1970年11月25日,以極為慘烈的方式切腹自盡,成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事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已預先限定我們對其文學內容的探討。這就是說,當我們進入三島由紀夫的殉道領域之時,遍布在其作品中互為矛盾的自然觀念,很可能被其七生報國似的載道之言覆蓋。但是歷史研究做出證明,探索作家所抱持的自然觀念,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文學圖景,甚至得以深入他的生死觀,從中找到視死如歸的最終根底。就此而言,這樣的閱讀和探索,既有比較文學研究的廣泛意義,亦可作為另類宗教思想領域的途徑。

自然中的各種形態
以歷史性的角度來看,「自然」(Nature)這個詞,很早就出現在日本的佛教、儒教、神道、和歌、俳諧、繪畫等領域中,進入近代之後,它作為自然法、自然科學、自然哲學或自然主義等概念和專門術語,為使用者注入了活力,形成鑄就的用語習慣。日本作家繼承這樣的傳統概念或表現手法,豐富和深化「自然」的內涵。我們從蘭學家高野長英的《見聞漫談》(1835年)、《薩摩辭書》(1869年)、冷冷亭主人的《小說總論》(1886年)、岩本善治《文學與自然》(1889年)、森鷗外(林太郎)〈讀「文學與自然」〉(1889年)等文章,就可略知其源流。
一九〇〇年代,法國作家左拉的作品,給予世界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股強力的思潮也湧向了位處遠東的日本島國。當初,經歷寫實主義洗禮的先鋒作家坪內逍遙,便積極地迎向這嶄新的文學技法;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之下,小杉天外的《はつ姿》和永井荷風的《地獄の花》,就是這方面的成果展現。緊接著,福樓拜和莫泊桑等作品,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引介。譬如國木田獨步的《武藏野》(1901年)、《獨步集》(1902年)、《運命》(1903年)島崎藤村的《破戒》(1906年)、田山花袋的《棉被》、《鄉下教師》(1907年)等等,以及島村抱月和長谷川天溪在《早稻田文學》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都為自然主義文學擴展了論述的舞台。其後,正宗白鳥、近松秋江、岩野泡鳴、真山青果、小栗風葉等作家的努力下,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更蓬勃地發展了起來。進入嚴苛拑制言論自由的一九三〇年代,劇作家唐木順三發表〈關於現代日本的自然與道德史的考察〉(1932年)、小說家寺田寅彥的〈日本人的自然觀〉(1935年),可視為對自然主義文學的深刻自省。
在日本人的定義中,歐洲文明的基調向來是征服自然的文明,亦即向自然挑戰的文明。然而與此相反,日本文明則是重視與自然文明共生,順應自然、尋求調和(和諧)的文明,這樣的觀念和認識佔著主導地位。諸如以小泉八雲為代表的外國學者,也都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甚至是對自然的讚美者。1968年5月13日,著名西班牙文學家迪耶斯・德爾・科拉爾就曾與三島由紀夫以〈東與西:接觸與交流〉為題進行深度對談。他在對談中提及:「在我看來,竹筒裡的插花與其他鮮豔綻放的花朵,是同整個自然相聯繫著的。此外,它也在呼籲人們享受擴展於田園的生命和豐饒現象。進言之,日本人的整個生活是置身在自然的變化豐富的律動之中。人們為了欣賞二月裡的梅花、四月的櫻花、五月的杜鵑花和紫藤花、夏季的蓮花、十一月的菊花和紅葉,竟然可以捨棄城市提供的便利,奔向偏遠的地方旨在要置身感受季節的色彩氣息,這樣看來,他們彷彿整個生活就這樣充滿著一種絕妙的芳香……。」他進一步指出,歐洲的家庭和團體的飾章多半是猛獸或猛禽類,而在日本,日本皇室的家徽是菊花,德川的家徽是三葉葵,三島由紀夫(本名平岡公威)平岡家的家徽則是圓形蘘荷,亦即以植物占絕對多數。然而,這位西班牙文學家在讚美日本人與自然共生的同時,仍然不忘提出警告,人類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好處,亦得付出慘重的代價。各種產業造成的公害污染著大氣、河川和海洋,為了擴大和建造住宅,開發產業道路和促進觀光,大片山林遭到砍伐、嚴重破壞了日本的自然景觀和生態體系,自然的風景之美,隨著產業的大幅開發迅速消失。例如,國木田獨步於大正時期流連忘返的「武藏野平原」,在二戰之後,已淡出了民眾的生活視野,只留下空盪盪的回憶。換句話說,現代人已清醒感受到這種危機的到來,他們察覺到自然環境正陷落在無機的技術文明的沙漠裡,枯竭的生命自然本能地發出吶喊,憧憬野性和尚古主義的渴望,成了他們精神深處的鄉愁,甚至是出自生理上的必然需求。
野性的復歸與新生
可以看出,三島由紀夫很早就表示出他對於「野性」的復歸。1948年5月25日《國學院新聞》上,刊載了讀者對於「野性」的意見。林房雄和龜井勝一郎等作家,對「大學」這個公共領域的學習環境,表達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它應該發揮著旺盛的野性。三島由紀夫就直接表示:「我往返於本鄉(東大校園)那段期間,就覺得大學新聞這種東西實在太空乏了,連把它拿起來看的興致全沒了。我覺得它散發著學院式的臭氣、犬儒主義的臭氣,知識分子的臭氣,完全沒有青年應該具有的強烈的野性。直白地說,失去野性的大學新聞,還有什麼用處嗎?總而言之,沒有野性的理想主義,等同於沒有知性,它比虛無主義還要糟糕,簡直令人欲嘔的。」正如日本文學評論家千葉宣一指出的那樣:三島由紀夫的「野性觀」,應該不同於A・湯恩比所謂的野性的文明,而是說明對所謂文明的野性的同感,他的志向並未停留在觀念性的憧憬上。毋寧說,三島由紀夫是個怪才,他把這個觀念重新改造,也就是把自己引導向肌肉所思考的肉體的原始主義世界。為了將思想肉化成第二本能,他誘使自己做健美運動,終於從以思考的立場來行動的文人,向背向自己的本質,以行動的立場來思索武人的方向轉變,這如同成為奧菲士教徒展開的狄俄尼索斯的祭典一樣,把自己引到狂喜的頂點,並在那神聖的瘋狂中不斷地成熟起來,然後疾步地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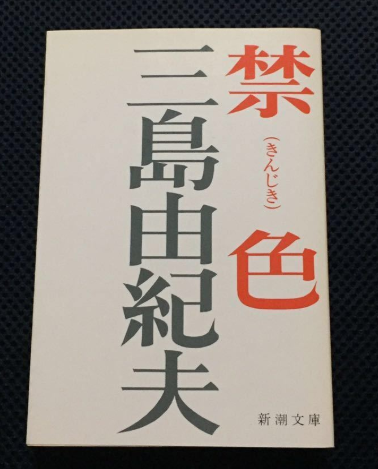
三島由紀夫對此做出回應,他發表〈現代小說能是古典的嗎?〉一文,旨考察日本與自然的關係。另外,他在小說《禁色》中,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在日本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原本就有希臘式的親和性,有多神教和泛神論的東西,而從更嚴峻的風土中產生的佛教教給我們另外的同自然發生關係的方法,開闢了走向超越藝術的道路。這宛如沃爾松格敘述有關文藝復興前的北方藝術,北方的神祕主義只不過是『與深刻意識到世界的不可知性的東方神秘主義相反,北方人感到自然與自己之間只是有一層薄紗』。而且,這種薄紗就是北方的霧。在這種情境下,或許我們可以援引哲學家和辻哲郎的《風土》見解,以此做出反差的佐證:「在西歐,冬天的溫度比日本要低得多。這一自然的順從意味著自然的單調。在這裡,不存在我們通常所感受的那種冬日風情。例如,寒風滲入身體帶來嚴寒的同時,我們還有到向陽處取暖的樂趣;一邊思忖著漫天大雪將積起一片鬆軟的風景,次日卻在晴空的朗照下悠然聽聞雪花化成的水滴聲。這一濕氣、日光和寒冷的交響樂只憑寒冷是無法產生的。可以說,西歐的冬日風情只是表現在了人為性的東西上,如室內、爐邊、劇場、音樂廳、舞廳。這無疑是冬天激發了人的主動性。」但值得注目的是,三島由紀夫的自然觀,並非是從日本自然風土的直接體驗出發的,相反地,他卻是逆向而為,以形而上的自然(存在)觀,即用希臘式和印度式的抽象類型為自己的美學觀開闢道路。順便指出,三島由紀夫對於輪回轉世思想的關注,其接受希臘思惟的影響應該更先於印度思惟的影響。
禁色中的顫慄和死亡定向
嚴格講,在三島由紀夫的美學觀中,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缺陷和矛盾。正如他在《禁色》中所言:「……在自然與藝術作之間,存在著一種親近世間卻又隱微的背離之心。也就是,藝術作品對於自然的逆反,類似女人委身於他人卻不貞的意志。儘管如此,再沒有比像近似尋求自然精神的人工性的精神那樣重要的了。所謂精神即如自然的物質把自身隱藏於有石頭、樹木、泉水的庭園之間。這時,不論多麼堅固的物質,被精神從內部所侵蝕。物質就這樣在各個角落受到精神的凌辱,石頭和樹木以及泉水原本的物質作用漸漸被削弱,從而成為某種營造庭園的沒有柔軟目的的精神之永遠的奴隸。」或許,三島由紀夫這段話與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學》有幾分相似之處,其實更準確地說,三島由紀夫對於自然的認識,帶有明顯書齋型作家的印記。關於這一點,對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了解甚深的日本文學史家唐納德・基恩可以為此佐證。唐納德・基恩翻譯過其《薩德候公爵夫人》,為了譯出豐饒之海四部曲之一的《奔馬》,事前做過多方查考,於1966年8月22日起連續四天三夜,尋訪了奈良櫻井市的大神神社,聽取了中山宮司為他的講解。他回憶與三島由紀夫一同旅行的情景:「那時候,我和三島前往奈良採訪兼旅行。然而,我為三島對於樹木和植物花卉以及動物的知識如此貧乏,不無感到份外驚訝。在該神社的後山裡,三島向一位年長的庭園師匠問道,在他眼前的是什麼樹木?那名匠師吃驚地回答:那是松樹。接著,匠師可能認為三島問的是松樹的種類,於是又換個說法:這棵叫做雌松。三島一隻手拿著鉛筆,認真地探詢道:這全是些雌松,而沒有雄松,怎麼能生出小松樹來呢?當天夜裡,傳來青蛙的鳴叫聲,三島仍然不懂,直問那是什麼聲音?

然而,表面上看三島由紀夫是個意志剛強的作家,其實在內心深處,他亦有猶豫不決的一面。在他尚未在自決取義之前,已經和美國的出版社簽定四卷本《豐饒之海》的合約,有著明顯的保障,但是他仍然擔憂著,在其死後這四卷本的出版事宜是否中止?對此,唐納德,基恩在一篇文章中說:「一個為了祖國的墮落而憤慨,盼望著藉由最戲劇性的難以言喻的忠誠姿態,極欲喚醒同胞實現日本的理想的武士,為何對其作品的英譯本如此操心呢?」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三島由紀夫是個雙重性格的人?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此勇猛剛健,其實他總是以耀眼的表象來掩蓋那短暫的軟弱嗎?尤其,就三島的死亡美學而言,讀過英譯本《太陽與鐵》的小說家G・比達爾卻持相反的見解。在他看來,三島由紀夫的死亡,與其說是日本式的死,不如說是世紀末西歐式的死,因為他是透過對肉體的信仰把生活藝術浪漫化的行動者,在其文學裡,看不到本質性的發展。從寫作本質上說,他也是對語言缺乏關心的作家。然而,美國歌倫比亞大學L・莫利斯教授則為三島由紀夫的隱諱申辯。他說,儘管三島反對二戰後的國語改革,是個積極恢復死亡語言和漢字的作家,但作為善於言語表達的工匠,三島的確探索了日本語文學性的萌芽。撇開這樣爭鋒相對的爭論,或許三島的戲劇作品,不像其小說中的機鋒那樣充滿爭議,他的《近代能樂集》英譯本受到較多的肯定。這部作品不僅搬上美國紐約的舞台,還有由先鋒派劇團在德國、澳洲等世界各國近三十個國家的主要城市上演,可謂把其名聲推向了世界的高峰。

如今,三島由紀夫死後已快半個世紀了,他的悲壯之死或說奇詭之亡,仍然延續著好奇者們對他的探究,但我們終究不是共時性的見證者,頂多只能藉由其文本做出各種想像性的評述。在此,我們不妨引述唐納德,基恩的題為〈三島由紀夫〉悼詞,因為他與三島有深厚的情誼,對其文學作品的闡揚,發揮著巨大作用。唐納德・基恩這樣說道:「三島在其體力和精神達到顛峰時決然辭世了。他表現出這樣一種政治態度:試圖喚醒日本自衛隊去改變物質繁榮下,缺乏精神性的日本社會。這種自我放任的表現方法,與他那顯赫的死亡是不相稱的。在他心裡,或許還心存一絲希望,可以改變日本的政治,不過正如他的希望一樣,如今已然死去,他戴著多年前就已戴上的假面具告別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