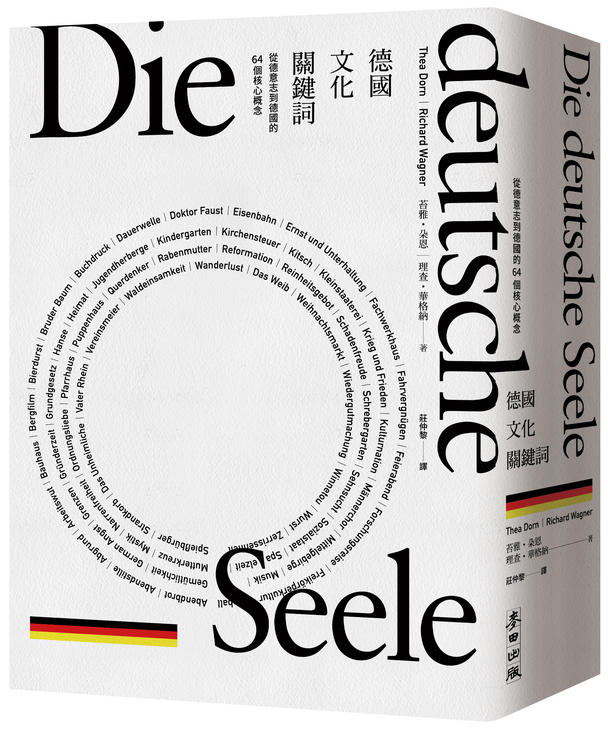書名:德國文化關鍵詞: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
作者:苔雅‧朵恩、理查‧華格納
譯者:莊仲黎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7/0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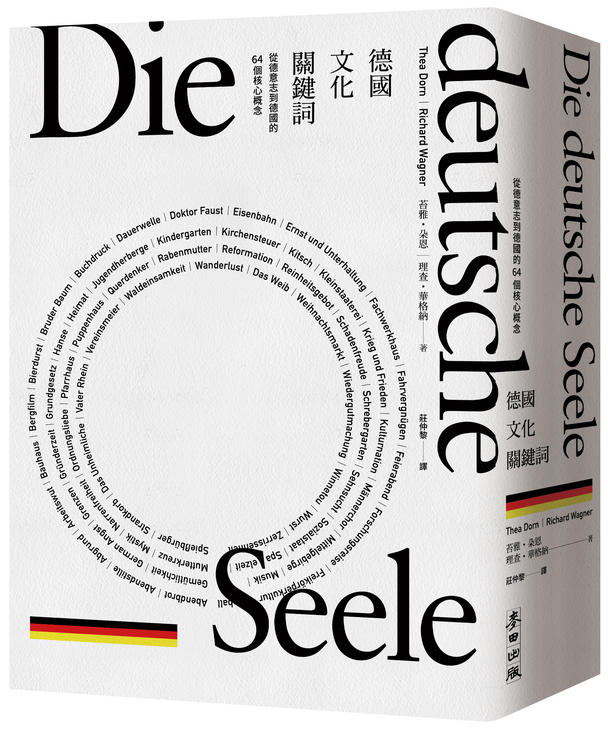
24.基本法(Grundgesetz)
生活在困苦的時代,挨餓是主要的問題,左派劇作家布萊希特對此曾有很露骨的說法──生活的一切只為填飽肚腹,只為免於飢餓。二戰結束後,德國女詩人瑪莉.卡許妮茲(Marie Luise Kaschnitz, 1901-1974)在面對被戰火摧毀的家園時,則寫道:「當棲身的房子已塌毀時,我們只能守住那些僅存的東西,例如,孩提時期在山間小路遊盪時,那棵長在路旁的綠樹,或走在深夜的街道上仰望星空,瞧見自己認得的星座依舊出現在頭頂上方相同的位置。在家屋的瓦礫堆中搜尋,既令人厭煩也沒有意義。然而,失去的房宅難道只是由泥漿、黏土或石頭構築而成?它不也代表居住者的自信與夢想?」
德國在一九四五年簽署的投降協議,等於宣告了國家的政治破產。當時的德國諷刺劇演員,曾把美國、英國和法國這三個西方強權在西德的軍事占領區戲稱為「三個區域」(Trizonesien),至於其餘的部分則已被蘇聯紅軍占據。德國投降後,西德一些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很擔憂德意志民族的未來,他們認為不能一直陷於美蘇兩強對立的僵局當中,因此,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結盟,並藉此重獲國際社會信賴。此時,西德的敵人是西方盟國的舊盟友──史達林,當然,還有從前的納粹。在美蘇冷戰時期,西德由於受到美國強力支持而迅速從二戰的挫敗中東山再起。
一九四五年納粹投降後,年事已高的普魯士歷史學家弗利德里希.麥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曾針對德國遭逢的空前災難發表看法;隔年,著名的左派政治家恩斯特.尼基許(Ernst Niekisch, 1889-1967) 已經看出對立的西德與東德就是德國未來的命運座標;一九四七年,德國記者暨作家艾力克.雷格(Erik Reger, 1893-1954)在柏林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創辦《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並喊出「關於未來的德國」(Vom künftigen Deutschland)這個口號。他當時表示:「我們從前急於讚揚的二十世紀已經過了將近一半的時間。從一九一四年至今(指一九四七年)所發生的一切,將會影響接下來的後半世紀。對於全世界來說,關鍵問題在於,德意志民族是否能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做出了不起的貢獻,以彌補前半世紀種種不光彩的表現。」
誠如雷格所言,國際社會因為德國人在戰後積極展現對歷史負責的熱情,而願意給這個民族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任何人都可以在德國人的傷口上撒鹽巴,不過,西方陣營為了對抗強大的蘇聯,在考量冷戰的國際局勢後,必須儘快與德國化敵為友。因此,德國人此時早已不是敵人,而是盟友。
一九四八年,十一位西德的地方領導人曾公開表示,他們不希望看到德國的分裂,不希望在美、英、法三國的占領區成立新的國家,而僅僅要求這些西方盟國,先成立一個擁有統一行政權的政府。當時這些西德的政治人物相當憂心,西德與東德之間不斷深化的分裂,會被合理化為不可改變的政治現實。美國占領區的主席魯修斯.克雷將軍(Lucius D. Clay, 1898-1978)則對此有所評論:「這是一個特殊的狀態⋯⋯,我代表所有戰勝國授予德國人全部的政治權利,然而德國人卻聲明,他們並不要求全部的政治權利。」這位美國四星上將在美國占領軍政府所在的法蘭克福I.G.顏料企業大樓(I.G.-Farben-Haus),召見巴伐利亞、不來梅、黑森、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等邦首長,並當面加以訓斥,而後還不滿地對外表示:「德國人決心貶低他們真正的支持者與朋友──美國人⋯⋯,如果我們只在西歐而不在這裡,德國人早就變成蘇聯人了!」
如此躊躇不決並遭受外國勢力責難的德國人,開始為重建新德國跨出第一步。問題跟著來了:戰敗的德國人憑著當時的實力,能重建什麼樣的德國?或者,更關鍵的問題是:德國人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被准許重建什麼樣的德國?一九四九年,德國建國在即,沒有什麼比憲法的制定更急切了!基於保密考量,當時的憲法制定者全聚集在波昂這個偏僻的小鎮上開會。經過一番討論之後,他們不只確定眼前發生的一切已無法挽回,而且接下來德國將會如何發展也已昭然若揭!他們很清楚,二戰後制定西德基本法的波昂,絕不是一戰後制定威瑪憲法的威瑪,有鑑於威瑪共和政體的失敗,它也不該變成威瑪。
首先,西德的「三個區域」及東德蘇聯占領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都因為德國的分裂而自認遭受嚴重挫敗。在蘇聯占領的東德,俄共頭子史達林透過蘇聯占領軍政府頒布一套法令,並成立「烏布利希小組」(Ulbricht-Seilschaft)。「必須使民眾產生民主的印象,但一切必須全掌握在我們手中。」這就是首位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當時的政治運作原則。至於西方陣營的西德所產生的政治領導階層,則持續致力於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擴展。
當時東、西德的差異也反映出美國與蘇聯這兩個超級強權的不同。經由這樣的對照,德國人再度意識到德國與西方的長期歷史淵源,當普魯士因為納粹垮台而沒落之後,德國也開始回歸西方的懷抱。德國從前曾透過普魯士而在地理與精神上獲得向東擴展的機會,由於普魯士精神已被人們簡化為軍國主義,因此,普魯士必須為整個德國戰敗的悲劇負責。與普魯士切割,並把一切的過錯推給普魯士,是一種非常簡便而聰明的作法,如此一來,德國就可以不用承接所有納粹的舊帳。
一九四九年,一些西德的重要人士在制定基本法時,雖然立法的自由受到限制,不過,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間;西德基本法的起草者當時也這麼認為。這些法律專家在訂定基本法的條文時,把分裂的德國當成暫時的狀態,並未視為最終定局,因此,他們不稱這份過渡時期的法律文件為「憲法」,而是「基本法」,而且還深思熟慮地在序言中附上聲明,為日後德國的統一與政治常態的回復預作準備。因此,這部基本法的序言已預先設想往後冷戰結束時,德國將面臨新局勢的衝擊。其相關內容如下:
「德國人民意識到在上帝及人類面前的責任,意志堅定地捍衛民族與國家不被分裂,在團結的歐洲國家裡,作為平等的一員並致力於世界和平。巴登、巴伐利亞、不來梅、漢堡、黑森、下薩克森(Niedersachsen)、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drhein-Westfalen)、萊茵─普法茲(Rheinland-Pfalz)、許列斯威悉─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巴登─符騰堡以及符騰堡─霍亨索倫(Württemberg-Hohenzollern)等邦的德意志人民為了國家生存,並為了在過渡時期形成新秩序,根據憲法賦予的權限,通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此基本法亦適用於那些拒絕參與的德意志人民。所有德意志人民將繼續被賦予任務,以獨立不受干涉的自決權完成德國的統一與自由。」
一如人們在一九四九年制定的西德基本法的序言所讀到的,這部德國國家的根本大法攸關德意志民族的統一與國家的自由,它反對分裂並賦予人民自決的權利。此外,這份序言還為德國人民從一九四五年的無條件投降中爭取到一些權利與自主的空間,並展現戰後德意志民族堅定的自信心。四十年後,蘇聯老大哥崩解,德意志民族獨立自主的自決時刻終於到來,德國的統一不僅時機成熟,它所象徵的歷史意義更為重要。由於西德在一九四九年制定基本法時,已預設日後兩德的統一,因此,對於一九九○年德國的統一來說,這部基本法開頭的序言與條文內容並未過時,仍能切合當時的政治現實,並不需要做大幅的增刪和修改。基本法的本文規範德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序言部分則在於維護德國國家至上的利益。一九九○年德國正式統一時,經過修訂的基本法序言如下:
「德國人民意識到在上帝及人類面前的責任,在團結的歐洲國家裡,作為平等的一員並致力於世界和平。德意志人民根據憲法賦予的權限,通過這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柏林、布蘭登堡(Brandenburg)、不來梅、漢堡、黑森、梅克倫堡─前波緬(Mecklenburg-Vorpommern)、下薩克森、北萊茵─威斯特法倫、萊茵─普法茲、薩爾蘭、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特(Sachsen-Anhalt)、許列斯威悉─霍爾斯坦及圖林根等邦的德意志人民,已經透過獨立自主的自決權完成德國的統一與自由。這部基本法對於所有德意志人民一體適用。」
一九九○年完成統一的德國一致通過這份基本法的序言,這不啻意味著戰後的兩個德國──前西德與前東德──已不再隸屬於美國和蘇聯,它們已經由順利的政治整合而確實歸屬於德國人民。即使某些西德與東德的思想家曾唱衰這個新德國的未來,但它的文化面貌並未因此而頹敗崩壞,反而靠著人民無比的意志力完成內在的蛻變。從前,有一位西德總統被問到關於熱愛祖國的問題時,這位政治家還必須顧左右而言他,俏皮地回答:「喔,我愛我的太太!」現在,那樣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了!國際的政治氛圍已再度允許德國人可以表現自己的民族特色。
德意志民族或許不優雅,不過卻堅定地支持自己的民族精神。
根據西德的基本法,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關於這一點,西德和其他國家並沒有什麼差別。至於西德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國內那些具有批判性格的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在過去幾十年間不斷對西德社會進行批判,他們在乎的不是「誰比較敢說?」而是「誰提出較多的警告?」他們深信,自己已經在德國人的本質裡發現那些導致災難的因子,並因此而認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特質都是荒謬可笑的。後來,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文藝批評家喬治.盧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也加入這批德國左派文人的行列,一起走在這條思想的歧路上。名氣響亮的盧卡奇還斷然地把德國豐富的哲學思想歸入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us),他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理智的毀滅》(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其中一段內容便可證明他的愚昧:「一方面,英國與法國人民在政治改革層面已領先德國一大截,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末所發動的民主革命已獲得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位於德國東邊的俄羅斯民族由於較晚發展資本主義,因此,人民的民主革命能夠順利轉化為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成功地避免德國人民至今仍在承受的痛苦與衝突。」

當時德國左派知識分子的思維終究禁不起時代的考驗:當一九八九年街道上的東德人和電視機前的西德人一致支持東、西德統一時,全世界只有這群自命為言論捍衛者的人對這種現象感到驚訝不已。這些文人空有犀利的文筆,卻已無法對此出言反駁。一九六八年法蘭克福的學生運動曾喊出「人行道下方是海濱的沙灘」(Unter dem Pflaster liegt der Strand)這句廣受歡迎的口號,二十幾年後,事實的發展卻凸顯這句口號的謬誤。誰說,人行道的下方並不是海濱的沙灘?
相較於德國民眾的「不理性」,這些「特別理性」的左派人士仍不甘示弱,後來便展開反擊。在柏林圍牆拆除後,他們聚集在一家位於柏林新市中心的劇院食堂裡,公開指責德國人民背叛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只因為德國人民已無法再撐過長達二至三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已無法放棄以資本主義作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在這個左派文人圈當中,以東德社會主義文學家史提凡.海姆(Stefan Heym, 1913-2001)和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 1929-1995)的發言最為熱烈。
這群左派知識分子曾短暫地針對一些關於德國統一的議題發表意見:他們認為,應該重新制定德國的憲法,或至少應該改換德國的國歌,畢竟西德在一九四九年時所作的相關決定,東德人民並沒有參與。根據他們當中某些人的想法,德國的國歌應該改成一首由布萊希特作詞的兒童頌歌(Kinderhymne):「既優雅又辛勤,/既熱情又理智,/美好的德國繁榮昌盛,/如同另一個美好的國家。」
然而,德國左派文人這些主張只是讓自己再次出洋相罷了。他們在二戰後,選擇站在與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立的立場,全力為東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做政治宣傳,並取得這個社會主義政權的認同。因此,當西德強勢地統一東德時,他們對於以西德為正統的新德國憲法和國歌已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他們一向把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作復辟的封建政權,而東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雖然政治方向正確,卻還是個需要照顧與呵護的孩子,在初期的發展階段難免會暴露許多缺點和弊端,就像孩童會生病一樣。持有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就是戰後入籍瑞典的猶太裔德國文學家魏斯,他曾直言不諱地指責西德的陳腐與墮落。相較之下,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的態度就顯得比較模稜兩可,他曾以批判性眼光觀察東德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也曾經坦言,東、西德的統一將會引起一些問題,無法一帆風順。曾在青年時期被蘇聯占領軍的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八年有期徒刑、而後逃往西德的作家華爾特.肯波斯基(Walter Kempowski, 1929-2007)則從頭到尾一貫地維持批評東德的態度。

這些左派自由主義分子並不想走回頭路,他們既不認同德意志帝國,也對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以為然。那麼,他們是否真的為了制伏資本主義陣營的敵人而前往莫斯科?不,他們不費力氣地將自己定位為世界主義者(Kosmopoliten),並與所有發生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在面對實際的政治角力與衝突時,他們總是以和平主義者的姿態一味地反美國、反宗教、反以色列、反資本主義、反西方,實際上,這群知識分子根本是在反對西德與西方世界的連結。
戰後的西德若要與西方連結,就必須在歐洲打破與法國以及英國的政治隔閡,因為,光有美國這位盟友,西德仍無法在國際間生存,這是可想而知的事。與西方連結也同時表示,位處中歐的西德必須在冷戰時期的兩大對立陣營中選邊站,必須放棄向來所扮演的、協調工業先進的西方和斯拉夫東方的中介角色。西德與西方的聯合,就如同回歸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地緣政治形態:神聖羅馬帝國在中世紀是歐洲政治運作的主要政體,因此,人們可以從中了解它當時對於歐洲的真實意義。神聖羅馬帝國以一種歐洲的價值模式存在上千年之久(西元八○○年至一八○六年),它與西歐國家彼此依存互動的方式,其實就是戰後西德如何建立常態對外關係的示範,而不是十九世紀以來由普魯士所主導的、與西歐保持距離的外交政策。
末代德皇威廉二世的威廉主義並沒有把德國推向光輝的歷史巔峰,而是讓德國走上一條大錯特錯的國家發展路線。在德國統一後的一九九○年代初期,許多國際人士都認為,有必要對德國再三告誡,以免這個國家又回到納粹第三帝國的粗暴狀態;當時,只有一位法語作者獨排眾議,把統一的新德國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再起,他就是阿蘭.曼克(Alain Minc, 1949-)。這位法國猶太裔企業家暨作家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新的中世紀》(Le Nouveau Moyen-Âge)這本著作中表示:「法國人對於德國的再起感到憂心忡忡,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性質。他們把德國和俾斯麥的治國模式畫上等號,這種觀點是不恰當的,其實,這個國家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也就是類似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運作模式。東、西德在一九九○年統一後,德國原則上已經排除『往斯拉夫東方發展』的傳統普魯士策略,而是重新固守自中世紀以來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中歐。這個地理區塊不僅涵蓋從前德意志帝國的國土,甚至還擴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匈帝國疆域」。
一個國家的憲法同時也是它社會狀態的彰顯。與西方結盟仍是統一後的新德國最重要的國家特點,德國也透過基本法所制定的內容,確保這條政治路線的延續,而且基本法也因此而獲得更深層的意義。至於傾向往斯拉夫東方發展的普魯士,現在頂多只被視為一個位於古羅馬帝國邊境防線之外的日耳曼政治體。
德國可能出現的危險,並非如國際人士一再提起的第三帝國的重現,而是與西方連結的斷裂與放棄。現在的德國為了表明自己是西方的一分子,早已放棄德意志帝國──這個遲至十九世紀後期才形成的民族國家(相對於法國而言,成立時間較晚)──所遵循的向東擴展的政治方針。德國社會哲學家赫穆特.普雷斯納(Helmuth Plessner, 1892-1985)也曾指出,普魯士當時所主導的對外策略對於德國的發展而言,是一種特殊路線,而非常規路線。(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