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法律系畢業,立即改念歷史。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網址:blog.roodo.com/chita
歷史是段無垠的鐵道之旅,但每逢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的N十年乃至百年紀念,就是停歇暫憩的大站月台,爾後再思考何去何從的大哉問。於是屆滿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除了追思會、音樂會、史蹟巡禮、研討會、書籍出版、藝文展示……等例行活動,是否還有新義初創,眾人都引頸企盼或狐疑之中。
話說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人於1987年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透過演講、遊行打破島嶼長期的緘默;但二二八可以公開暢談並全面研究,已是1990年代之事。暢談意味著既有的二二八出版物全面解禁,也代表學術研究逐漸取代意識形態的吶喊。二十多年來,潛心其中的學者專家藉由檔案解讀、口述積累,以及外國檔案、文書、報章的出土,凡此已闢出多重路徑,然而放眼今日,籠罩於島嶼上空的二二八陰霾似未清除,顯見學術新徑和政治舊道仍少溝渠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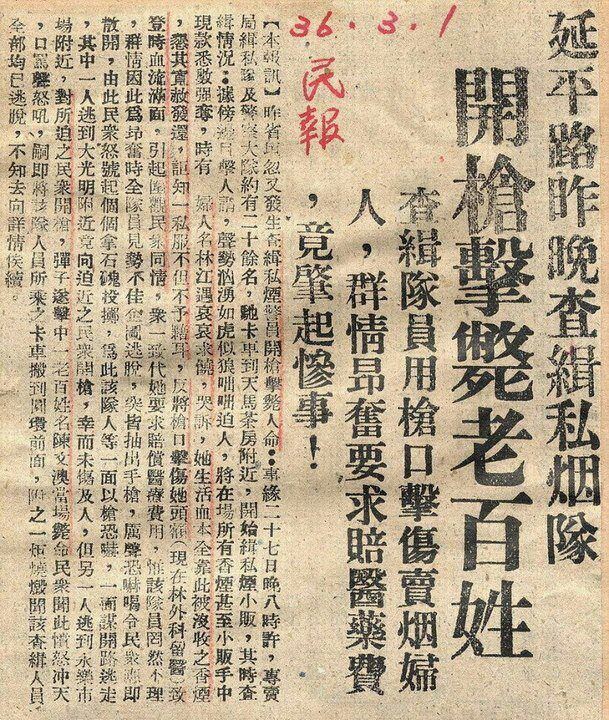
近年來二二八論述遇到最大的瓶頸在於: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元凶是誰?
前者從早期官方側重外省人死傷嚴重的一兩千人,到民間動輒以萬起跳的傷亡人數(史明聲稱有100000萬人,蘇新、林木順說是10000上下,楊肇嘉則指稱17500人),而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則引陳寬政教授說法,估計是18000到28000之間,凡此差距都不可以道里計。
去年吳乃德在一場以〈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為名的演講,拿林獻堂日記為本,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000上下,這可捅到蜂窩,瞬間批判聲不絕於耳,事件在吳撤文後暫歇。今年二二八前夕,林邑軒、吳駿盛兩個年輕人聯合發表〈重探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性別 死亡比例的推估〉乙文,以人口學推估死亡人數當在1304到1512之間。這引發受難者家屬非議以及一些歷史研究者的責難,是可以想見;但讓人遺憾的是,批判責難通常不是基於方法論辨析,而係它挑戰到既有的聖壇,於是情緒、權威取代實事求是的討論。
其實早年各方的報導都有誇大之嫌,而在事件可以公開討論的20多年後,逐漸擺脫悲情與既有的歷史研究,多方酌取各種社會科學為工具,全學科而非被台史學界壟斷的二二八研究才不致如博物館標本被釘死。或許林、吳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反思集體記憶從何而來?血流成河的印記是否集中於基隆、台北、嘉義、高雄,以致我們擴散為各地皆然?因為長期的禁忌,反讓惡靈不斷滋長?…當然也可以質問林、吳二人這樣抽離具體時空的科學研究,是否遺漏了什麼環節?但這是求全而非以擬神學教義的手法否定他們的用心。
何況不論死亡人數是以萬起跳,或者吳乃德和林吳二人的千人說,都掩蓋不了21師來台後於各地有系統獵殺菁英頭人和青年學子的惡毒用心,它的殺雞儆猴效用迄今仍在。可以說若無二二八的軍事鎮壓,台灣菁英頭人大量被殺被關或流亡在外,倖存者多半緘默一生,或有如蔡培火那樣卑躬屈膝,以及多數台灣人從此視政治參與如畏途,全體心靈重創,否則1949年敗逃至台灣的蔣氏國民黨政權也不可能在政經文化全面踩在台灣人腳上喝香吃辣一甲子以上。泛藍與犬儒者一意拿成王敗寇的中國歷史觀意圖稀釋二二八,全然是醬缸心理發酵。二二八死亡人數的深究就在破除醬缸文化,祇是它不該囿於既有架構分毫不可質疑。

再就真凶元惡問題。前些時日國史館出版新掘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六冊,陳儀於1947年3月2日尋求南京出兵的電文終於出土,足證陳儀對事變參與者虛與委蛇,背後猛力插刀的陰狠事實,不止陳儀,當時軍方頭頭柯遠芬、彭孟緝、史宏熹、張慕陶以及率21師來台的劉雨卿也都逃不掉責任。問題在於現有檔案資料還找不到蔣介石手書「格殺勿論」之類的明證。真要追究蔣介石責任,得進一步釐清他允許派兵的目的,以及其後軍方掃蕩、清鄉所為的殘虐惡行,到底知情多少?是否惡意縱容?2006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提供了一些方向,但這都得進一步詳查相關的檔案文件,所以此際所談祇能是政治責任,至於民刑事責任以及戰爭責任,都還太早。
更糾結的是,1949年國民黨敗逃至台灣後,昔日中央鎮壓地方的問題若不解決,蔣家王朝勢難安穩南面而王。於是,一方面有妥協,1950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既有安撫溫和仕紳派的用心,也有繼續監控的意圖;另一方面,傾左的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則逐一在白色恐怖期間清理掉。所以儘管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在時間與內容上有別,但置於台灣特殊的歷史時空,兩者卻必須匯整梳理,畢竟白色恐怖中還是有不少二二八因素,如此蔣介石與其鷹犬(特別是彭孟緝)的罪愆才得以全面鋪展,這是台灣轉型正義的辛苦路。
死亡人數和元凶追查之外,如何釐清二二八的性質其實更為棘手。關於性質的縷述歷來有族群(文化)衝突、追求自治、階級矛盾總爆發…等,早期有些獨派人是族群衝突論的力贊者,但事件初起雖有本省人(絕大多數為流氓)毆打、洗劫外省人事例,但很快遭制止,所以族群衝突祇是表象而非本質,其後不少獨派學者傾向文化衝突(現代VS.前現代)。經受日本殖民苦煉獲致某種現代性的台灣人,和停留於前現代模式的中國大異其趣,所以事件爆發確實帶有相當多的文化衝突色彩,但這論調有淪入扁平化的危險,因為二二八事件仍須納入二戰後所有殖民地脫殖獨立或返歸母國的衝擊來研究,這面向不僅於台灣/中國,光是文化衝突不足以涵蓋全部事項。
近來,將二二八定位於爭取自治似乎最為四平八穩。事件後延安中共的定調如此,前此國民黨的馬英九政權亦如是,不少穩健持平的台灣史學者也認肯。觀諸「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三十二處理大綱》內容,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宗旨,但如此定調又無法反映國共內戰後,台灣物資短缺、物價高漲引爆的經濟鬥爭。
於是,中共方面除了界定事件屬於地方自治而非尋求台灣獨立外,更把焦點定著於階級矛盾。近日中國大肆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就表示二二八事件係「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吃台灣人豆腐的言行,卻無視於中台當時明顯存在的文化衝突,這祇是中共意圖攘奪二二八話語權的政治伎倆,完全是對台灣人的無禮漠視。
總的說,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脫殖期間,各界都對未來有高度想望,卻又全體失落的集體行動,對象既是陳儀,也是對中央國民政府的不滿。於是不論左中右溫和或激進的人群全捲進這場歷史大風暴。一方面,溫和的仕紳派循著早年自治運動的軌跡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亟思在體制內與長官公署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日治時期的台共、新文協、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等左翼運動者,面對新局則喚起社會革命的美夢;最後,屬於戰中世代的少壯派(深受皇民運動洗禮,以及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則試圖以武裝暴力反抗長官公署的歧視統治與經濟剝削。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座新舞台,既有20年代左右鬥爭的痕跡,且有少壯勢力摒棄溫良恭儉讓的無畏行動,既聯合又鬥爭,且時時競爭領導、詮釋權。所以愈深入二二八內裡,就愈不能用單一、明確的指標來蓋括事件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