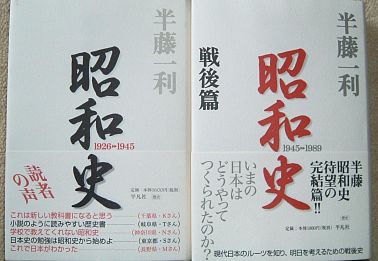然而,從社運到政治的轉換對哈里斯壯來說並不困難,族群才是永恆的挑戰。
五年前哈里斯壯在一場討論性別與族群議題的論壇上,認識當時華人學生組織「學運DEMA」的秘書王澤欽,而後成為室友。長期耕耘運動的組織經驗讓他們都意識到,馬來西亞的族群融合多麼不易,即便在進步的運動圈都是縮影。哈里斯壯和王澤欽所處的組織,在創立之初皆強調多元族群,但時間一久,還是無可避免的各自分流。
「語言和文化差異的確是最大原因。」王澤欽在檳城喬治市著名的愛情巷,一家社運圈愛去的咖啡店酒吧跟我說。
他目前是民主行動黨議員的政策幕僚,堅持不入黨,不作選民服務,還有來自南馬柔佛州的質樸。「別說我是左派青年,」接著他給了我ㄧ串更長的身分標籤,「我在社會主義大學念新馬克思主義及新社會運動,被地方文化建構而成,我讀的不代表我是誰。」
王澤欽當時所投入的「學運DEMA」,是1998年由烈火莫熄世代的大學生成立的跨校民主運動組織,最初設定為關注人權、環境、食品安全與農業、媒體、私有化等議題,《當今大馬》旗下KiiniTV執行長楊凱斌和檳州公正黨州議員李凱倫都是第一代成員。
楊凱斌認為學運創立之初是以多元族群為訴求,十五年下來演變成華人為主的學生組織,並非當初所期望,然而這並非「學運」獨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