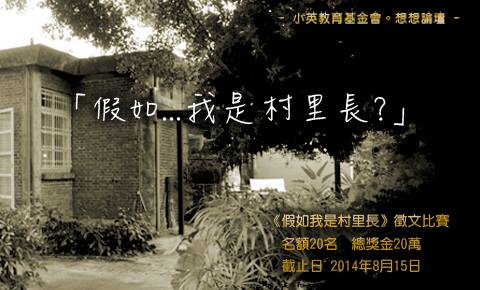古人說伴君如伴虎,去年王金平遭到馬英九政治追殺,現在張顯耀似乎也面臨同樣的情景。這種得君愛就萬事無礙,不得君寵則變害蟲的故事,在過去的歷史上一再重複上演著;只是,在民主的當代台灣,竟會重演君主專制或威權年代的故事,倒是令人感到詫異。
《韓非子‧說難》曾經談到一則故事,春秋時期衛國有個名喚彌子瑕的人獲得衛國君主衛靈公的寵愛。當時私自駕駛衛國君主馬車必須接受斬足之刑,有一天彌子瑕母親生病,彌子瑕偽稱君主命令搭乘衛靈公馬車出宮。不過,衛靈公不但不處罰靡子瑕,反而讚揚彌子瑕孝行。又有一次,彌子瑕與衛靈公同遊果園,彌子瑕將吃了一半的桃子遞給衛靈公吃,衛靈公不在乎桃子上還有彌子瑕的口水,直稱彌子瑕是因為愛他所以把美味桃子給他吃。然而,幾年後,彌子瑕失去衛靈公的寵愛,衛靈公想要把他趕出宮,於是拍桌大罵當初彌子瑕偷駕馬車以及讓他吃剩桃是在欺辱君王。這則故事,就是成語「餘桃啖君」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