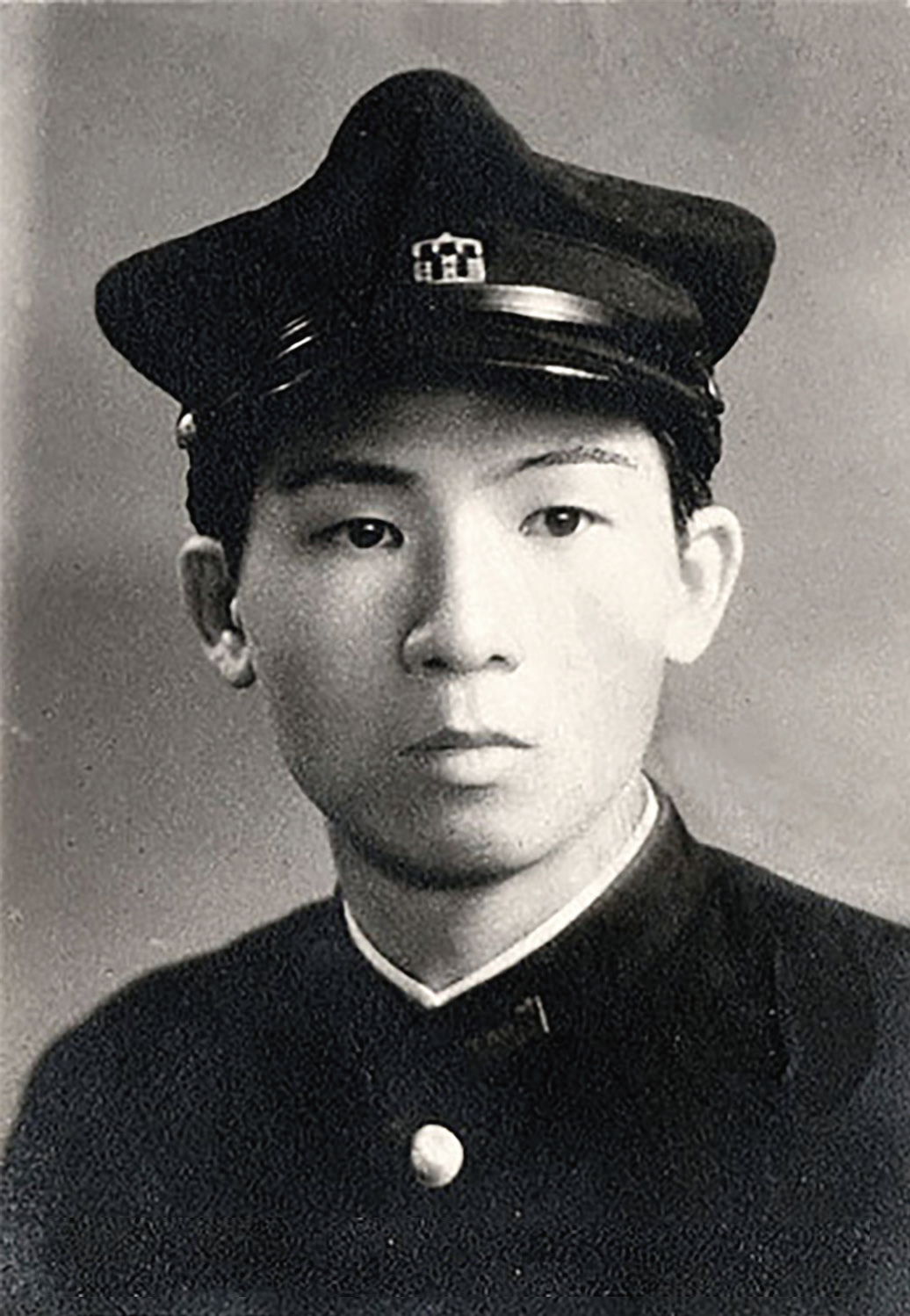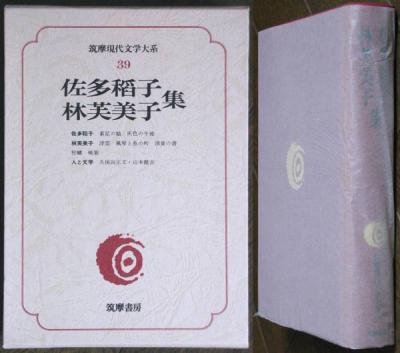1920年代受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日本本國對於政治社會的思想也呈現多元開放的景象。當時日本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很濃厚,特別是1921年國共產黨成立,隔年日本共產黨隨之成立,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也因此受到影響,加上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出現,意識形態論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況。文化協會創立以來,由於時常與島外留學生連絡,島外留學生也常組團返台擧辦巡迴演講。當時最為風行的思潮,就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透過文化協會的活動,這些當代思潮遂逐漸被引進台灣。

在潮流的影響下,文化協會也產生了改變。其一是農民爭議與農民組合的成立,加上農民爭議事件屢屢發生,使得文化協會為解決農村現實問題,漸漸從民族差別問題,轉而注意農民問題。其次,留學中國的學生受到中國改造爭論的影響,藉此名義探求台灣社會的特質及改造之路線。其三,文化協會組成的成員大多為地主與資產家,雖然期間出錢出力,但因日本當局抵制,請願始終無法排上議程。長此以往,當然易使參與者灰心,對於請願的意義產生懷疑,而請願運動本身也因長期沒有太大進展,也漸漸流於形式化,成為某些人物的特定商標,無法提升台灣民眾對政治社會運動的持續熱潮與支持。這樣的情形當然也就引起激進派的不滿而產生對立,加上總督府有意識與計畫地進行拉攏、滲透、分化、打擊與消滅,終於引起文化協會的分裂。
當時文化協會已分成三派,一是共產主義的連溫卿派,二是受辛亥革命影響的蔣渭水派,三是合法鬥爭型,即台灣民族運動的蔡培火派。到了1926年左右,鬥爭呈現表面化,1927年1月文化協會終於因路線問題而分裂。於是文化協會完全由連溫卿一派掌握實權,向來以從事民族主義文化啓蒙的的文化協會,轉變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啓蒙團體。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等由新章程和意識形態的意見不同,紛紛退出新文協,以別於以「階級鬥爭」為主的新文協。於是兩派因路線之爭,形同水火關係。
1927年2月,文協舊幹部協議組織政治結社,並以蔣渭水的提案為主,成立台灣自治會,但因該會主張「自治主義」,因而被禁。之後陸續改名為台灣同盟會、解放協會、台灣革新會、台灣民黨等民稱,向當局申請結社,結果不是因為主張自治,就是因為結社團體綱領出現「台灣人全體」及「解放」等字,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團體,而遭到當局禁止。台灣民黨被禁後,同年7月,蔣渭水等人再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初,立黨精神不免受制於官憲而無法暢所欲言。迄至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通過「對於階級的態度」和二次大會宣言,加上蔣渭水也在此期間發表眾多文章,依此吾人才得以從中窺探民眾黨成立之初未能充分表現的立黨精神。根據這些文章的闡釋,可知民眾黨的立黨精神與指導原理,如下:
(一)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是要同時並行的。
(二)擁護農工階級,就是階級運動的實行。
(三)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中心力量。
(四)企圖農工商學之聯合,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共同戰線。
(五)本黨要顧及農工階級之利益,加以合理的階級調節,使之不致妨礙階級運動的前途。
(六)集結台灣各階級民眾,在黨的領導下,實施全民解放運動。
在上述以蔣渭水言論為主的指導原理引導之下,自1928年以後,民眾黨漸漸發展成為台灣同胞反抗日本的最主要領導力量。其後,新文協與台灣農民組合相繼受到當局彈壓,民眾黨又在反對鴉片新特許及霧社事件上,表現出與總督府對立的尖銳作法,使得民眾黨愈成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雖然民眾黨在當時的形勢大好,但隨著內部的分裂及改組,民眾黨最後竟遭到總督府的禁止處分而吿終,加上領導人物蔣渭水在民眾黨解散後不久即辭世,致使被解散的民眾黨更趨於解體。
台灣民眾黨雖然既難產又早夭,但在短暫的奮鬥過程中,已從創立初期「民眾的信念已極混亂,左翼份子的惡宣傳亦甚猖獗」,從而發展為「對內獲得四百萬同胞的信賴支持,對外已獲得日本中國及國際間的認識」。最後,更因力行與總督府當局對抗,使民眾黨被認為是推動民族解放運動之團體,並足以撼動當局的施政,又有能力動搖日本國策,故不被當局允許而被「有計畫的絞殺」,使成立於危難之中的民眾黨,僅短暫存在3年7個月,便走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