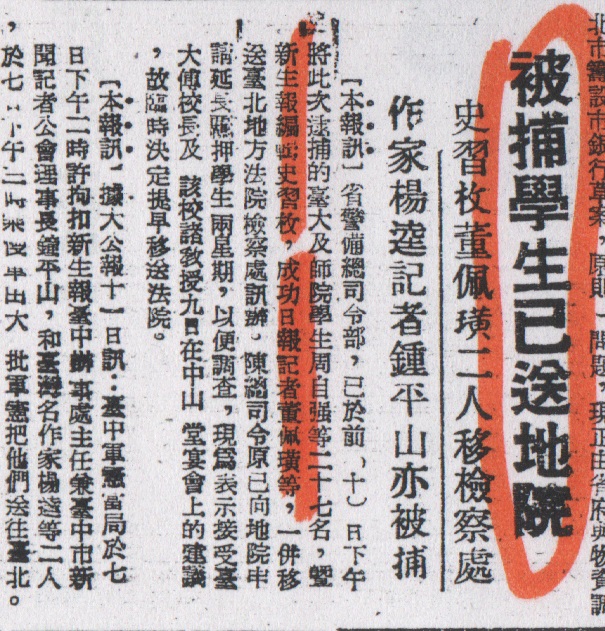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戒嚴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曾經有段期間,台北市的中學生自9月起就沒有假期,必須為了雙十國慶、台灣區運動會,被動員去排字,成為國家慶典的人肉布景。
北韓動員數萬民眾在國家慶典上演的排字秀,能分秒不差地變換畫面,宛如人體LED,舉世稱奇。其實在廿年前的台灣,每逢光輝的10月,台北市的中學生也要上演排字秀;先是為了歡迎歸國僑胞於10月9日在體育館舉行的四海同心聯歡晚會,有數千名學生手舉牌字版排字;接著是10月10日在總統府前的閱兵大典,更有數萬名學生頭頂傘帽,排出國旗、中國民國萬歲等圖樣;月底還要在區運會演出。
排字的創始人是北一女美術教師黃鈞。他在1963年從教育電視台轉任北一女後,先是創立儀隊,設計各種隊形;之後在1964年的北一女運動會,利用不同顏色的帽子與衣服,指導啦啦隊排出簡單的字樣;接著在1969年的台北市中學運動會,指揮千名北一女啦啦隊排出各種加油標語,大出風頭。自此,每逢重大國家慶典、運動賽事,就會伴隨北一女的排字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