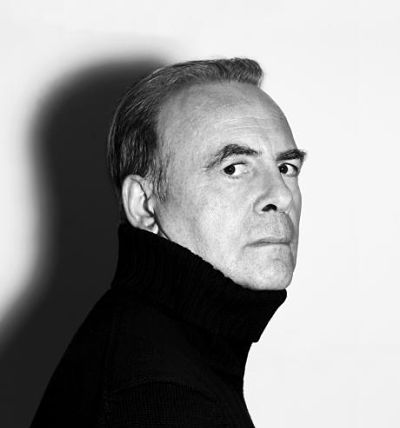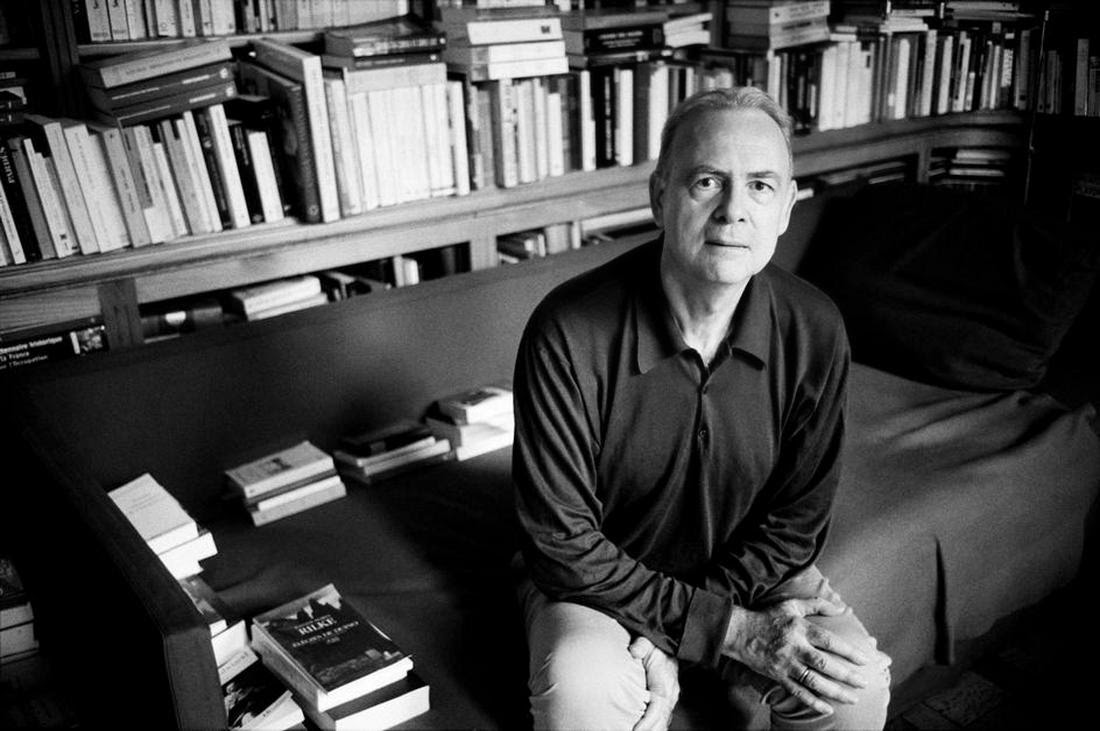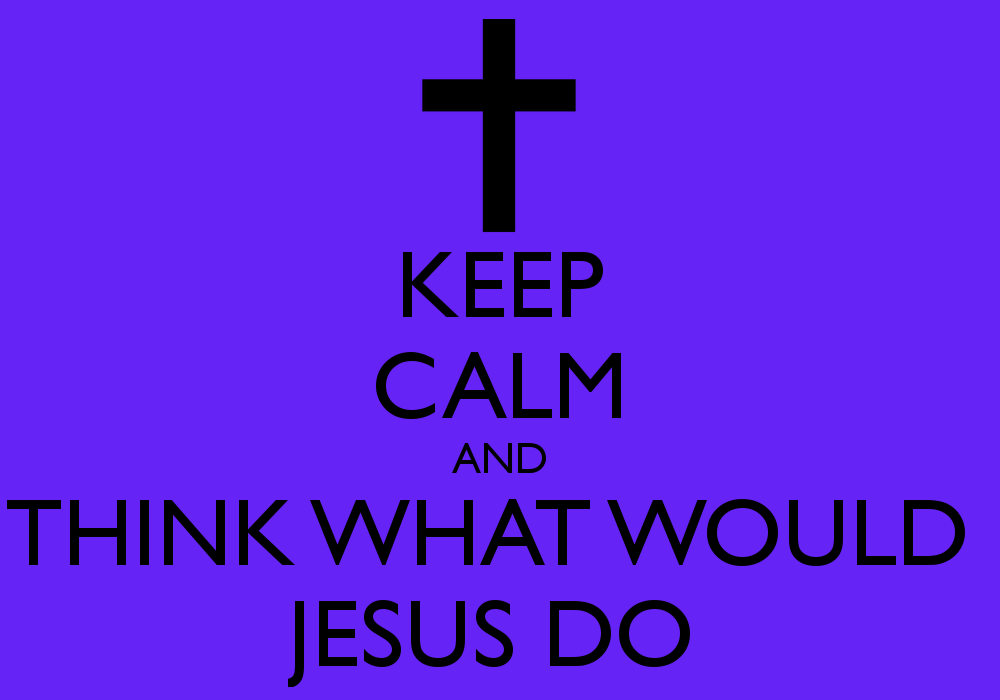今年八月,香港「有線電視」製作了一部中英聯合聲明三十週年的專輯,節目中有位不願曝光的受訪老中共黨員,以「白蟻政策」來形容中國對香港的滲透手法。所謂的「白蟻政策」意指中共派出大量如同白蟻的人員,鑽進香港這棵大樹的各個層面以為齧蝕。外表觀之,大樹依舊是穩重堂皇,但內裡早已被白蟻一點一滴蛀空蝕透。

同樣的,馬邦伯治台這些年,中國因素就像白蟻一般,大剌剌地挺進台灣,滲進社會各層面;因此,若2016年馬邦伯順利交棒給中國國民黨的接班人,那可見中國白蟻在台灣將更形猖獗肆虐,台灣這棵大樹是否得以表裡如一的健康續存,將令人懷疑。設若天佑台灣,中國國民黨在2016失去執政位置,台灣人民首先必須面對「中國白蟻」的問題,勢必歷經除蟻工程的試煉。但問題是,中國白蟻在台灣,究竟遍布在哪裡?又以哪些面目出現呢?
中國白蟻的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