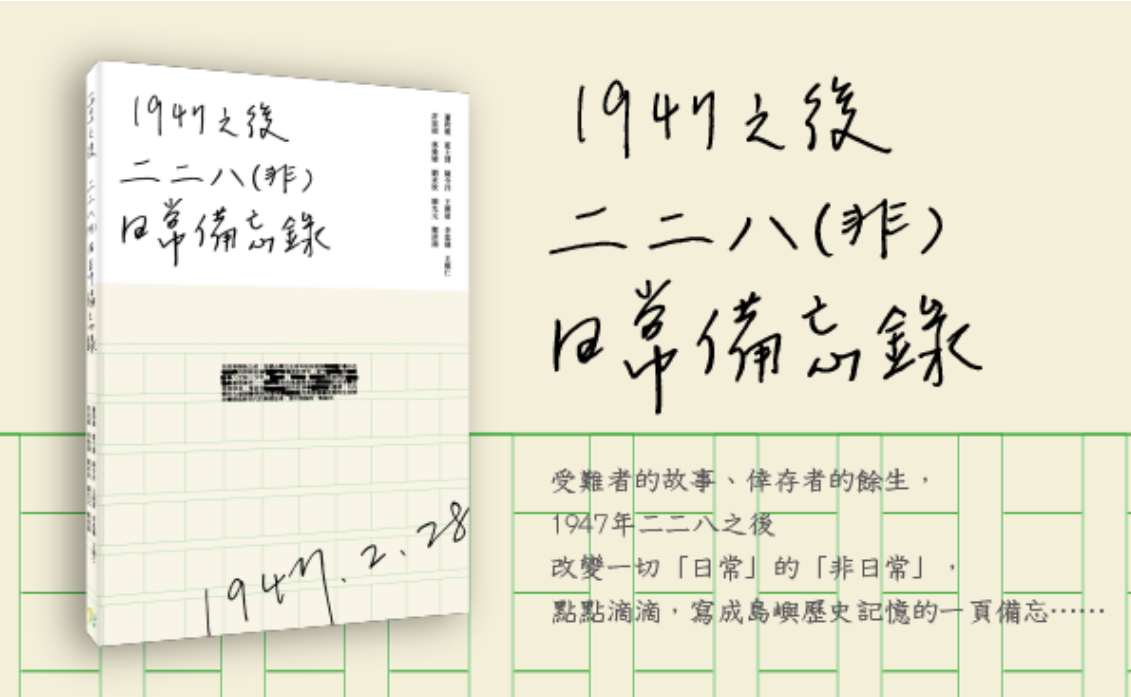「回來後龍以後,火車若嘟,阮心肝就微,想每一次這趟車若來,阮頭家就自八堵回來,現在有去無回來。」(王鄭阿妹)
「到現在,我昨天才看到報紙,寫講單親的母親需要社會的人來照顧。彼時伊被劫走去,我就變成單親的母親,只有一直想要顧囝仔,看囝仔能不能和其他人的囝仔一樣,我彼時不知道單親的母親這麼難做,自己又要賺一點錢給這些囝仔吃,又想看能不能教得有行。」(郭一琴)
「有時暗時睡不著,我就一直想這件代誌,想這個國家怎麼生成這種款?想阮頭家人又無怎麼樣,好好的人,來把伊抓去打死,這叫什麼國家?」(張楊純)
「作為一個查某人,我這世人的感覺是:『勇敢活過來。』男人的工作,我都統統做,好像很勇敢的活過來。」(張玉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