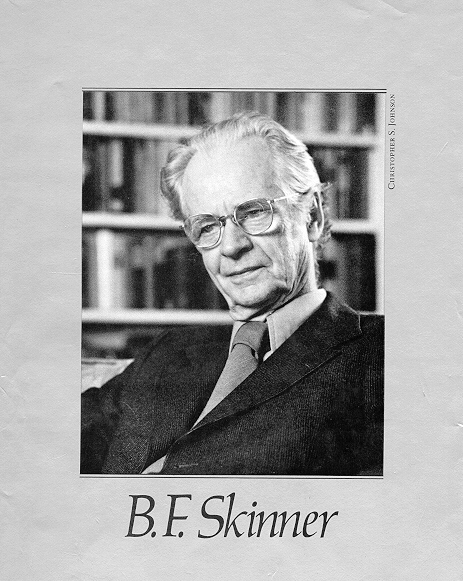中國倡議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北京提議起,國際反響可說是不溫不火,除了一部分亞洲發展中國家應和外,發達國家在美國的「打招呼」下都僅坐壁上觀。然而,今年3月中旬起,風向急轉直下:3月12日,英國宣布加入;13日瑞士,16日德國,法國,意大利也相繼宣布加入。自此,七國集團(G7)中已有四國確定加入。近日,韓國和澳洲等國亦宣布加入。截至3月29日,共有41個國家申請加入,全球十大經濟體,除了美國和日本,已全部加入。

美國盟友們此次倒戈,不啻是美國外交的珍珠港時刻。時移世易,這次實施暗算的是美國的歐洲盟友們;而當年對美國下黑手的日本,目前為止還跟華盛頓保持一致。之所以遲至3月份才宣布,一是中國劃定3月31日是創始成員申請截止日,二是北京在亞投行的治理結構方面向歐洲國家做了重大讓步(如作為第一大股東,放棄否決權),第三就是讓華盛頓來不及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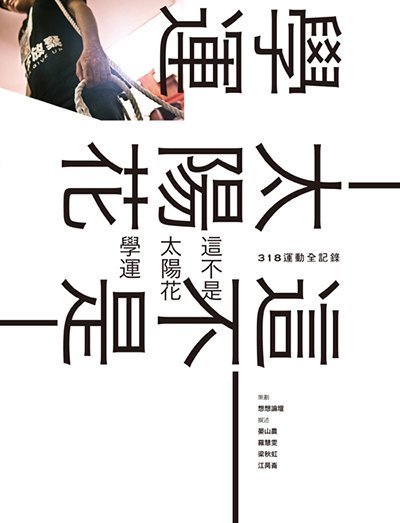
 新任台中市長林佳龍近日宣佈廢除台中BRT系統,引起各方熱烈討論。根據媒體報導,台中BRT經過專家體檢後,小組報告提出的四個方案,分別是完成國際標準BRT、有優先號誌的混和道、無優先號誌的混和道,以及公車專用道
新任台中市長林佳龍近日宣佈廢除台中BRT系統,引起各方熱烈討論。根據媒體報導,台中BRT經過專家體檢後,小組報告提出的四個方案,分別是完成國際標準BRT、有優先號誌的混和道、無優先號誌的混和道,以及公車專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