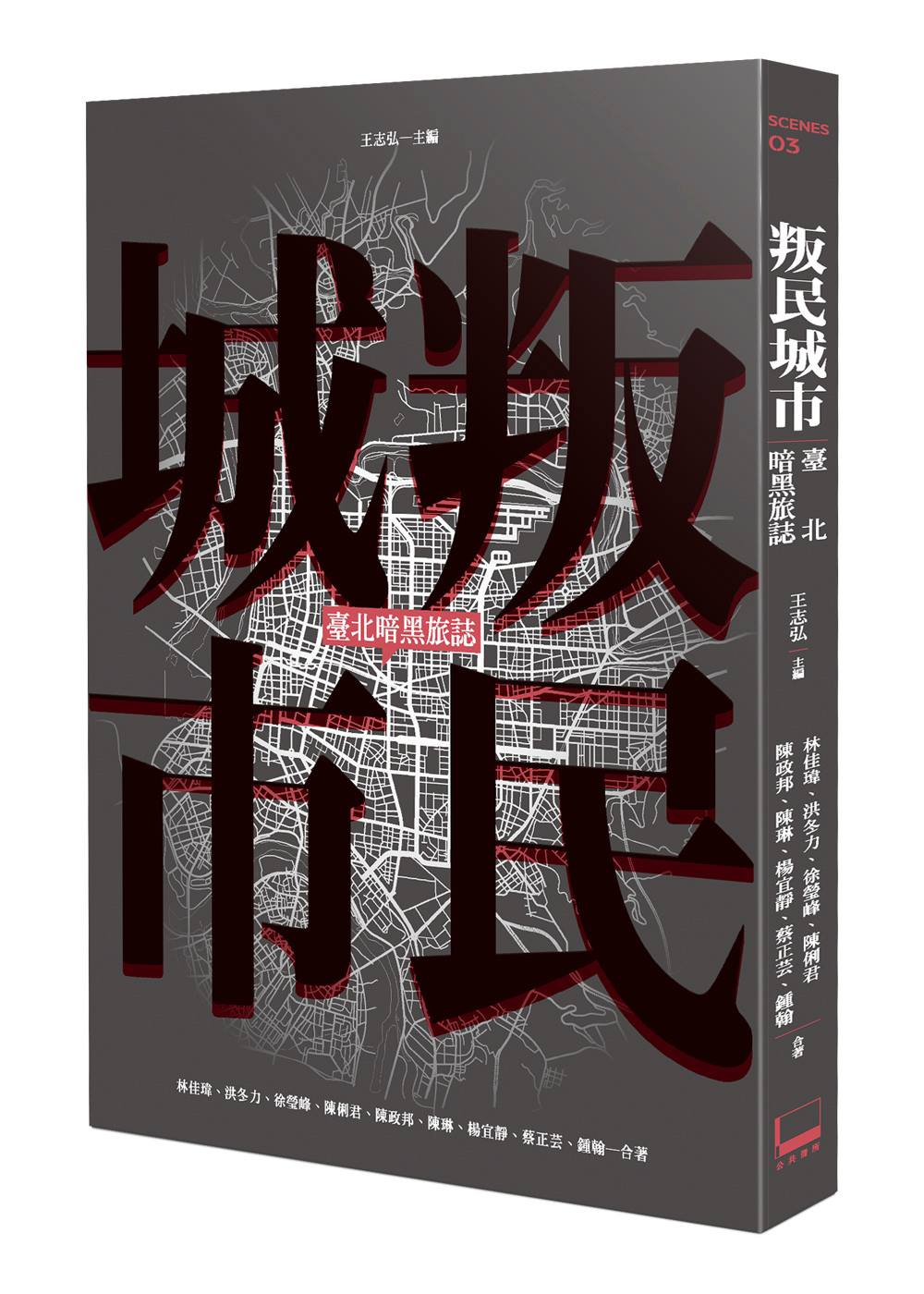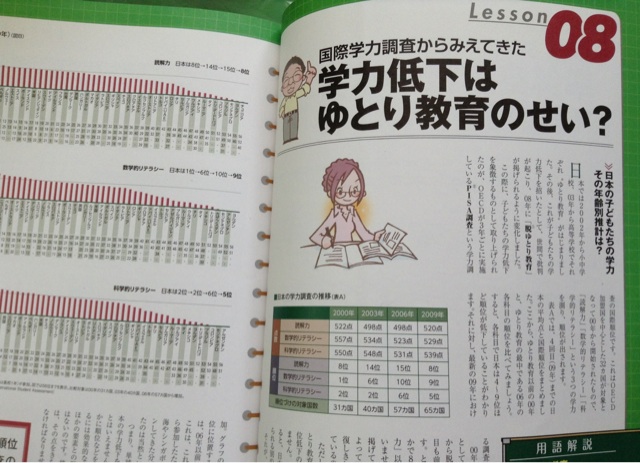國民黨下午召開臨時黨代表大會,黨代表出席891人,最後812位經舉手表決贊成通過廢止洪秀柱參選總統;同時,提名審核委員會立即提案徵召黨朱立倫代表參選、立即經由臨時中常會核備後提報臨全會,完成了國民黨「柱下朱上」的戲碼。
一連串緊湊的「臨時」與「立即」,看似倉卒緊急,實則在七月十九日全代會之後的第三十七天,朱立倫奪柱行動已有跡可循。今天的臨時全代會,從出席人數突破換柱門檻,到形式上公開、民主的「舉手表決」人數,只不過是朱立倫當著全台灣民眾的面,要讓不甘心不放手的洪秀柱輸得心服口服、顏面盡失。今天下午的這齣舞台劇,可以看到朱立倫運作廢止洪秀柱並即刻完成被徵召的「快」、用舉手表決公然挑釁換柱程序不正義的「狠」、傾盡全力動員黨代表的「準」,這是他拿回總統參選權的畢功之役。我們僅看到一位挺柱黨代表手拿連署書要求不記名投票,卻看不到其他挺柱黨代表力挽狂瀾;九成表決贊成通過廢柱的不一定代表國民黨多數,卻清楚看到朱立倫精密點算人頭的運作心計。此舉讓全民目睹,國民黨為了爭權奪位,罔顧同黨情誼、逆行正常議事規則、玩弄民主法治程序的假民主、真封建。
從換柱風聲開始,洪秀柱一路走來冷暖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