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作為日本唯美文學代表性的作家,永井荷風(1879-1959)深刻反映著兩種近乎矛盾的文學異質風格——對於法國文學中浪漫自由的熱愛,另一方面,他在其細膩精微的筆觸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對於昔日江戶文化的緬懷。

在批評家看來,荷風所謂的文學藝術至上論,其實並不徹底,因為表象的浮現多於本質上的突顯,尤其他對於時代社會和政局變動總是漠然看待,一味著墨於小說主角進出下町的花街柳巷,狎妓伴遊的細節生活。面對這種批判聲浪,他並未正面還擊,依然以此為寫作的進路。然而,他果真如批評家所言,僅只耽溺在東京郊外情色冶蕩的淫窟裡,遊走於文人的低級趣味,而不願舉起正直的筆尖揭開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各種惡俗偽善的面具?
文明衝突與作家心路歷程
1903年,永井荷風在父親的安排下,前往美國留學,後來又學習法語,遊歷法國。在歐美留學期間,他深刻觀察著物質文明的進步,更著眼於其精神文明與文化特色,而在這樣的文化衝擊下,他漸漸對明治時期的思想文化產生厭惡之情。但反過來說,1908年又可謂是永井荷風文筆生涯的起點。
這一年,他結束了遊歷生活,回到日本,發表了《美利堅物語》、《法蘭西物語》等力作,其唯美浪漫的情感再次與其生活據點連結了起來。在此之前,他寫過一些短篇小說,處女作〈簾中月〉和〈野心〉〈地獄之花〉〈夢少女〉,還有以他叔父為原型寫的〈新任知事〉等作品,都曾經獲得好評,不過,彼時他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後來,他發表了〈監獄的背後〉和〈狐〉等短篇以及〈冷笑〉等中篇小說,對於日本當時過度追求西化的庸俗性有所諷刺和抨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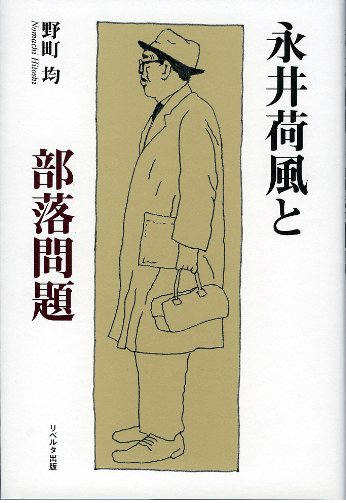
但與此同時,在〈深川之歌〉、〈歡樂〉、〈隅田川〉〈歸國者日記〉等小說中,他的敘事風格發生了轉變,從反對當時主宰文壇的自然主義,開始轉向謳歌唯美主義,傾注在描繪與妓女的純情之愛,追求頹廢官能享受的快樂。尤其,他主編慶應大學《三田文學》雜誌後,躍升為唯美主義文學運動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不過,兩年後1910年爆發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十餘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震驚了整個日本社會,他的精神亦深受打擊,對社會(事件)採取消極迴避的態度,轉而描寫或寄情花街柳巷的妓女生活及其處境。〈妻宅〉、〈新橋夜話〉、〈疏柳窗晚霞〉、《爭風吃醋》《阿龜矮竹》等中長篇小說,就是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此外,由於他的法語能力甚佳,翻譯出版了法國詩選《珊瑚集》、《夏姿》,寫了隨筆集《短齒木屐 》、《雨瀟瀟》、《麻布雜記》、《下谷叢話》等。
1931年,他描寫銀座咖啡館女侍(私娼)生活的中篇小說《梅雨前後》,更加奠定了文壇的聲譽。進一步說,當他的作品《背地裡的花》(1934)和著名中篇小說《濹東綺譚》(1937)問世後,他已成為名符其實的頂尖作家了。但好景不常,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文人作家和藝術家們的創作空間受到了嚴重擠壓,他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政治思想、不得發表反對戰爭的言論,有些作家迫於各種考慮,甚至主動配合國家戰爭政策成為愛國的合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永井荷風因小說題材過於萎靡淫穢被禁止發表,其住宅在美軍的空襲中被燒毀,一時找不到棲身處所。儘管如此,他仍然發揮著堅持寫作的品格,一方面躲避戰火的侵襲,埋頭筆耕不輟。戰爭結束後,他陸續發表了戰爭時期完成的作品,如《浮沉》、〈勳章〉、《來訪者》、《獨白》等;值得一提的是,荷風多卷本日記《斷腸亭日乘》,因其記載翔實可靠,對研究者提供很大助益,研究者依循日記的進路,都能找到彼時四季的嬗遞、拈花惹草的樂趣、讀書感想:(如《落葉》薄田泣菫著、《照葉狂言》泉鏡花著、《今戸心中》広津柳浪著、《三人妻》尾崎紅葉著、《一葉全集》樋口一葉著、《柳橋新誌》成島柳北著、《梅暦》為永春水著、《湊の花》為永春水著、《即興詩人》森鴎外著、《四方のあか》蜀山人著、《うづら衣》横井也有著、《霜夜鐘十時辻占》黙阿弥著、《菜根譚》、《紅楼夢》、《西廂記》、《随園詩話等》)、文人交友往來、與出版社編輯交涉、到古舊書店買書和曬書,下町居民的生活細節和物價指數等等。

寫實主義敘述的勝利
在永井荷風眾多作品裡,〈勳章〉是一部很值得深入探討的作品,因為其對底層人物處境,有深刻的理解,文字細膩而生動,輕易地就能贏得讀者的共鳴。他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切入,回憶為一位以外送飯菜至劇場後台的老大爺(他年輕時曾參與日俄戰爭)拍了照片,要將照片贈送予他,而這老大爺卻不知去向了。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荷風不愧是常年進出劇場戲院和風月場所的行家能手,否則不可能寫出如此逼真寫實的場景來。例如,他這樣描寫曲藝場後台的情景:「一進門,就是一道板壁,上面貼著各個場次的表演通知。沿著板壁過去,緊接著有一座樓梯。它又窄又陡,上面扔滿了垃圾。上了樓梯,有一小段狹窄的走廊。它的中段有一道破門,連嚴寒時節也是敞開著,這裡是舞女們的大房間。」
接著,他也點出當地警察局對於演藝場所的風紀管理,並表示自己與劇場的關係,「對於舞女們的房間,警察局曾經有訓示,規定凡是劇團外面的男子,無論有任何要事也不得入內。不過,唯獨我總是大模大樣地進進出出,即不需要經過誰的同意,也沒有人對此加以指責或奇怪。這中間當然是有某種緣由的。我第一次來這家劇場後台時,已經是花甲之年,所以,在別人看來,我擅自撞進半裸體女人橫躺豎臥的房間,要幹出什麼傷風敗俗的事情,在體力上也負荷不起。」寫到這裡,他突然筆鋒一轉,將場景移向了舞女的大房間,重現視覺、聽覺、嗅覺、味道的立體交響,「平時,這裡經常總有十四、五個舞女。她們在破爛的榻榻米上墊著破爛的蒲團,或坐、或臥、或仰、或伏,什麼樣的情態都有。

而且,她們幾乎都是赤身露體,只是隨便抓點東西(譬如舞台服裝、後台便服或是澡堂浴衣)來把腰腿部分遮蓋一下而已。無論誰進來,她們都滿不在乎。她們有的三、五人湊在一起玩著紙牌,有的懷抱著嬰兒、對著鏡子描筆化妝;有的神情專注地修剪自己的睫毛,有的在織著毛衣;也有的正興味盎然地看著講古雜誌。沒有鋪榻榻米的那一點木板上,胡亂地仍滿了底破幫裂、帶斷跟折的舞台鞋履。有銀色高跟鞋、女人涼鞋,中間還夾雜著一些後台用的草鞋、室內拖鞋,外出穿的氈鞋、高齒木屐等等。這些大堆大團的鞋子、橫躺豎臥,連走路也沒有下腳的地方。廢紙屑、花生殼、栗子殼、水果皮、筍殼、菸頭等等,各種髒物混雜一起,又被踩得亂七八糟,每天靠一、兩個輪班的舞女也打掃不完。」這躍然紙上的描景功力,令人嘆為觀止,依我閱讀的印象,台彎作家凌煙在其長篇小說《失聲畫眉》中,對於歌仔戲團後台的生活寫照可與之比肩。比起評論者稱許荷風的唯美主義筆法,在我看來,這比自然主義的描寫更勝一籌了,說它是寫實主義的勝利,絲毫也不為過。
同時代相似空間的生產與重現
基於跨領域學科的整合精神,永井荷風小說對於場景(空間)的開創性的啟發,同樣可以借用「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的觀點與之連結起來,「……我們要想擺脫混亂不堪的局面,就既不要再把(社會性的)空間與(社會性的)時間當作(只不過被不同程度地改造過的)「自然的」事實來看待,也不能把它視為「文化的」事實;而必須將其視為產品(products)。這就導致了「產品」的用法及其內涵的改變。空間作為一場產品,並不是指特定的產品,一種事物或物體,而是指一組關係,這個概念要求我們拓展生產與產品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解。」要言之,永井荷風所刻畫的劇場後台,在1900年代初期的上海,似乎可以看見相似的場景(空間),亦即生產者(劇場老闆)、經濟活動與社會關係的辯證性的相互作用。

在此,我援引一下「美」蕭邦奇《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一書,第三章第一節〈法租界生活〉的敘述:「1906年至1909年,沈定一前往日本留學,他在那裡成為學生領袖,最後因資金告罄而離開日本。有好幾年,尤其是在1919年和1920年,沈定一就生活和工作在法租界大約二平方公里的區域內。他在這裡經歷奠定了他的作品和思想的基調,法租界位於國際租界南面,呈扇形,從面臨黃浦江外灘極窄的區域一直延伸到較寬的華人區。1919年,它的三條主要大街是:愛多亞路,在租界北端;公關馬路,在外灘附近平分租界;霞飛路,從英國跑馬場南端一直延伸到租借西端。每條街道風格不一,各自展現出西方對於華人佔主體社會的某幾個方面的影響。(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上海及其環境》第55-57頁)
「與鱗次櫛比的中外商號鄰接的愛多亞路被一個西方觀察家描述為「過渡區」,在這裡,新的外國建築物與古樸的舊貨店以及苦力臨時棚屋之類並存(C .E. Darwent《上海:旅行定居手冊》第71頁)。中間矗立的一座異國情調的宏偉建築是建於一戰期間的兩座娛樂宮之一的大世界,位於愛多亞路和西藏路之間。這座被譽為水晶宮與蹄兔島合一的建築是一座巨大的六層大廈,擁有數十個劇院、大廳和飯店,從屋頂花園的鳥籠到娛樂性魔術幻燈,無處不充滿迷人氣息。
例如:第三層有玩雜耍的、賣草藥的、做冰淇淋的、照相的,還有一群穿著分叉到臀部的旗袍的姑娘……,而在一個新奇的展臺前,陳列著幾排清潔用具,老闆正向好奇的顧客講解其用法:不必再蹲而是坐上去,這種清潔用具與進口管道極好搭配。四層則擠滿了射擊房、彈子房、旋轉輪,按摩椅、針灸櫃、熱毛巾櫃檯、乾魚和臘腸,以及跳舞臺……在最高的頂層,有人在鋼絲繩上來回滑行著,另外還有蹺蹺板、中國象棋、麻將、嘶嘶作響的爆竹引信以及彩票和婚姻介紹所。(潘玲:《老上海尋蹤》第93頁)。由此看來,這兩段現代性的場景(空間)描述,與永井荷風對劇場後台人生百態與社會圖景,有著異巧同工之妙,換言之,他們為我們回到問題的源頭,通過引入歷史社會學式的概念,並嚐試發現一些新的和更精緻的方法,來深化我們的文化視野。
底層與邊緣的聲音
嚴格講,永井荷風在〈勳章〉中,對於多數日本人不願意碰觸的尖銳問題——在日朝鮮人的處境,仍有含蓄巧妙的揭示。他點出劇場後台的人物實態,順理成章地安排了小商販朝鮮人的出場。「那天,我和往常一樣,慢慢登上二樓,看見那裡有一個滿臉麻子的青年男子。他穿著西裝,樣子像個朝鮮人。這時候,他正把一些化妝用品,慢慢地裝回一個偌大的皮包裡。一些買東西的女郎,正在向他付錢。
他剛起身來往外走,又進來一個四十歲的婦女,打扮像是某大雜院的大嫂。她把手裡的包袱攤開,裡邊是一些男女兩用襯衫、毛巾、手帕之類的東西。」接著,荷風將後台演員們購物的情狀,寫得唯妙唯肖,「一聽說有純棉的衣物,原本躺著的舞女們驚跳了起來,一齊擁過來圍在貨物的四周。甚至有一個青年部演員,顧不得剛剛卸裝洗完臉,半裸著身子就走到這裡,擠進舞女們們的重重包圍圈,便宜呀貴呀地對商品大聲議論。」這個場景結束後,小說主角——以送包飯維生的老者登場了。這時,從樓梯口又踉踉蹌蹌地上來一個老大爺。他身材高大,臉色潮紅,手上提著一只沉重的骯髒的送飯提盒。一個舞女正對著窗戶光線查看手帕的質料。她一看見老大爺,便大聲嚷嚷起來,怎麼這會兒才來?她肚子都餓癟了!老人沒有吭聲,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正如前述,這位老人每天看準時間到後台讓劇團的人訂飯,然後又算著時間拿著髒污的提盒把飯菜送來。實際上,這一帶所有的娛樂場所(歌舞劇院),都有不同的飯館來此承包伙食,而這送飯菜的老人,只是其中一家包飯館的外送員。他為了賺得微薄的跑腿費,一年四季幾乎風雨無阻送飯,難怪他總是一副疲憊的倦容。舞女們都叫他「鮫屋的老爹」。諷刺的是,在這淺草公園六區的娛樂場所市街,或是公園外面入谷町或千束町的偏街後巷,根本沒有一間叫「鮫屋」的包飯館。
我(荷風)探問了劇場後台的人,他們不知道老大爺住在哪裡,是否有妻室兒女。有一次,老大爺提著空的提盒來到後台,把大小碗碟收拾妥當後,取下夾在耳朵後面半截煙捲,一邊點火,一邊與一個穿著士兵劇裝的青年部演員聊談著。青年問老大爺是否打過仗,老人說,他參與過日俄大戰,地點就在滿洲。說完,老人目光茫然注視著演員的士兵劇裝,彷彿回想著他於明治37(1904)年參與的那場戰役。永井荷風以溫情的筆觸形容老人的心境,「畢竟像老大爺這種人,平時自然既沒機會、也不習慣去冷靜回憶自己的過去。所以,當別人問起的時候,當場也就數不清過去的年份了。」那個扮演士兵的男演員說,老大爺既然打過伩,可曾得過勳章?老人一聽,充滿用充滿自豪的口氣說:「他當然得過勳章的,現在,放在老闆家裡,要不帶給大家看看?」一個舞女趁勢說道,「下次把勳章帶來,穿上阿新的劇裝,再將那枚勳章縫上。」老人聽到這個提議,心裡非常開心,笑過之後,急忙站起身來,提起裝著空碗的食盒,徑直地走了出去。
其後,鮫屋的老爹果真趕來了。他這次沒有提著食盒,而是空著手來的。他坐在剛才坐過的地方,馬上從圍裙口袋裡掏出一個陳舊的布包,裡面果然有一枚勳章。他拿出來給大家看的,是一枚八級瑞寶勳章(注:授予文官、武官和民間的有功人員的勳章,最高一級,最低八級)和一枚從軍紀念章。舞女們立刻圍了過來,好奇地看著。這時,一個舞女說,何不把老大爺的勳章縫到劇裝軍服上,再由我(荷風)為他拍張照片。二十幾個舞女齊聲鼓掌叫好,老大爺被這熱情捧得暈頭轉向興奮不已。
他終於脫掉圍裙,穿上劇裝軍服,戴上軍帽,還掛上一柄道具用的刺刀,站到我的相機鏡頭前面來了。這時候,老大爺的頭上淌滿豆大的汗珠,滴滴嗒嗒地直往下掉。儘管我與老大爺從未交談過,但這時他卻三番五次向我道謝。我回到家裡,當天晚上立刻把底片沖洗出來,整體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但我注意一看,卻發現那枚勳章的位置放反了。它沒按規定放在胸部的左邊,而是放到右邊去了。我推想,勳章放錯位置可能有兩種原因,其一,當時那個舞女順手揀起一件別人脫在那裡的劇裝,不分左右邊就把勳章縫上去,其二,要不然就是老大爺年紀太大,一時糊塗造成的。沒辦法,我在加印放大的時候,只好把底片翻過面來做些模糊處理,讓別人不至發現什麼破綻。過了十幾天,我帶著照片來到劇場後台,準備把它送給老大爺。結果,一個舞女表示,自那次以後,他就沒來過。又過了一星期左右,我再到那裡遊逛,再次問起老大爺的去向,整個後台竟然沒有一人說得上來,甚至沒有人願意回憶一下,以前是否有一個老頭往這個後台送過飯菜。我(荷風)不得揣想起來,按照老大爺的操勞程度來看,他可能因腦溢血之類的疾病死去了,如果他有親人在世,我真想把特意為他拍的照片送去。最終,我做了一個決定,把這張照片和各劇場的節目單、流行歌曲以及舞女等各種照片和資料,一併收藏在一個盒子裡,把它標示為《淺草風俗資料卷》,以資保存記念。
結語
從日期上來看,永井荷風〈勳章〉發表於1942年,那時正值太平洋戰爭方興未艾之時,拿著筆桿的作家們不是被徵召至戰場,或組成筆桿子部隊,支持國家總動員政策,就是封筆保持沉默。確切地說,荷風採取的寫作策略,極為高明——迫害與隱微寫作藝術。二十世紀猶太德裔政治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1899-1973)亦善用這樣的書寫策略,因為這樣既能保全自身安全,又能繼續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場。
在我看來,荷風藉由打過日俄戰爭得過勳章這個社會邊緣人,最後淪為生計奔波忙碌的送飯老頭子,似手旨在於餘溫灼人的批判:沒有人記得這老爹曾有的輝煌,沒有人惦記他奮力掙扎的身影,沒有人願意為他遞送回憶的溫情。然而,研究者有另一種解釋,舞女之所以為老爹的劇裝縫錯勳章的位置,其實就是對軍國主義的反抗;舞女們無視於老人的存在,意味著她們對於(帝國)軍人的蔑視。總括地說,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荷風憑其〈勳章〉這部七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說,已為自身開闢出最大限度的言論空間了。而且,憑其絕妙的寫作技藝,留名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就此看來,誰說小說家的筆桿不能勝過老舊的自走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