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要創立一種學說體系,深入前人未竟之地,開拓嶄新的領域,絕非輕易之事。這需要遠大的抱負毅力和不斷努力,才可能接近這光輝的頂點。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1875-1962)在這方面的成就,堪稱為最佳的例證。早在他赴歐洲之前,他就具體了歐洲民俗學和人類文化學的知識,尤其是閱讀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馬林諾夫斯基的著述。在方法論上,他的確受到歐洲社會科學的啟發,但是他並非生搬硬套地加以引介,而是帶有屬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思考和情感來進行民俗學的田野調查,在累積實證研究的起點上,創建出一個國家的民俗學。

以日本妖怪故事為例,他認為,這些傳承和民眾的心理和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將妖怪研究視為理解日本歷史和民族性格的方法之一,亦即要強化和突顯日本的獨特性。他在早期的作品《遠野物語》中,生動描述了天狗、河童、座敷童子、山男等妖怪形象而廣為人知,主要著作有《妖怪談義》、《桃太郎的誕生》、《論民間承傳》、《國史與民俗學》、《關於先祖》、《蝸牛考》等。柳田國男的著述豐富,歿後出版《柳田國男全集》全32卷,成為研究者探索其思想軌跡的重要文本。
然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柳田國男初期他對於現實中的國家制是持批判態度的,而在學問的確立過程中這種批判態度卻被所謂近代天皇制國家所侵吞。不僅如此,他抱有殖民主義意識,甚至贊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而這些矛盾的光影,卻不由分說成為其學問和思想的特色。因此,我們如果暫時將目光從民俗學領域中移開,依其介入政治意識形態的順序,直到享年83歲為止,考察他如何看待和反應時代中的重大事件,如撼動東亞歷史深處的戰爭,應該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歷史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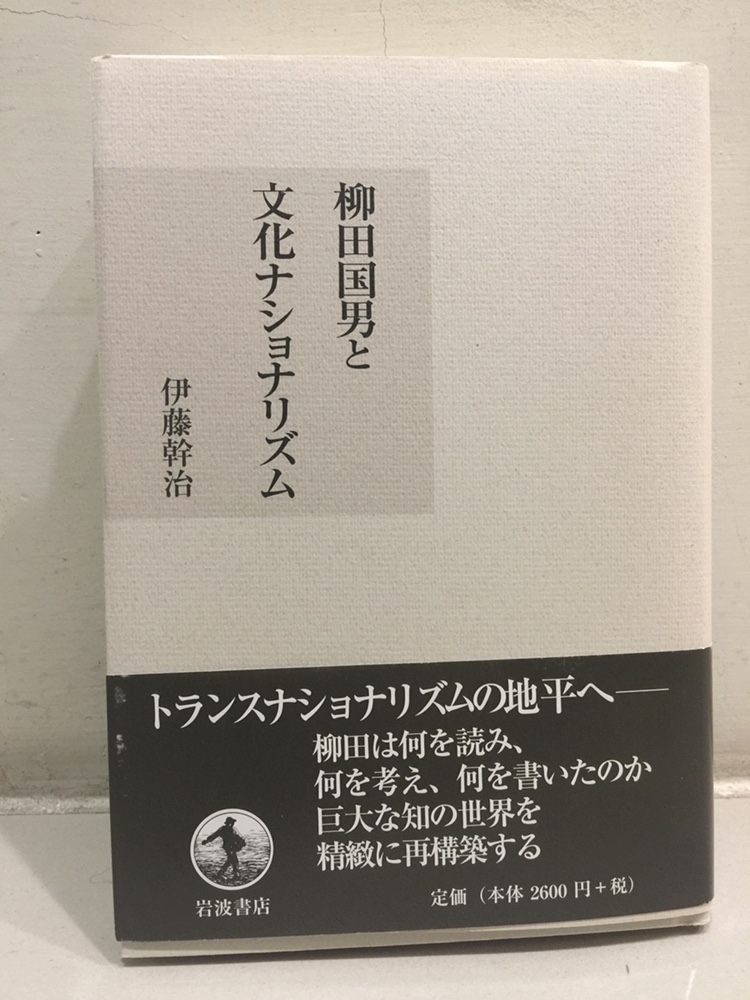 中日甲午戰爭的返光
中日甲午戰爭的返光
按照編年史來看,中日甲午戰爭開打之際,柳田國男約莫20歲左右,看得出,他對於這場戰爭印象深刻並留下時代的回聲。他在《關於祖先》一書中,就提及新舊墓碑的變化:「就我印象所及,在日本歷代祖先的墓地中,原本都有各自的墓碑。爆發日清戰役那樣的重大事件之後,在每個村落的路口,紛紛立著參與那場戰爭的青年戰歿者的墓碑。這成了為亡者設立墓碑的開端……。」換句話說,柳田國男如此驚奇的發現,因於中日甲午戰爭的緣故,日本村落裡的墓碑亦出現了變化。當然,這時候柳田國男所看到的光景,僅止出於像自然主義般的觀察,以詩歌般的直覺為基礎,缺乏系統性,尚未建構成嚴謹的方法論。不過,這似乎可以看出他在民俗學上的萌芽。他在〈靈魂與土地〉一文中,亦重提類似的看法:「……緬懷祖先不是像現在所想像的那樣將文字刻在冰冷的石碑上,當時的人們把快要腐爛的遺體藏在人跡罕至的河流或者山谷深處,這也算是回歸自然的方式吧。喪家會在喪屋守靈數日,才返回家裡,不識字的人們,只是在墓地周圍的樹枝上做個記號,或者根據岩石的樣子記住墓地的位置。儘管偶爾還會去獻花祭拜一下,但隨著時光的流逝環境改變,最終仍然會被人遺忘。至今,無論是原野上還是在深山裡,到處都能看到這樣的野墳,不僅如此,我們在有些地區還可看到人們根據習俗在墳上貼滿各種各樣的梵文。有些人為了祭拜祖先,會在別處設立臨時的祭壇,還會將沾染過家族成員鮮血的物品作為永久遠的紀念。經由這樣的演變,寺院成為專門管理喪家亡者靈魂的地方……」。
另外,柳田國男在《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職業婦人的問題〉一文中,提及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的猛增現象,包括職業婦女人數直線上升,這種因於戰爭時期的勞動供需會衍生出相對的問題:「在外出打工人群之中,女工的數量明顯占多數。從我們國家產業發展的歷史來看,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女性只在製絲和紡織這兩個行業裡快速發展,如果說我國工業是從擴展女性工作範圍之後才開始發展的,一點也不為過。但遺憾的是,這個發展過程伴隨著各種各樣的不幸。由於自己的日常生活,她們的性格發生了改變,她們對於出身農村感到自卑沮喪,與此同時,她們還必須忍受周遭各種冷嘲熱諷,雖然她們相互的同情和理解有所緩和,但更加不幸的是那些機械般的生產勞動以及對她們身心的摧殘。所以,女工慘遭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她們已經做出了重大的犧牲,但是為了肩負起家庭的重擔,她們只能欣然接受。還有一個現象,大多數年輕女性之所以自發性地去應徵女工,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的。我認為,這種情況是我國特有的寄宿制度而引發的。例如,進入養蠶採茶的時節,就會臨時更換一批工人,只要過了這個時節,雇主再讓她們重新返回工作崗位。總而言之,凡是屬於工人階層,他們就會被換來換去。現在,大多數的工廠工人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柳田國男舉出這些實際案例,忠實反映出他對於當時勞動力受其時代的影響。這個社會事實恰巧也引證一個尖銳的反諷:那就是一旦打贏戰爭,國家就可以獲得大量賠款,並促進養蠶與紡織業的繁榮,提前來到產業革命的門口。
參與起草併吞韓國條約
柳田國男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00年進入農商務省農務局工作,成為明治政府的農政官員,同時他也以客座講師的身份,在早稻田大學講授農政學。眾所周知,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是培養日本高等優秀人才的學校,能夠從那裡畢業自然被視為飽學之士,可以在大學裡執教。從那個時點來看,日本帝國已經取得臺灣這塊南方殖民地,柳田國男雖然是明治政府的官員,並沒有被派駐或擔任殖民地官員的經驗。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柳田國男與殖民地政策毫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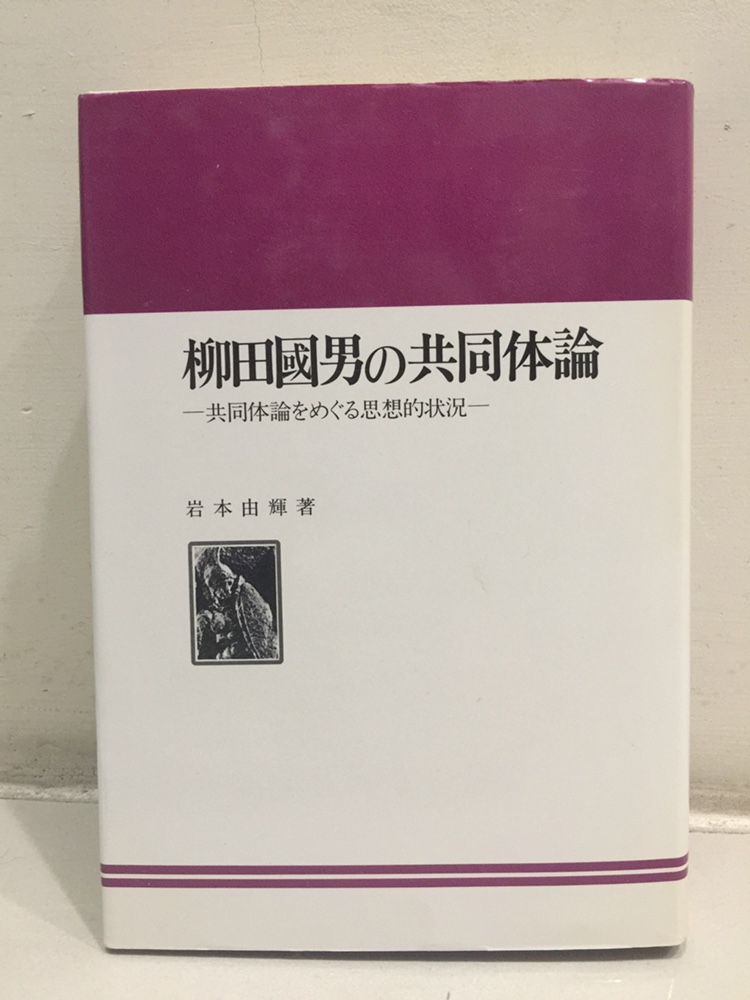
根據柳田國男研究專家岩本由輝指出,1902年2月1日,柳田國男被任命為內閣法制局參事官,屬於職司「關於內務外務軍制教育及帝國議會之事項」法制局第一部。翌年12月5日,該部裁撤之後,他依然從事舊第一部業務,參與過1910年8月22日簽訂《關於韓國併合之條約》的草案。令人詫異的是,該年6月,其代表作《遠野物語》由聚精堂出版,這不由得讓讀者產生了錯覺,懷疑這是出自同一個作者?或許柳田國男自知立場矛盾和尷尬,對於參與起草的事情閉口不談,遭到質疑時即辯稱,「韓國皇帝」依自己之意志提出「譲与韓国全部に関スル一切ノ統治権ヲ完全且永久二日本国皇帝」,而他只是按其原意「日本国皇帝」採取「譲与ヲ受諾シ全然韓国ヲ且つ併合スルコトヲ承諾ス」之形式條文起草的。這就是說,他並未實際參與條文的修訂,只是遵照韓國皇帝的意志起草而已。然而,1911年6月13日,我們從明治政府依「韓国併合二関シ尽其功不少」授予柳田國男五等瑞寶勳章來看,似乎更能說明他在這條文中所發揮的助力。而且,這次受勳的高等文官共有92人,包括內閣法制局參事官柳田國男等4人。當時,內閣法制局專任的參事官只有9人,柳田國男之所以論功得賞,絕非無足輕重的事情。另一方面,柳田國男那個時期的發言,充滿強勢的官方色彩,而引來不必要的反彈。他曾經得意談到任職法制局的優勢地位。例如,他說「政府官員以法定之自由,可觀察時事批判(國家)政策,任何細小之案件,准許與否全由己裁決,但每日皆需議論以終……」。於是,有論者批判,柳田國男在「關於日本帝國併吞韓國以及相關協約和法令」時,正反映出自己前後矛盾的政治修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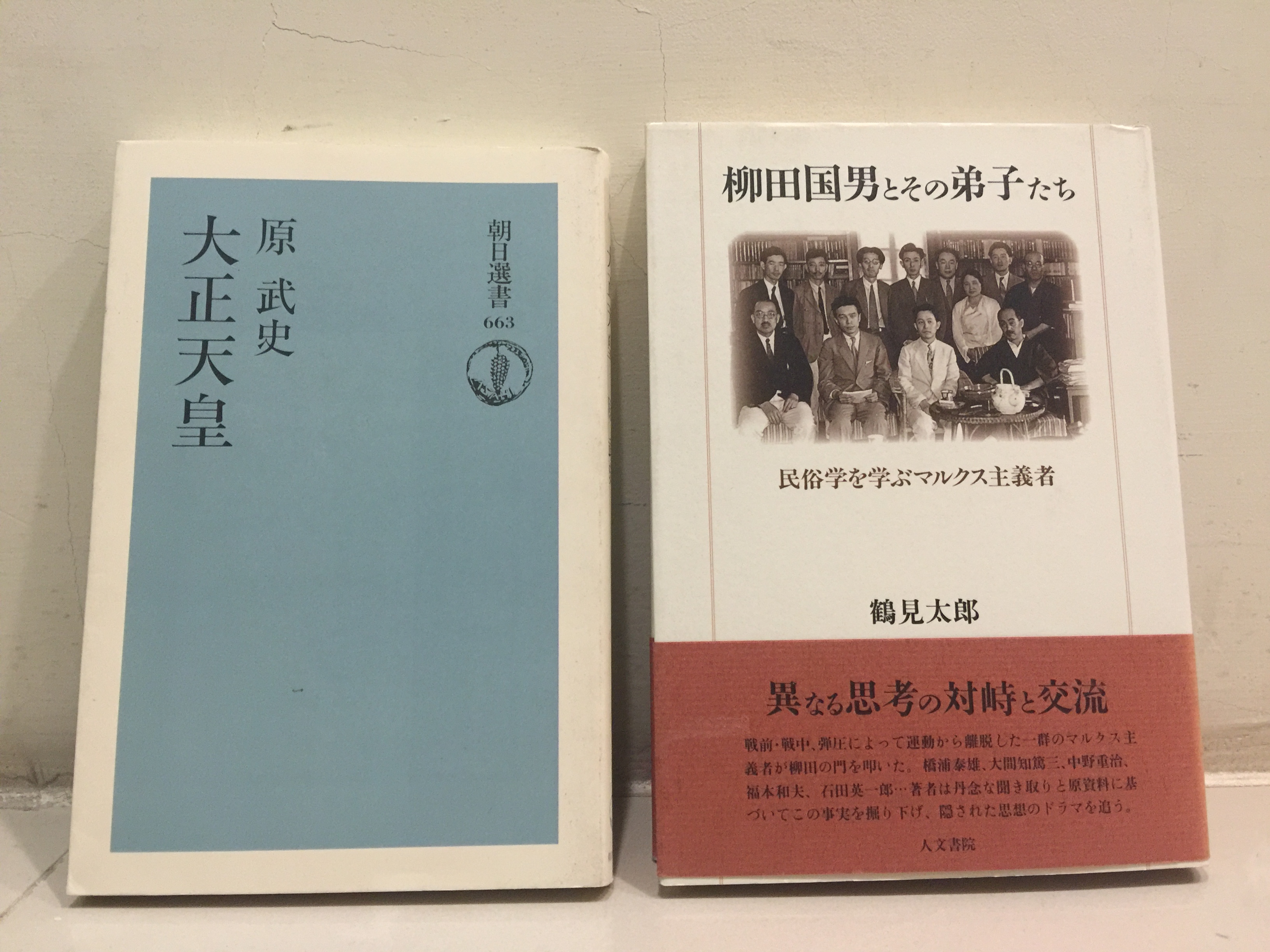
震撼日本帝國的噍吧哖事件
在此,必須特別指出,1915年6月發生的西來庵(噍吧哖)事件,很大改變著日本殖民臺灣歷史的航道。關於這起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最大規模和死傷人數最多的武力抗日事件的研究甚多,新近出版的《臺灣憲兵隊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6月)中譯本,即是稀見史料的出土。毋庸置疑,這個武力抗日事件的始末,同樣進入了柳田國男法制調查的視野裡。彼時,柳田國男擔任貴族院書記官長,是年5月1日,其妻的叔父安東貞美前往台灣擔任臺灣總督,為臺灣日治時期第6任總督,成立「台灣勸業共進會」,開始開發太平山、八仙山、以及宜蘭線、屏東線鐵路的開工。由於噍吧哖事件的影響層面甚大,當時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內田嘉吉引咎下台,由下村宏接任,柳田國男正是由下村宏推薦來到殖民地臺灣考察的。根據臺灣總督府統計,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臺灣各地,被捕人數多達1,957人,日本帝國基於《六三繼續法=三一法》,除了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以外,高達866人被判處死刑。其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的輿論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771人)被特赦為無期徒刑(引自維基百科)。其後,是年12月至翌年3月,在第三十七次帝國議會的眾議院和貴族院的本會議以及預算委員會中,認為這起鎮壓事件手段極為殘暴,被判處死刑人數過多,並追究安東貞美的政治責任,而貴族院一連串的審議,就是在時任書記官長的柳田國男面前展開的。岩本由輝《柳田國男の共同体論》一書指出,關於這起事件的經過,柳田國男曾經在《故鄉七十年》一書中提及,但在他看來,為了減輕安東貞美的政治責任,柳田國男明顯而刻意隱瞞事實。
1916年1月28日,在貴族院預算委員會第六分科會上,經由柳田國男的推薦,擔任民政長官的下村宏出席會議,他們以閉門會議的形式對事件主因做證。因於那是閉門會議議事錄中的做證內容亦被刪除,事件真正起因:日本殖民當局為了掠奪臺灣林地所致。為了防範類似事件發生,下村宏認為臺灣林地的問題迫在眉睫,因此敦請柳田國男來研商對策,因為柳田國男任職內闆法制局參事官時期實際參與過日本山林的調查。另一方面,柳田國男為了讓妻子的叔父安東貞美穩坐臺灣總督府,也做出了積極回應。他於1917年3月20日至6月2日,前往臺灣、中國、朝鮮旅行之際,於3月30日至4月4日,特地前往臺灣的山區視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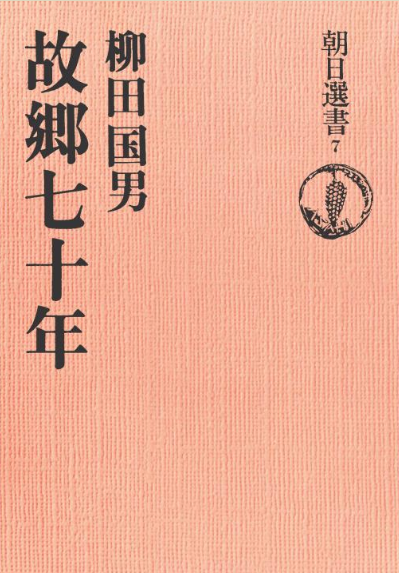
那次旅行的經過,柳田國男在《故鄉七十年》裡,這樣描述,「此行,並非下村(宏)為款待我,特意邀我前往臺灣」進行官員接待的訪問,而是需要我具體提供改善殖民地相關政策。熟悉日本文壇史的讀者知道,小說家田山花袋與柳田國男同為文學之友,他聽完柳田國男的臺灣旅途見聞以後,把它寫成了小說,題名為〈山區的巡查們〉,發表於1918年《雄辯》雜誌正月號,小說主角「A長官」就是以柳田為原型,而「H」=南投廳埔里,其內容「前來調查林業;想不到,問題沒想像中簡單……」,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日治時期臺灣林地的問題與弊病。
確切說來,日本內地官員前來臺灣視察林地,畢竟不宜大擺陣仗,更不能堂而皇之,避免官員接待引來側目,所以才以旅行名義而來。柳田國男視察臺灣林地之時,除了下村宏同行之外,還有安東貞美的女婿廣東總領事太田喜平,這真是一次奇妙的組合。下村宏與柳田國男視察山地之後,於5月3日至8日,在總督府殖產局林野整理課長鈴木三郎的陪同下,前往在西來庵事件中死傷人數慘重的噍吧哖(玉井)巡視。有趣的是,柳田國男前往殖民地臺灣旅行,後來竟然衍生出與小說家島崎藤村產生芥蒂的插曲。柳田國男在《故鄉七十年》中回想,他在台北與島崎藤村的哥哥秀雄見面,他告訴秀雄如果藤村問起,就說他來臺灣「是受安東總督講情有人要讓出某個林地」,但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他是專程為調查因抗日事件而衍生的臺灣林地問題而來,島崎藤村知道真相後大為不悅。然而,對我們來說這些意外的歷史插曲並不重要,也無法消除柳田國男到殖民地臺灣之旅的足跡,我們經由這歷史性的回眸,進而認識柳田國男在政治立場與戰爭觀的精神面貌,一個矛盾與統合的心靈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