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往前閱讀:
作家的還魂丹——截稿時間(上篇)
作家的還魂丹——截稿時間(中篇)
江戶川亂步
正如前述,許多日本作家想盡辦法最後仍然沒有戰勝截稿時間,而成為稿債的逃兵,受到經濟收入和自我良心的譴責,有的作家因此變得裹足不前,發誓再也不幹這種苦差事,不如改行來得痛快。然而,寫作本身和作品完成所帶來的心理滿足,終究輕易就能擊退這種沮喪時的想法,說它是虛榮心並不為過。著名偵探小說家江戶川亂步,他對於截稿時間(還魂丹),有著別樣而積極的看法。他在創作談〈三つの連載長篇〉一文中,毫不隱藏地顯現出其愛與怕。按照他的寫作年譜來看,他於大正14年正式成為專業作家,與之前相比,創作量的確增加不少,共計寫了17部短篇小說和6篇隨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翌年(大正15年)才是他的創作高峰,寫出5部長篇小說、11部部長篇小說和23篇隨筆。不僅如此,他同時撰寫3部連載長篇小說,年初還得為月刊、雙周刊、周刊供稿,可謂忙得不可開交。說到這裡,讀者或許會感到好奇,他是如何使命必達完成這大量約稿的呢?即使他在寫作領域春風得意,難道就不曾失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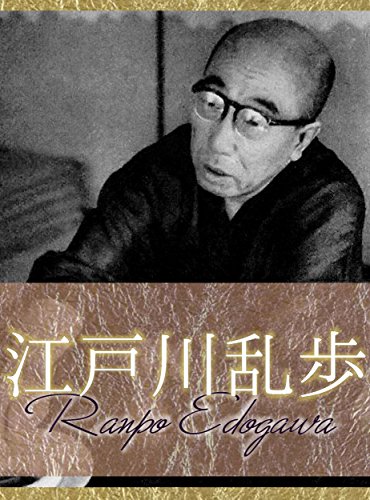
據江戶川亂步說,他於大正14年,創作了《苦樂》和《人體椅子》兩部小說,獲得很大的回響,為讀者票選的第一名。這個殊榮很快將他的寫作事業,推向了新的高峰。雜誌社總編輯見機不可失,立刻向他約稿,從該年的正月號開始撰寫連載長篇小說。剛開始,對此他猶豫過,因為他原本只寫短篇小說,缺乏撰寫長篇小說的經驗,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在此,他所說的長篇小說,是指正宗的情節內容首尾相通的寫法,而不是單純的篇幅擴增。在他看來,當時《苦樂》是雜誌社向他約寫的首部長篇小說,自然是作家的美事,但他擔心把它寫壞了,很想把它辭掉的。後來,他表示抵不住虛榮心的誘惑,當紅作家的光環,以及新聞記者的性格,不掂量自己的實力,就接下這個挑戰了。當然,這其中還包含專業作家的現實問題,他們必須大量撰稿產出,才有相等的稿費版稅收入,相反的,敝帚自珍似的純文學寫作方式,就與大眾讀者和稿費的距離更加遙望了。江戶川亂步是深諳這個道理的。因此,在神聖的稿費面前,他只能硬著頭皮,一面寫作一面摸索。令人玩味的是,作家愈是浸身在這種狀態中,就愈能更早參悟到個中三昧,有些作家的文章風格,便是經此鍛鍊形成的。
江戶川亂步坦承道,他接下長篇小說的約稿,第一次寫了40枚稿紙(大約16000字)交稿,那時儘管他已寫下故事大綱,但是小說如何結局並不明確。總而言之,在截稿期限之前,他就得想方設法把連載的稿子擠出來,完全沒有打混推拖的餘地。所謂工夫不負苦心人,江戶川亂步付出實際的勞作,還是受到高度肯定的。當時,雜誌社推出偵探作家系列作品選的特輯,他總是擔任先發的作家打響雜誌社的名號。作家交稿賺取稿費之外,有時雜誌社還安排旅遊行程,慰勞作家的辛苦。他說,長篇連載《苦樂》第一回刊出後,大獲讀者的好評,為此雜誌社總編輯招待他前往六甲苦樂園泡溫泉。根據他的回憶,他們在浴池中裸裎相見的時候,該總編輯稱讚他,第一回連載的稿子,頗有谷崎潤一郎的文風……。從這個意義來說,或許這是截稿時間對他的回報,溫泉消解作家的疲累,又得到前輩作家的比興和讚譽,這樣的報酬真是無比殊勝。這裡存在著一個巧合。谷崎潤一郎(1886-1965)比江戶川亂步(1894-1965)年長八歲,他們卻同年同月辭世;江戶川亂步於該年7月28日逝世,谷崎潤一郎歿於日7月30日,兩名作家相差二日離開了人世間,但他們都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重要的足跡。

橫光利一
儘管作家深切明白還魂丹的功效,最終卻基於各種不可抗拒的因素,無法準時償還稿債,但是認真細究原因,還真是無奇不有。與川端康成齊名的新感覺作家詩人橫光利一(1898-1947),就是典型的例證之一。從他的自述中可以發現,其對於天氣的變化是格外敏感的,或者說,他的寫作順利與否幾乎受制於天氣和時辰,由它們當家做主。他在〈書けない原稿〉文章中,提及為何遲延交稿的原因。他很相信命理師的說法,出生時辰對於自己的影響。例如,他於3月份早上出生的,這注定他每天早上的幾個小時裡渾渾噩噩打不起精神來。而在現實的生活裡,亦是如此。某人於早上來訪他,那一天就諸事停擺了,渾身不對勁,直到下午,他才能逃出那種難以名狀的混沌狀態。而且,在那種時刻下,他任由對方高談闊論,自己只能忠實的聽者。

根據橫光利一自述,他25歲以前完全不受氣候以及當日的天氣的影響,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在他30歲以後,天氣變化卻開始影響他的身體機能,支配著他的生活步調。此外,只要有人向他約稿,他多半不拒絕,儘管如此,他還是欠下稿債。在他看來,約稿表示對方的好意,他沒有拒絕的道理,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就應該寫稿以酬。殊不知,作家想破頭腦寫不出稿子,就如同面臨凌遲的酷刑。進言之,編輯或雜誌社記者,一開始即抱持逼死作家取稿的想法,那麼對方的動機就已變質,從好意變成赤裸裸的利慾導向。更有甚者,當他答應卻沒能如期完稿,有些品格低劣的雜誌記者就會匿名惡言攻擊他。然而,與此相反,有些雜誌社的記者人格高尚,即使他欠稿過久仍然會耐心等候,讓他甚為感動,因此當他終於起死回生似的完稿之際,必定會先捎寄給對方以回報這份情誼。
詩人橫光利一堅信,人品高尚的記者齊聚的地方,才可能產生優良的雜誌。以他切身經驗而言,某雜誌社記者向他約稿,每個月上門三次關心進度,他卻拖了一年仍未交稿。每次看見記者上門,他總覺得應該盡早完稿,否則實在過意不去。可是他有時認為,若因人情因素而倉促成稿,豈不是辜負對方的好意,自己也於心不安。而愈是這樣思來覆去,他愈寫不出稿子來,折騰了一年,最終無法順利運筆成篇。沒錯,對作家來說,沒有比稿債壓身更難受的了。相反,當他確實地交稿才能算是如釋重負,如卡奴還清他長年積欠的債款一樣。另外,橫光利一有其作家的堅持,他不喜歡雜誌社記者以苦心之名,或者為了他們的需要,而擅自更動他的文句,把原來一個句子切成兩句使用,這樣做,就是不尊重作家創作的初衷。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堅持和方法。橫光利一的寫作習慣很特別,他總要提早一個星期交稿,否則就失去寫作的動力。這有兩個原因:首先,他認為剛剛完成的稿子,必有不妥善之處,他很在乎讀者的批評。其次,每次完稿後,他立即放入壁櫥裡,徹底忘卻這份稿子的存在。七天過後,他取出稿子細讀,這時就會發現文章中的缺點。問題是,那時截稿日期逼近,已經沒有多餘時間重寫,最後只能做到訂正或校改錯字而已,那一星期的靜置時間,好像毫無幫助似的。迫不得已,他把稿子關進了壁櫥,七天後又悄悄取出重讀,這時偏偏有訪客上門。這樣一來,其冷靜客觀的閱讀受到了中斷,又得把稿子送進壁櫥,再等上一個星期。情況很糟的時候,他一直在重複這種苦難的過程。這麼說,並不表示他把純文學推到至高的頂點而視金錢如糞土,他甚至認為生活高於文學藝術,這完全是其寫作習性使然。
我們再次回到橫光利一寫作的動能受限於天氣制約的話題,同時亦可把它視為作家寫作行為的重要參考。他舉例說,某日他在悶熱的房間寫作,突然雷電交加,雨勢沛然而至,這時他就會打噴嚏,不想繼續寫作了。因為他剛才在斗室裡振筆疾書之際,已忘卻了暑熱,當他感受到舒適的涼意,自然更想沉浸其中。他比任何人明白,接下來他的文章必定會受此涼意的影響,就此轉變調性,與他先前的構想迥然不同。此外,他對於風很敏感,討厭風的吹襲,總覺得風挾帶著雨絲向他撲來。他說道,在下雨的某日,雜誌社記者上門催稿。說來這令他備感壓力,對方為了其一篇小說,三個月內來了六次。他每日寫不到300字,五天之內,勉強擠出2千字左右。
直到第六次的時候,一件事情讓他擱筆不寫了。那個記者忽然冒出了一句:「我們最終還是沒收到正宗白鳥先生的小說稿子呀……」準確地說,正宗白鳥(1879-1962)是橫光利一所景仰的小說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與這位卓越的作家在同個雜誌刊登,偏偏那時他又陷入寫作困境,前輩拖稿的消息,自然使他更意興闌珊了。對橫光利一而言,寫不出稿子的時候,真的是束手無策,他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整日在屋子裡兜繞。分明沒要事可做,回過神來,他卻發現已在廁所裡,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接著,他用額頭輕撞著拉門格子,懊惱地說,「我到底為何寫作呀?」或許,那時他終於領悟到寫作的奧義,它無非就是對於精神勞動的記錄。
遠藤周作
相對於其他作家面臨截稿大限而焦慮不安,以自律甚嚴聞名的遠藤周作也不例外,他同樣沒能擺脫這種狀態,只不過,為了健康著想,他不挑燈夜戰,而是固定在早上九點寫稿,吃完午餐,立即回到桌前,一直坐到暮色降臨。然而,這段伏案苦思的時間,並沒有任何文字產出,多半只是呆坐著,時而玩弄著鉛筆,時而掏挖煙斗屑,同一份報紙版面看了好幾次。具體而言,他整日都焦灼地構思著文稿的進行。有個作家同行告訴遠藤周作,他三天不寫稿,就渾身不自在,奇妙的是,若順利交稿這種病症就頓時消失。不過,他的情況不同,每日從早到晚,因寫不出稿子而頭疼不已,宛如吃下的年糕沒消化堵在胃裡般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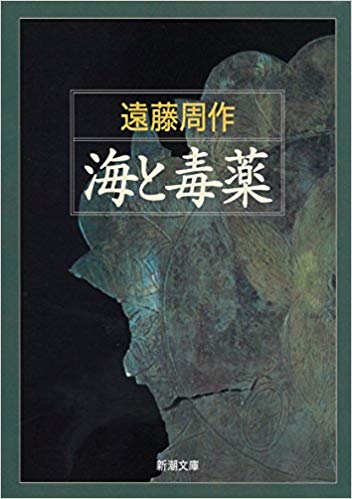
在寫作方面,遠藤周作有個習慣或心理障礙,儘管已經設定主題,後續若沒浮現具體的影像(即使是飛鳥、樹木、電線桿等等),他就無法動筆了。這時候,他就會把玩手中的鉛筆,要不就是打哈欠,試圖從內心世界挖掘出什麼東西來。他與這些苦澀的經驗打交道足有十年之久。而困境終究是要打破的,這時他外出散心,搭乘電車或計程車,反正先離開令人苦悶的寫作環境,完全置身在交通工具裡,瀏覽著窗外的景色,心情自然要好上許多。當他經由這舒心的過程,抓到了具體的影像,就開始運用於小說中的哪個部份,也就是說,他在腦海中擬定草稿綱要,之後便進入寫稿狀態。
因此,對他而言,寫作之前構思醞釀的過程,遠比實際寫作的時候來得辛苦。有經驗的作家知道,一旦順利進入寫作狀態,自然就會左右逢源,不斷湧現新的靈感,讓作者寫得不可自休,甚至抱怨自己為何打字的速度如此緩慢。儘管如此,遠藤周作其自我否定的心理因素,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按照他的說法,有時候他的小說寫到一半,突然覺得不滿意自認為拙劣之作,他就無法往下寫了。果真,翌日拿出來重讀一遍,發現有很多缺點和敗筆,這樣的稿子,交予出版社的編輯,實在有愧於良心。在這時候,他就埋怨起為何要定訂截稿日期來逼迫日本作家準時交稿呢?相反的,若沒有截稿期限的話,或許他即能隨時坐在書桌上,削著鉛筆、伸懶腰、打哈欠,悠哉度過每一天。許多人以為,他的作品豐碩必然是傑出的小說家,他卻有著悲觀的想法,自己並非頂尖的小說家,否則不致於深陷在稿債的危機中,畢竟寫作過程中的油盡燈枯的滋味,實在不好受。他吐苦水地說,當他寫完三十枚(小說)稿紙,體重必定減輕三公斤,他愈加體悟到小說寫作這個行當,還真是有損身體健康呀。話說回來,幾乎所有作家都在抵抗截稿日期的公然威脅,但是最後他仍然很感念這帖還魂丹的裨益,它既是正面的催命符,也是拯救作家的良藥,因為沒有截稿日期,就沒有交稿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