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多年以前,我讀過若干日本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的著述,對他的文學觀點了解有限,一直很想購得其代表作《日本人精神史》(六卷本),後來這個小小的夢想終於如願以償。

不過我必須坦承,迄今為止,我尚未充分運用這套書籍。兩年前的冬季,我到北海道的函館旅遊,在市區走走逛逛,後來往山丘方向走去,卻意外地發現了龜井勝一郎的墓園,我在墓園前待了二十餘分鐘,並拍了幾張照片紀念。
如此說來,我與日本作家之墓真是緣份不淺。某日,我總覺得自己有點頹廢,渾身打不起勁來,有一種像日本無賴派作家的「無賴」(另種含義的無所依賴)之感。於是,我漫無目的往書堆裡翻動,順便查看這次攜回的書籍。在這批書籍當中,我重新發現高山秀三《蕩児の肖像:人間太宰治》這本厚書專著的時候,我的眼睛頓時熠熠生輝起來。我原先只是信手翻看,消磨時間的本意遠遠大於嚴肅的閱讀,可就是那麼巧合,我翻著翻著在這部評傳當中,竟然出現關於龜井勝一郎的論述,以及他對於太宰治其人其事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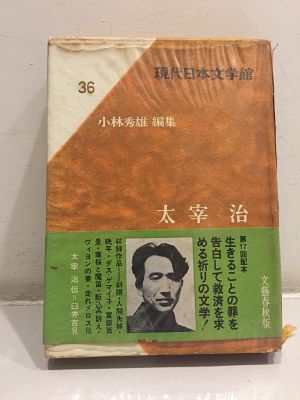
根據太宰治的傳記作家指出,太宰治於1936(昭和11)年6月舉行《晚年》出版紀念會,龜井勝一郎亦受邀參加此次盛會,他們就是在這場合上結識的。眾所周知,彼時太宰治過度依賴藥物的關係,這導致他的身體狀況衰弱, 虛弱到他最後上台發言時,若沒有人在他身旁攙扶隨時都會倒下來。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39(昭和14)年9月,亦即太宰治從山梨縣甲府搬家到東京三鷹市。就龜井勝一郎印象所及,那時太宰治從新居徒步到他位於吉祥寺的住處大約十五分鐘,在他看來那時太宰治很有精神。太宰治擺脫病懨懨的糾纏,顯然得助於他與石原美知子結婚,而擺脫晦暗的生活,精神方面也安定下來。確切說,在此之前,龜井與太宰之間並沒有深切的交誼,但某個時期,他們曾經是《日本浪漫派》的同仁,撇開這個因素不說,龜井本人很喜歡《晚年》這部作品。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就是相近的地緣關係。龜井勝一郎是函館人,太宰則是青森縣人,他們的故鄉僅隔著一道津輕海峽。他們在風土人情、食物和語言也有許多共同點。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太宰治自從落居東京之後,終其一生在公開場合上,他都不說東北方言,但是在私底下,他卻渴望傾聽朋友操著的津輕口音,因為這鄉音讓他感到心裡踏實。在思想行動方面,龜井勝一郎比太宰治更投入左翼運動,發表更尖銳的文章,只不過,他們後來放下激進的路線轉向文學活動,或許正是這個共同的默契,他們交談的時候都沒有觸及這個話題。
太宰治死後,龜井勝生郎寫過一篇文章〈無頼の祈り〉悼念這位無賴派作家。龜井回憶道,事實上,太宰治很風趣開朗,是個令人愉快的朋友。龜井進而自承,他原先傾心於武者小路實篤的處世風格,堅持奉行禁欲主義,滴酒不沾等等,可是太宰治卻教他飲酒的樂趣。據他的了解,表面上太宰不善於與陌生人打交道,初次見面的時候,的確有點害羞內向,一旦飲酒以後,卻彷若他人一樣,變得非常饒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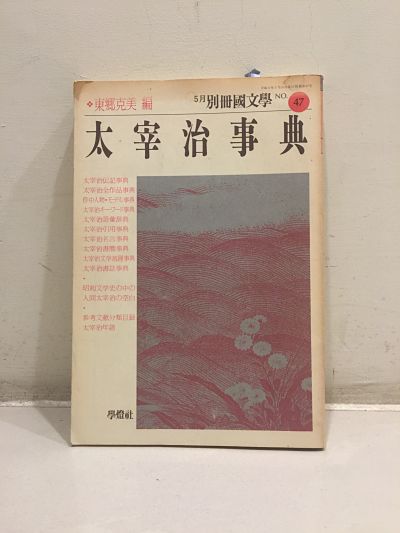
在龜井看來,太宰治是個率直之人,完全沒有頹廢的氣息或病態的神色。對太宰而言,他最嚮往的典型的友情,就是其筆下的《梅洛斯,奔跑吧!》主角了。就太宰治總是盡其所能地說笑逗弄大家的特點來說,他已在自己的小說中多次提及。在其長篇小說《不復為人》(人間失格)中,他即透過大庭葉藏這個主角,回述著他於少年時期,下課回家以後,肚子並不覺得飢餓,家裡的女傭男僕卻央求他吃點什麼東西,而他為了討取大家的歡心,卻故意配合演出直嚷著,簡直快餓扁了……。在短篇小說〈丑角之花〉中,同樣表現出生命中的滑稽身影,雖然是文學小說的體裁,卻頗富自傳性的色彩。
正如前述,他在半醉之後,樂於為大家帶來歡笑,藉著酒意調侃前輩和朋友,也毫不隱諱自己的情感,在笑談中表露內在的苦衷。然而,高山秀三在《蕩児の肖像:人間太宰治》一書中指出,龜井所看到開朗形象的太宰治確有其事,那時正值這位無可依賴的作家,在精神和身體獲得安定的時期,在這種良好的狀態中,埋在太宰治的意識底層的獻身精神更容易被激發出來。因此,在敬慕白樺派主將武者小路實篤的龜井勝一郎看來,那種樣態自然是健康而洋溢著青春活力。

然而,就實際情況來說,太宰治與龜井勝一郎交誼的時期,在小說創作上,確實頗為豐收的。例如《正義與微笑》(1942年)、《津輕》(1944年)、《惜別》(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5年)等等。相較於數次尋短未果的太宰治而言,龜井勝一郎自承,他從未想過自殺的問題。從這角度觀之,他愛讀太宰治的《晚年》,卻無法理解太宰治年輕時期的作品,像小說〈我很想尋死〉中的思想,他就是無法苟同和理解。但我們若換個角度,從太宰治的性格切入,也許可以找到些許線索。
青年時期的太宰治正值於日本施行政治高壓體制的時代,他與同時代的熱血青年一樣,對於社會的普遍貧窮、以及因此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抱以深切的憧憬,進而參與非法的共產黨活動。然而,他的革命同志看出他性格軟弱,不敢把危險的任務託付予他,而這個不可言說的心理陰影,最終還是滲入了他的生命深處,形成了他在自嘲與自我救贖之間的繩索。相反的,龜井勝一郎給人溫和的感覺,內在意志卻堅定強靭。也許,正是這個特質,使得他們走向不同的文學道前,龜井勝一郎成為傑出的評論家,而情感纖細易變的、甚至帶點神經質的太宰治,在生前即享有文名,與愛人投水自盡以後,其作品同樣引起持續的矚目。

太宰治不僅有許多忠實的粉絲,更有忠貞的追隨者……同為無賴派的作家田中英光(1913-1949)於1949年11月3日傍晚,在三鷹市的禪林寺太宰治的墓前,先是吞了300粒強效安眠藥和1800毫升的燒酒,用剃刀劃開自己的左手腕意圖自殺。彼時新潮社的編輯聞訊趕到,緊急將他送往上連雀的醫院搶救,但於晚間九時四十分身亡,享年36歲,可以說是英年早逝。總括地說,太宰治和田中英光這兩位無賴派的作家,活著的時候歷經諸多生命的困頓,離世時卻走得匆促,為後代的讀者留下了疑問,有關於掩飾鄉音的苦悶壓抑,有小說創作過程中的惶惑,這些難題都將隨著閱讀的進行得到呈現,也可能因於被日常生活的困乏壓垮而無疾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