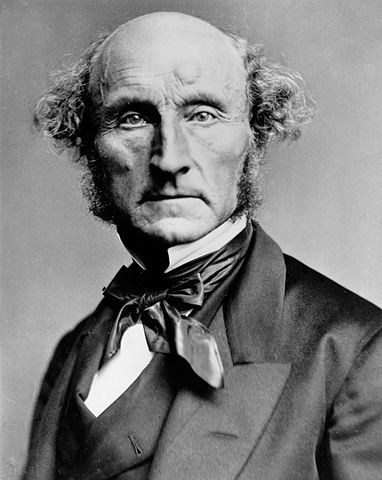曾擔任總統秘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秘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業餘興趣是研究中國天朝主義的系譜學批判。
六、帝國化與民主化的兩難
其次,林正修論及「中國政體的民主轉型」,在中國與台灣的天朝主義論述中,看似罕見稀奇。然而,這也凸顯了他試圖接合國民黨正統的小天朝主義思維與今日主流的天朝主義論述的做法,即便在天朝主義陣營內部,也勢必不受歡迎。雖然如此,林正修不愧為精明的說客,他既沒有明確界定「中國民主轉型」的內涵,也不斷藉由「不挑釁中國」、「要耐心等待」等修辭,來修剪他的「中國民主轉型說」。因而,實際上他的「中國民主轉型說」保留相當的「彈性空間」,只要一個華麗的轉身,就可以把「不能挑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當作「不挑釁中國」的基本元素,而從容地在「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的東方主義話語下,接受主流的天朝主義論述普遍論說的「人民社會優越論」,藉著將「人民專政政體」裝飾上一點「伊朗式民主」(如在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或「審議民主」(如在浙江溫嶺市)的,來證成和合理化對「公民社會」的全面鎮壓。畢竟,當初的清帝國王室,也是可以用「中國轉型的艱難」為理由來鎮壓革命黨人的,不是嗎?
此外,林正修的「民主轉型說」還刻意迴避了天朝主義論述內部最核心的疑難:對主流的天朝主義論述,近代以歐洲民族國家經驗為原型的代議民主與政黨民主體制,勢必會瓦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的「帝國遺產」;對他們來說,在當前中國以人民專政來維繫多民族國家統治的政治現實下,無法想像帝國性主權能與共和式民主調和共存。確實,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密爾早就發現,在多民族帝國下幾乎不可能實現他眼中的「自由制度」:各民族間缺乏共同情感,就難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輿論,從而也就無法建立真正的代議民主。上個世紀,在古老的鄂圖曼帝國,新生的現代改革派面對這個「共和或帝國?」的兩難,最終選擇了「放棄帝國遺產」的「小土耳其主義」,才勉強建立了今日人們熟知的土耳其,一個世俗性的民主共和國。但同一時期的華夏帝國內,自從梁啟超於1902年發明「中華民族」構想開始,國共兩黨雖在競奪國家權力上彼此是內戰中的敵人,卻都一致地接受「梁啟超構想」,選擇了「繼承帝國遺產」的道路,奮力營造「官方民族主義」取向的政治教化與文化規訓裝置,將現代的民族想像吸納進古老的帝國想像內,為古老的「帝國王權」披掛上時尚的「民族」外衣。
不論你要將這種政治想像和策略選擇定性為「帝國性的民族主義」或「民族性的帝國主義」,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百年帝國建設」的歷史積澱下,今日中國掌握發言權的社會菁英,幾乎都認為「中國民主化」是過度奢侈、無法負擔、脫離現實的幻想,不符合「大國崛起,重返帝國」的一般政治期待。就此而言,「中國民主轉型」的不可能性,中國權力集團的集體選擇所自我招致的「帝國問題」,源頭既非台灣的獨立主權對「華夏天下帝國」帶來的挑戰,也不是倚靠否定台灣主權的藍營小天朝主義論述就可以消弭。不過,林正修這樣經歷民主化浪潮而出頭的台灣社會菁英,在面對這種「帝國的疑難」時,居然會心生畏怯、裹足不前,別說去思考和抉發台灣主權在這種歷史脈絡下對「中國民主化」的積極意義,還附和意圖藉由消滅主權獨立的台灣而完成「春秋大一統」的儒教「天命神學」,以為這是實現「中國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依然讓人覺得悲哀。
七、「汎亞和平主義」作為「反帝的帝國主義」
最後,「汎亞和平主義」,也不是什麼台灣天朝主義的原創;而其實,林正修也不避諱這點,在論述上反覆援引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日本「帝國建設」進程中浮現的「汎亞主義」思潮和運動,來作為歷史的前例和類比。林正修運用這種歷史類比的手法非常有趣,充分反映了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論述近十多年來潛在的「帝國化」趨勢。儘管天朝主義「左派」一向給人仇視日本的印象,但天朝主義「左派」卻也是對日本上個世紀的帝國主義思維與方案最認真的學習者和模仿者。或許正是如此,20世紀日本的「汎亞主義」將亞洲人民從歐美帝國宰制解放出來的志向,是否還能完整無誤地移植到今日的國際社會?這個基本的問題卻鮮少被認真反思。
如果說在當年歐美殖民帝國主義勢不可擋的歷史背景下,以日本的現代化為支柱,來推進亞洲規模的「反帝國鬥爭」,還多少構成一個進步性的倡議,今日的我們難道不是早已知道這種「反帝的帝國主義」的巨大社會代價?以至於直到今日,還有諸多韓國知識份子認為,必須要推翻「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這類的帝國想像,以及從明治時期後以「亞洲團結」為大義名號的日本地域霸權,才可能找到東亞各民族和平共存的道路。
台灣的天朝主義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遊說韓國知識份子社群:這個願景很好──只要大家支持新的天朝霸權,就一定可以實現!關於這種「反汎亞主義的汎亞主義」,台灣的天朝主義者將一個基本的事實隱晦起來了:以中國的帝國式崛起為預設前提的「汎亞和平主義」,說到底也不過是另一種黑格爾形式的普世帝國論,認為唯有依靠霸權國家才能帶來「帝國式的和平」,此外就別無其他可行的國際和平模式;而以天朝帝國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與以大日本帝國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差別不過是將維持「帝國秩序」的中心從東京轉換到北京而已,不多也不少。當亞洲各國已歷經20世紀的「去殖民」歷史進程而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乃至東南亞國協都已運作多年,這樣的「汎亞和平主義」,除了為中國在亞洲周邊的帝國擴張,為中國取代「美帝」成為世界帝國的野心搽脂抹粉,除了是天朝版的「文明衝突論」,不知道還有什麼更進一步實質的「世界史意義」?
八、帝國想像的收驚儀式
對以「帝國治理的代理人和中間人」為自我定位的「公知」,這種「帝國式的和平」當然構成了不允許挑戰的「歷史先驗條件」,但對經受著帝國擴張而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卻定然絕非如此。林正修修正過的小天朝主義論述,還是不脫「炎黃世胄,東亞稱雄」的帝國心性:一方面要中國具備符合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民主民族國家傳統的表象,但同時又要中國保持「古典多民族帝國」的帝國本體,而且希望亞洲周邊的國家,能在一個「沒有大清皇帝的大清帝國體系」下,重新臣屬於華夏帝國在亞洲的歷史性帝國霸權。奇妙的是,經過20世紀,俄羅斯帝國瓦解了,鄂圖曼帝國瓦解了,乃至大日本帝國和德意志第三帝國也都瓦解了,為何這種將「民主化」傾向與「帝國化」傾向溶於一體的天朝主義論述,還能相信,中國這個「最後的帝國」,它的「帝國的回歸」,會是翻轉世界史的「最後希望」?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對林正修這位「汎亞主義最後的掮客」、「帝國和平最後的傳教士」,抱有無限的感慨。他的話語,毋寧像是趕在華夏帝國文明將衰而未亡之際,為天朝主義的信徒舉辦收驚叫魂儀式。但終究,他也無法逃脫天朝主義的帝國想像自我施加的兩難:要保持帝國主權的政治想像,就無法實現和平主義和「人民主權」的共和改革;要落實現代的民主共和,就無法保持以「天命王權」為政治基礎的帝國想像。林正修的視野隱含的問題,跟其他台灣從陳映真開始的天朝主義者是一樣的──一直要台灣人體貼「中國轉型工程的艱難與浩大」,卻從不敢向中南海說:請你們能理解,在一個人類歷史上的「最後的帝國」旁,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新興的共和國,是多麼艱鉅與偉大的人類事業。
擲筆前,只想說一句:正修,中國的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還是多關注一下平潭的台商,恐怕比較實在一些,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