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教育工作者,曾經幹過記者、教過書、作過研究,喜歡田野調查。
「基進側翼」議會入政的最後一哩路,功虧一簣,實是殘念。然而,更令人「殘念」的是,「基進側翼」入政議會之後的一項足以鬆動台灣基層議會現狀的任務,將無法實現。在入政選舉過程中,資源貧瘠到可憐的素人政團「基進側翼」的年輕參選人,愈選愈是想贏;因為,在選戰過程中,看見各黨派的議員參選人,似乎有著無止盡的資源投入,為的就是想勝選。常在跑選區過程中,更常聽聞某位候選人早已燒掉數千萬等令人咋舌的金額云云。

於是,基進側翼的素人參選人便自然萌生一個「問題意識」:話說議員可領津貼,包括為民服務費、出國考察費等等加總,一個月若以近20萬為計,四年頂多800萬,為何願意花費數倍的薪津金額來選舉呢?話說,「殺頭生意有人作,賠錢生意沒人幹」,為何長期以來,議員參選人縱然耗費鉅資,都想要參選呢?是想要撈個議員的虛榮頭銜來光宗耀祖一番,亦或撇開非法的貪污之外,台灣地方議會其實有著「制度性的『歪哥』」為灰色收入,因而讓人趨之若鶩呢?
換言之,若用經濟學的說法而言,「成為議員」有超乎議員公訂價格薪水的「尋租市場」此一看不見的好康補貼,不只將選議員的鉅額耗費給填補,甚至還讓每一位議員民代身家財產累積迅速。此種民代財產收入來源不明跟不合理,其實台灣人民長期了然於胸,卻也當成「理所當然」一般縱容。此種議員民代法定薪津外的「租」,讓一群覬覦民代尋租的爛咖,爭先恐後取得民代一職,於是,某種程度,議員競選的耗費亦就愈疊愈高,成了將素人公民排除參政的一堵高牆。

因此,撇開非法的貪污不說,此種鑲嵌於地方議會中的制度性「尋租市場」,究竟是怎麼運作呢?若能將之科學性地曝光揭露,則處於暗黑世界中的「民代尋租市場」,是否可能因為透由一手揭露而見光死,逐漸讓民代尋租市場的超額利潤逐步壓縮,造成「水清沒魚」,讓混水摸魚空間縮小,降低牛鬼蛇神類染指地方議壇的意願。如此,將可大為提升服務公眾為慮的有志公民,對城市政治與治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
當然,「開放政府」或者「政府透明化」或「議會透明化」不僅是學界討論「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指標之一,台北柯P政府據說也以此為方向指引。但台灣的「民代尋租活動」作為一種制度,並非法定程序的透明化可有效解決,因為台灣地方議會尋租活動,早已在行之多年之下成為一種「文化性」的制度慣習,箇中的「眉眉角角」就如同細節中的魔鬼,必須用人類學田野的眼光,才能洞穿這「眉角」背後的文化結構與邏輯。如果,用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武斷粗暴分野,社會學以工業社會或非國家集合體為研究之取材對象,那說好聽一點,台灣地方議會只適合那種研究前現代社會之部落集合體的人類學民族誌方式,才能有效理出跟厚描(thick description)那種已經鑲嵌成文化邏輯的制度慣行之「民代尋租市場」的眉角意義。說難聽一點則是,台灣地方議會那種狀態,根本無法用理論性或科學性較強的社會學加以理解,畢竟前現代的潛規則與地雷,遠非研究現代社會的理論科學所擅長之處。

因此,若能入政議會,基進側翼首先將用人類學民族誌的參與觀察,把地方議會當成人類學田調現場,進行議會現象尋奇式的診斷揭露。因此,基進入政議會的一個要務,便是想撇開過去「身在議會外」的外部批判,而是進入到裡頭,透由內部揭露進行解構,方能啟動宛如前現代方式存在的地方政治的再造可能。是故,不是傳統過往學術界那種研究「地方議會」,而是「到議會裡頭進行研究」,就學術研究而言,也可以填補台灣社會科學研究過於粗泛與理所當然,無法揪出窩藏在細節中的真正魔鬼,導致政治改革的幅度與深度過於表面。
蔡英文主席也曾呼籲李登輝前總統在近年大力推動的「二次民主改革」,但由於二次民主改革的震央必須從「地方政治」開始啟動,難度甚高;畢竟,台灣第一次民主化改革,是以「選舉」的徹底鬆綁為主旋律,而此種選舉輸贏作為執政誰屬的判準,懸繫於地方政治樁腳跟選票的基礎。若要將改革的刀砍向地方政治,難度勢必大增;因此,王城自內破,要破地方政治便只有從地方政治內部形成由下而上的內爆,跟由上而下的政治意志結合,方有李登輝前總統期待地從地方上啟動的二次民主化改革之可能。
因此,那天基進側翼入政功虧一簣之後的眼淚,不單是為了選舉落敗而傷感,而是對把議會當成人類學田調的可能夢想的消失、是對一種立基於對地方議會跟政治的人類學診斷,並以此進行揭露內爆的可能消失了,更是對期待從此種內爆中帶來台灣二次民主化改革能量的可能,就此消失了,感到悲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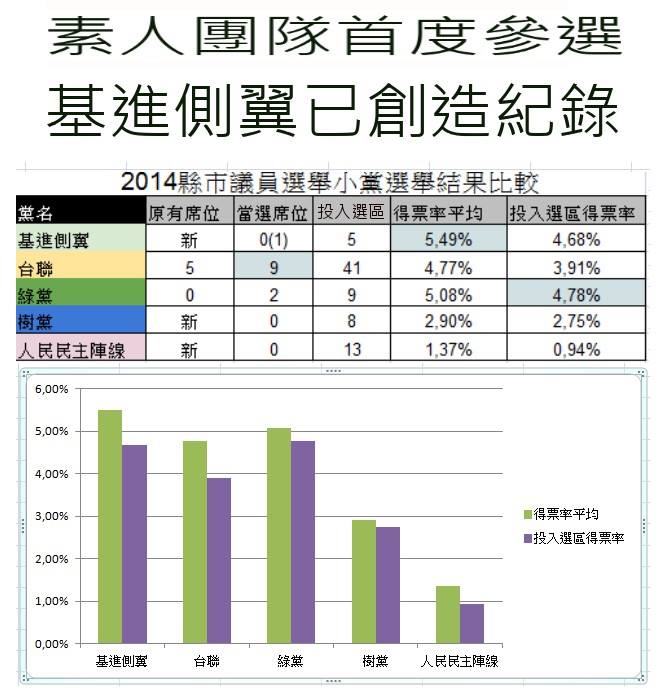
21世紀的台灣,卻有著「阻止地球轉」的19世紀型態地方政治運作邏輯;對此,台灣人民都深感嫌惡,但想揚棄此種落後的「基進側翼」,卻輸在想繼續封存此種遊戲規則的人的手中。不論如何,如同基進側翼的一位幹部所言,要看見日出,就須比光早一步抵達,那唯一的選擇,便只能在黑暗中就動身出發。
以此紀錄下,「基進側翼」那個想望但還尋不得的天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