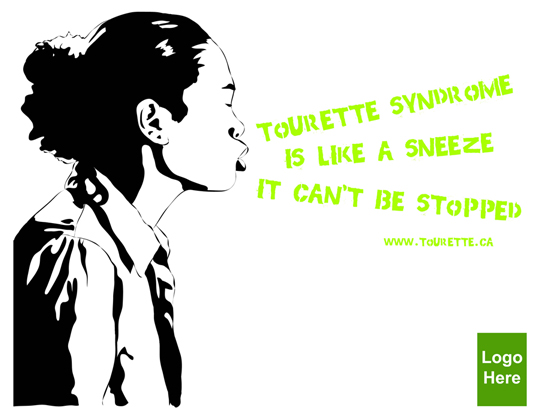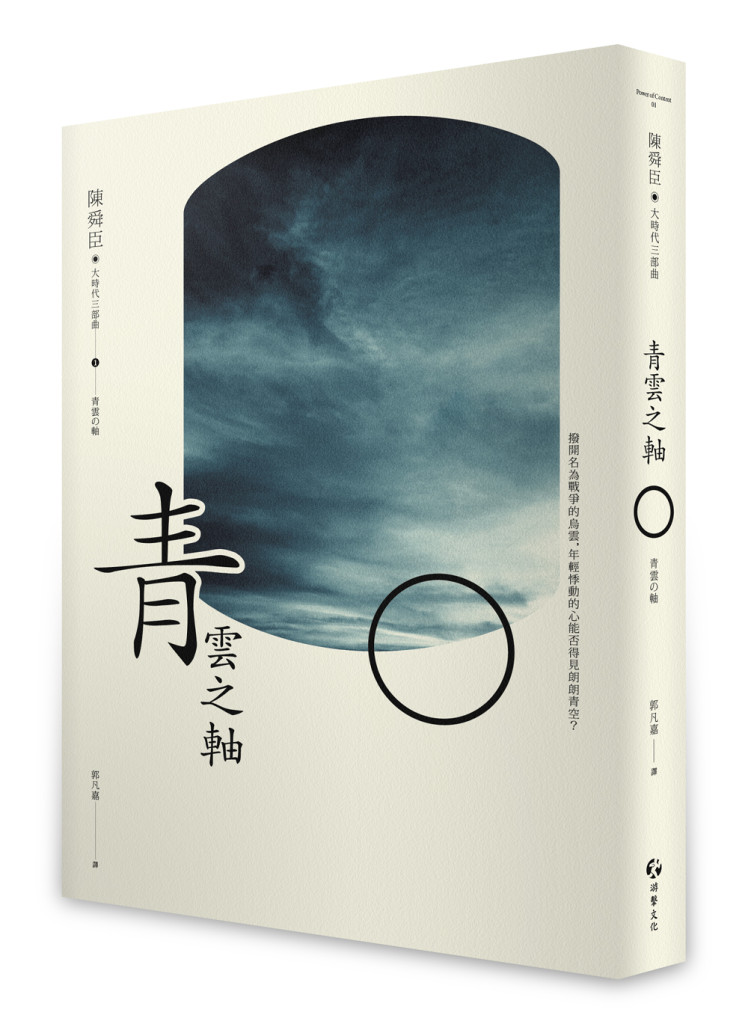「Why so serious?」「幹嘛這麼認真呢?」
──電影《黑暗騎士》小丑的經典對白
暢銷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與由其改編的電視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的作者George R.R. Martin,在一次《滾石》雜誌對他的訪問中,提到他小說中想要創造的世界,是一個即使有奇幻元素,卻仍然遵循現實法則的世界。也因此他質疑《魔戒》三部曲的作者寫得雖好,但是「善王必勝」的中世紀哲學式世界觀,卻和現實大異其趣:請問,亞拉岡的賦稅政策為何?《魔戒》三部曲結束時,魔王被摧毀了,但是山中還有許多半獸人,那麼亞拉岡應該去種族清洗,把他們全部殺光嗎?在現實中,光是用意良善並無法保證能夠妥善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