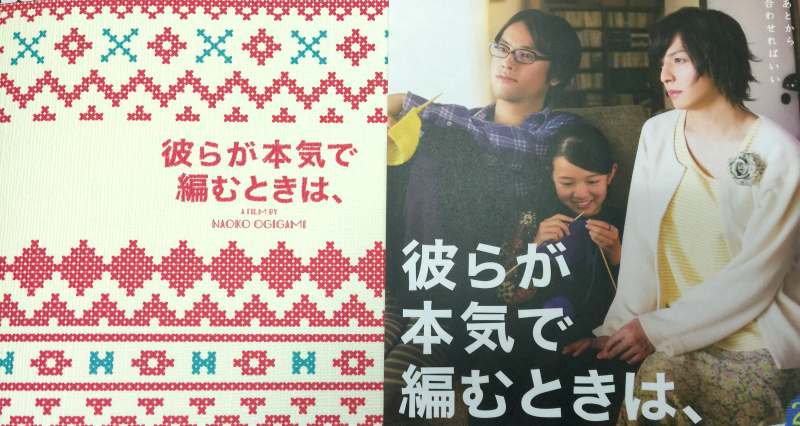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3月6日與3月7日是關鍵的轉捩點,蔣介石派兵陸續抵台,許多台籍菁英在關鍵的這兩日開始陸續失蹤。二二八這個大時代的悲劇故事,由於缺乏真相與元兇,故事都是由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記憶所拼湊起來。林界,一個外界不甚熟識的名字,從1947年開始迄今,他與他的家人,其實一直訴說著一個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時任《台灣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高雄市長黃仲圖邀請之下,在1947年3月6日上午與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父親)等人代表市民,攜帶《和平條款九條》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洽商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然而,3月6日下午開始,彭孟緝卻派出部隊鎮壓在高雄市區,更在3月7日以迫擊砲等重型武器攻擊高雄中學。3月21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槍決林界。
林界被殺身亡,留下了妻子胡錦華與三歲的林黎影、一歲的林黎彩兩姐妹。林界離開後8年,母親無法承受艱苦的日子因此自殺身亡,兩姐妹從此成為孤兒。
林界,是林黎彩那位相片裡的爸爸。林界,也是外省老兵廖中山那位未曾謀面的老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