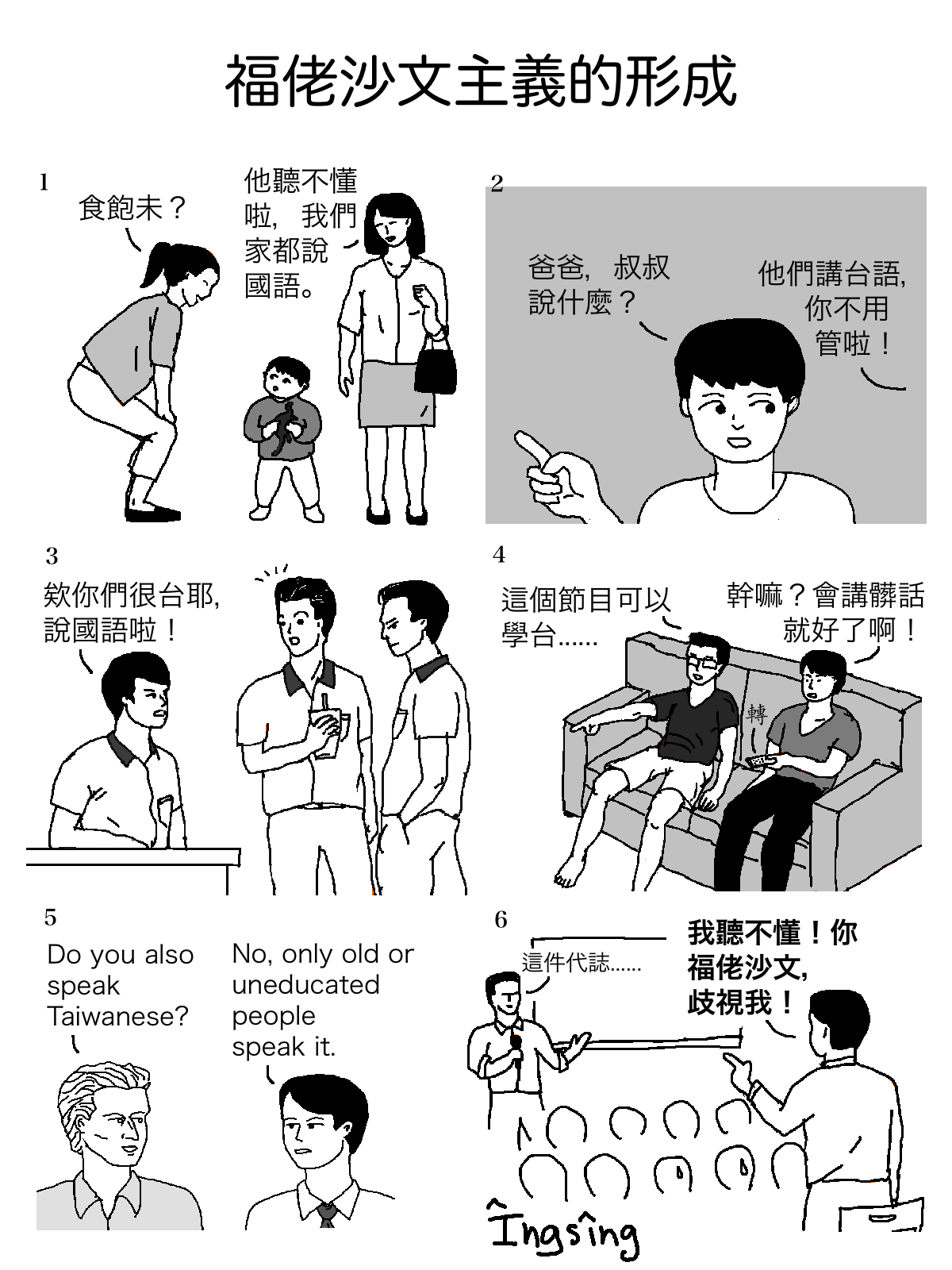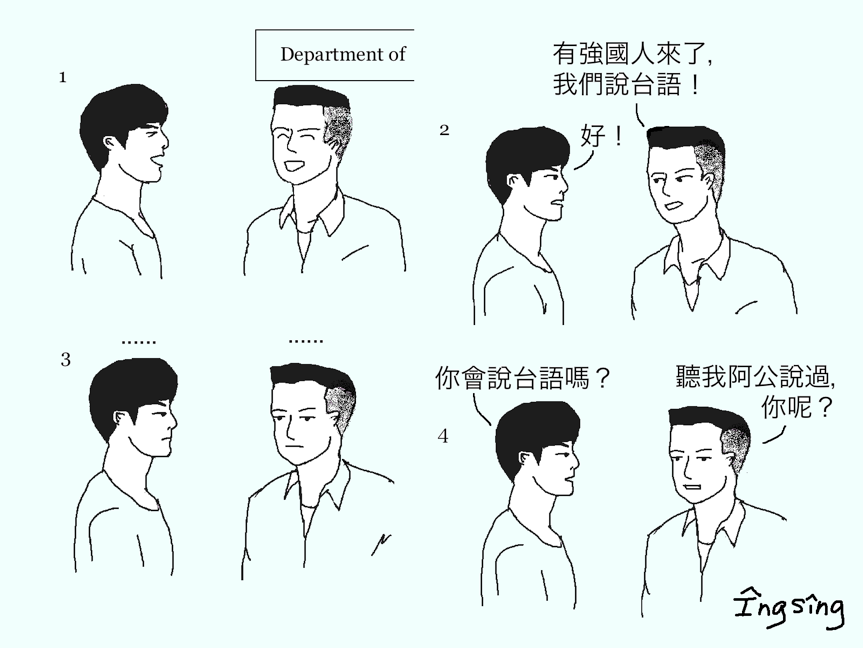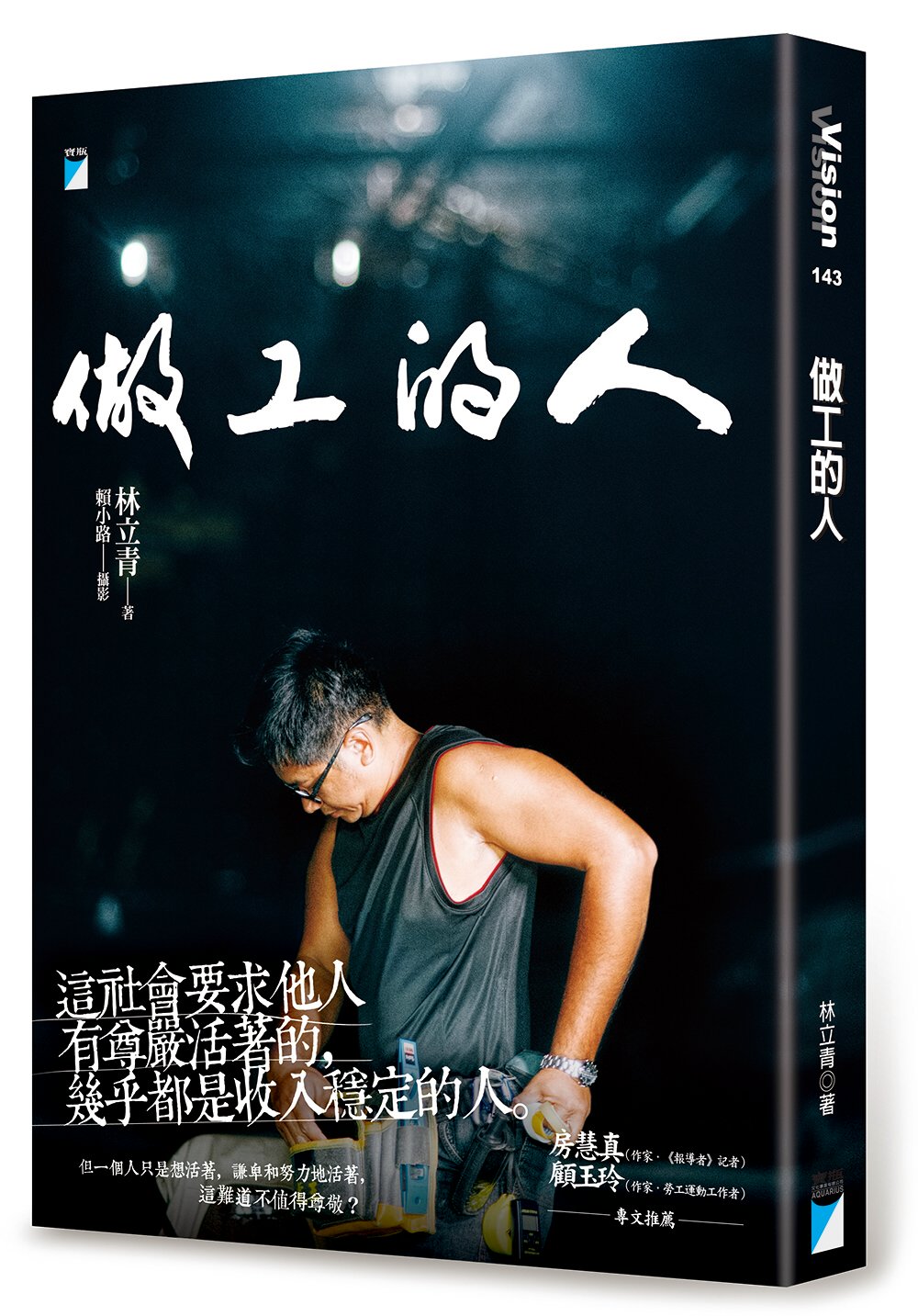童年時期的我,生長在物資缺乏、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十大建設正要開始展開的年代。玩樂的場所除了學校以外,就是家裡附近的田園、溪流、海邊;沒有3C產品、沒有制式玩具、更不可能有大型的遊樂場,但卻創造了無限寬廣與可能的玩樂空間、機會與方式。
收割後的稻田是孩子們的野戰場,順著稻梗抓上來的田土就是砲彈,稻草墩是躲藏的掩體,敵人衣服上的泥土印就是我們的得分點;收割後的稻田也可以是棒球場,報紙、水泥袋是自製手套最好的材料,竹棍、樹幹就是我們的球棒。一個裝奶粉或是裝鳳梨片的空罐子,就可以讓我們玩一整個下午的踢罐子躲藏遊戲。一小塊的紅磚碎片,可以拿來在地上畫上搶國寶、過五關、跳房子的遊戲圖。一根筷子、一支玉兔原子筆管加上苦楝樹的果實,就可以做一支打到人會痛的空氣槍。秋高氣爽的天氣,想放風箏,用報紙、細竹桿就可以做一只飛得又高又遠的風箏。生活周遭到處都有垂手可得的玩樂、遊戲材料、空間與機會,沒有任何大人教我們怎麼玩,就是大的帶小的,或是在旁邊看著看著就學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