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往前閱讀:【日晷之南】作家筆下的政治社會學: 選舉凶殺案(上)
在盛開的櫻花樹下
寒吉看到這番景致簡直不可置信,照理說,候選人這時候到處拜票才是,他也跟著來觀賞櫻花,這種做法令人難以理解!接著,寒吉手上拿著一個便當,若無其事地走過來,但沒有帶著大瓶的清酒。這是他的工作絕不許飲酒誤事呢。不過,他聽說三高吉太郎一行人事前已備妥若干大瓶的清酒了。照這情況看來,三高的手下們已經先送酒招待當地人(拜完碼頭)了。他進而推測,也許這是他們事先所布局的,接下來,就是與某些人暗自會合。
結果,三高與之會合的是那些面相凶悍的同路人。沒多久,他們一伙人全喝醉了,開始內訌似的爭吵起來。寒吉離開那裡,退身到其他的地方,繼續監視著他們。他不知道吵架的原因,雙方為什麼突然互毆起來。仔細觀察,只有同夥人的一方在吵架。打人的是其中一名助選員,而不是三高吉太郎。十分鐘之後,他們又圍成一團了,打架似乎結束了。同夥人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正要離去。他們又嗤嗤地笑了起來。其中一人哭泣著,受到同伴們的勸慰。原來那個哭泣者是三高吉太郎!於是,有若干男子簇擁著三高吉太郎回到宣傳車上。有趣的是,其他在場的賞櫻客們幾乎沒有察覺到,那個哭泣的人就是口若懸河的參選人。或許也是因為到處都有吵架喧嚷,不止是三高在哭鬧而已,各種各樣的醉客全來這發洩情緒,以致於沒引起很大的關注。最終,三高吉太郎一行人隨著競選宣傳車離去了。臨行前,三高吉太郎像個閙彆扭的小孩一樣,揮舞著手足大聲喊叫著:「啊,太無情了!不要放棄我呀。啊,太冷酷了,啊啊……」,而惹來在場的賞櫻人群捧腹大笑。這天,三高吉太郎的競選行程就這樣結束了。看到這裡,寒吉認為三高吉太郎藉酒澆愁的反常行為,注定這場選舉必敗無疑,但話說回來,三高選舉的成敗與否的確與他這個觀察者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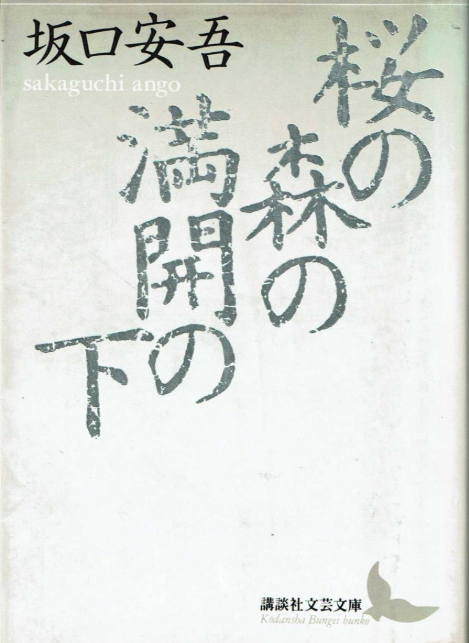
不為人知的祕密
翌日,寒吉正要前往上班,經過三高吉太郎的家門,剛好看見了一幅奇特場面:三高吉太郎立在宣傳車上準備出發,其家眷似乎來到路上目送他。寒吉發現,三高的妻子還很年輕,長得善良可愛,她還背著一個嬰兒。只見她搖動嬰兒的小手,對著丈夫說:「孩子的爸,加油!」看到這情景,寒吉不由得轉變了心意,或說要改變觀察的視角。他自承疏忽了,其實應該找來三高的妻子談談才對。他既然作為新聞記者,就必須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直接面訪三高的妻子打探實情。
「昨天,你丈丈喝醉了才回家的,是吧。」
「是的,他平常不喝酒卻……」
「哈哈,平常不喝酒嗎?」
「他是參選之前開始喝酒的,可他從來不曾醉成這樣子。」
「為什麼?」
「我不知道。這不是選舉造成的嗎?想不到他竟然出來參選。」
「太太的意思是,您反對他出來參選?莫非還有其他的隱情嗎?」
「有些人看起來會當選的就另當別論。我們可是花了大把鈔票呢,這簡直太愚蠢了!」
寒吉心裡嘀咕道,搞選舉又出來喝悶酒本來就很古怪,容易引來大家的猜疑。於是,他追問道三高的妻子:
「您是指他喝悶酒的事嗎?」
「當然是。我心情苦悶,也不想喝悶酒。」
「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參選呢?」
「事實上,我也想知道呢。」
「您是指他在喝醉的時候,總想說點心裡話吧。」
「如果是我絕對不說的。我心意已決絕不吐露出去固執到底。不過,我知道他好像有什麼隱情,他偏偏不告訴我。」
說到這裡,三高吉太郎的妻子聲音哽咽了。但對寒吉而言,倒是正中下懷。原來三高吉太郎出來參選竟然有所隱情,直到這一刻,這種埋藏內心的祕密,他仍然不肯向妻子透露分毫。進一步地說,三高作為參選人還沒正式敗選就逕自喝起悶酒了,這絕對是天下怪事?然而,三高吉太郎若知道下列的事實,不腦溢血倒下才怪:在現今臺灣的市長選舉中,某候選人僥倖贏得勝選以後,大頭病和自大狂發作,搞到睡前必須飲酒才能入睡、每日上班遲到、講話天馬行空、毫無邏輯可言,在每逢關鍵時刻,他為了拉高自己的政治量而胡亂放話,樂於造成社會大辭,發言的惡臭程度,足以壓倒1960年代的糞坑;尤其是,這種人說謊成性,以拉攏和圖利財團沾沾自喜,具有明顯恃強凌弱的暴徒性格,但他照樣坐領高薪享受社會學中的3P大獎:(Property、Prestige、Power)。幸好,三高吉太郎沒有穿越時空的本領,不知道邪惡政客的選戰充滿權謀,真要在公開場合掉下鱷魚的眼淚,都必須經過精密算計,絕不可以喝悶酒感傷哭鬧,因為那樣做與政治運作嚴重牴觸,也不符合政治經濟學。
因此,寒吉告訴自己,要繼續深掘這件事情,就不可躁進,因為截至目前,三高的妻子還不知道丈夫參選的祕辛,他有必要先取得其妻的信任,才可能抓到政治新聞的賓果。最後,寒吉對三高的妻子說:「這的確令人擔心。不過,三高先生也很努力了,您要盡量安慰並為他打氣呀。」她回答說:「我也是這樣打算。我在暗地裡為他拉票,能拉一票算一票。」或許三高的妻子政治敏感度不高,這番話立刻引來寒吉的提醒:「這可不行呀!你暗地裡替他拉票,這可是違反選罷法。」
在寒吉看來,普通民眾並不知道何謂「違反選罷法」,他這樣規勸三高的妻子,並不是出於真正的關切之意,反而像在突顯她所受教育程度不高。就此來看,儘管她是個善良的女人,平常大概很少閱讀報紙。不過,經由寒吉的說明,三高的妻子感受到這友善的提醒,她露出微笑,若無其事地說,「我所謂在暗地裡為他拉票,其實只是向神明祈禱而已!」
寒吉探查三高吉太郎參選的個中原因,總算比之前有所進展,他向報社主管做了報告。主管問他,他們一群人為什麼在櫻花樹下打架?寒吉只能簡略說明事情的經過,但尚未查出真正的原因。主管追問道,這樣不是很奇怪嗎?他既然出馬參選,為什麼瞞著妻子呢?寒吉被詰問得支吾其詞,有點沮喪和退卻,只好說,他會繼續調查下去,近日內,必定能得出滿意的結果。寒吉這樣說,後來他還是躲到博青哥店裡消磨了半天。說到底,寒吉畢竟是報社的社會組的記者,有仔細筆記的習慣,而且自律甚嚴,一有空閒,就會拿出筆記端詳硺磨。他在筆記上註記著:「他的眼神憂鬱,正好道出其內在心聲,所以只要掌握住他的眼神,就算是立下大功!他們喝酒打架的確是很不尋常的事。由此推估,三高在流鶯拉客的街頭演講,應該不是普通的把戲,我必須往下追查。嗯,我每天早上應該去訪問他的太太。」
就這樣,寒吉每日上班之前,向三高的妻子噓寒問暖,順便送上他在博青哥店換來的牛奶糖。隨著面訪次數的增加,寒吉與三高吉太郎的妻子建立友誼來,不再那麼陌生有距離。儘管如此,寒吉仍然沒調查出三高參選的真正目的,反而看到其妻子不像以前那樣愁眉苦臉了。於是,他試探地問道:「您先生當選議員,您就是議員夫人了。」不知什麼原因,她並沒有回答,這又讓寒吉有想像的空間,他暗自嘆息,她真是愚蠢的女人啊!他每日上午上門訪問,其實是另有所圖,她卻又覺得喜孜孜的,不知道人性的險惡。
不久,選舉結束了。三高吉太郎得到132票。從政治實力來看,三高吉太郎能夠得到百張的選票,終究是不容易。總而言之,一切順利落幕了。就在那時候,發生了一起詭異的案件,有人在小學的走廊上,發現了一具無頭屍體。而那間小學就位於「三高木工廠」的後面。據說,直到新聞截稿之前,警方尚未查出屍體的身份,在混亂世局中詭譎的氛圍如黑霧般席捲而來。

無名屍中的政治隱喻
不知什麼緣故,這起無頭凶殺案發生之後,寒吉心裡忐忑不安起來,卻又說不出具體事由。他總覺,這件事與三高吉太郎脫不了干係。「三高木工廠」重新營業了,回復到以前的光景。不過,寒吉仔細觀察,之前那些佯裝成助選員的人全消失不見了,他們到底躲到何處了?此外,那起恐怖的凶殺案,匆匆已經過兩星期,僵硬的屍體應該腐爛了。這時候,有好事者推理:死者應該是在賞花期間遭人殺害,小學的走廊上就成了棄屍地點,這是否牽涉到地緣關係?寒吉認同這個說法,自行推理調查:自賞櫻期結束以後,他再也沒看見三高吉太郎及其同夥的身影了。在那以後,寒吉都是在三高吉太郎開走貨車之後,前往他的家裡查訪。他進而聯想,如果那個充當三高的助選員男子(死者)失蹤了,總會有人騷亂起來,或者上門找人,問題是,又沒這種反常現象。寒吉決意打開苦悶的僵局,佯裝訪客來到了「三高木工廠」,他向一名正在工作的年輕男子問道:
「你老闆參加這次選舉,工廠的員工是否因此減少?」
「沒有啊,跟原來一樣。」
「那個年約四十歲面相凶惡的人不在工廠嗎?」
「四十歲的人?你是說這裡的老闆吧。」
「不是你們老闆。」
「我們這裡可沒有什麼四十歲的工人?一直都是年輕工人。」
「可是,選舉的時候,他還在的呀。」
「選舉期間,我們工廠停工呢。」
「那麼,他一定是去忙碌選舉的事。」
「選舉的時候,倒是許多人去幫忙。」
「你老闆在賞花地點演講,那名男子就在那裡。」
「這事我可不知道。對我來說,搞選舉最無趣了。你別再問了。」他氣呼呼地說,又不像是故意隱瞞,似乎很不想扯到選舉的話題。寒吉暗忖,這難道是其老闆的得票數過低嗎?看來只要提到選舉的事情,對方就露出輕蔑和彆扭的表情。他又想,這次又能向三高的妻子打聽消息,算是走運了。畢竟,選舉活動結束了,找她見面並不困難,也不必擔心被拒於門外。於是,寒吉趁著休假日,在超市門外守候了半天,總算等到三高的妻子從超市走出來。他立刻問到:
「選舉期間,有個助選員來為三高先生幫忙,他怎麼不見了?」妻子回答,「助選員都是我們的員工,他們都在才對。」
「可是他不在了。」
「不可能的,他沒有辭職呀。」
「我記得,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我第一次造訪貴府,就是他領我進來的。」
「你確定有那樣的人嗎?」
「有,我可以確定。他笑起來很誇張恐怖,神情有個瘋狂。」
「啊,我想起來了。你是說江村先生。他不是我們的員工,也不是選舉時的助選員。他偶爾會來幫忙,上次偷了錢,再也沒出現了。」
「他偷了你們家的錢嗎?」
「對,他偷走了十萬圓選舉費用。他的風評很糟,但我們沒有聲張出去。總之,他是個壞傢伙!」
「他什麼時候偷錢的?」
「我記不大清楚了。我丈夫說,可以借錢給他,但最後他沒有還錢。我們會想出辦法,請你告訴我丈夫一聲。」
「這種事可非同小可。不過,我只想看看太太您一面,順便打聽一下而已。他到底是何方神聖?他的面相很糟呀!」
「我們結婚之前,我丈夫就認識他了。我不知道他們的交友關係。不過,他這個人不好。我丈夫的朋友總是趁我不在的時候來偷錢,這點實在令人厭煩。他這麼亂搞,我丈夫大概不會原諒他。這是我的直覺。我們的員工都討厭江村這個人。聽說我丈夫出來競選,就是他在幕後操作的。」
「可是,你們不是沒有選舉總幹事和庶務主任嗎?」
「那是因為那壞蛋不想拋頭露面,結果,我們的選舉經費就這麼被他捲走了。」
「不就是10萬圓嗎?」
「您認為這不是一筆大錢嗎?」
「在選舉費用當中,這點錢的確不算什麼。再說,貴府不是已經用掉1-2百萬圓了嗎?」
三高吉太郎的妻子可能害怕這會觸犯選罷法,索性不予回答。
「您別誤會,我不是要向你們借款什麼的。下次,再去拜訪三高先生。」
「好的。我先生是個講信用正派的人。」
經過這番對話,寒吉刻意隔了三四日,穿著寬鬆的和服於晚餐後造訪三高吉太郎。三高一見到寒吉,立刻說道,江村是否向他借了什麼東西?寒吉沒有正面回應,直說他受害的最慘重呢!三高避重就輕地說,這也是選舉費用之一,不值得一提。現下,他不想再談選舉的事了。就在這時,三高的妻突然插嘴道,四、五天前,她把選舉的東西全燒掉了!工廠的年輕員工也惱火了,說競選辦公室的桌椅,一件不留全都燒掉了。這些東西都是多餘出來的,把它燒掉也不可惜。話畢,寒吉吃了一驚。他推測,這番話豈不證明要全部湮滅證據嗎?而且,再怎麼說四、五天前都有些時日了。那具無名屍被發現也第十天了。他們要湮滅證據的話,應該更早燒毀才是。他朝房間裡打量著,芥川龍之介和太宰宰的作品集不見了。只剩下一般雜誌。寒吉向三高問道,您不再閱讀芥川和太宰治的作品了嗎?只見三高的妻子代為回答:那些書也都燒掉了。三高無力地笑起了來,大概是苦笑說,尤其平常不讀的書,最好不要擺在桌上。寒吉繼續探問,您是指只有選舉的時候,才閱讀這樣的書嗎?三高回答,選舉之前,他就喜歡閱讀這類書籍,但這些全是自殺者寫的小說,寫得很無趣乏味。不過,只有那本書《悲慘世界》,他還想再讀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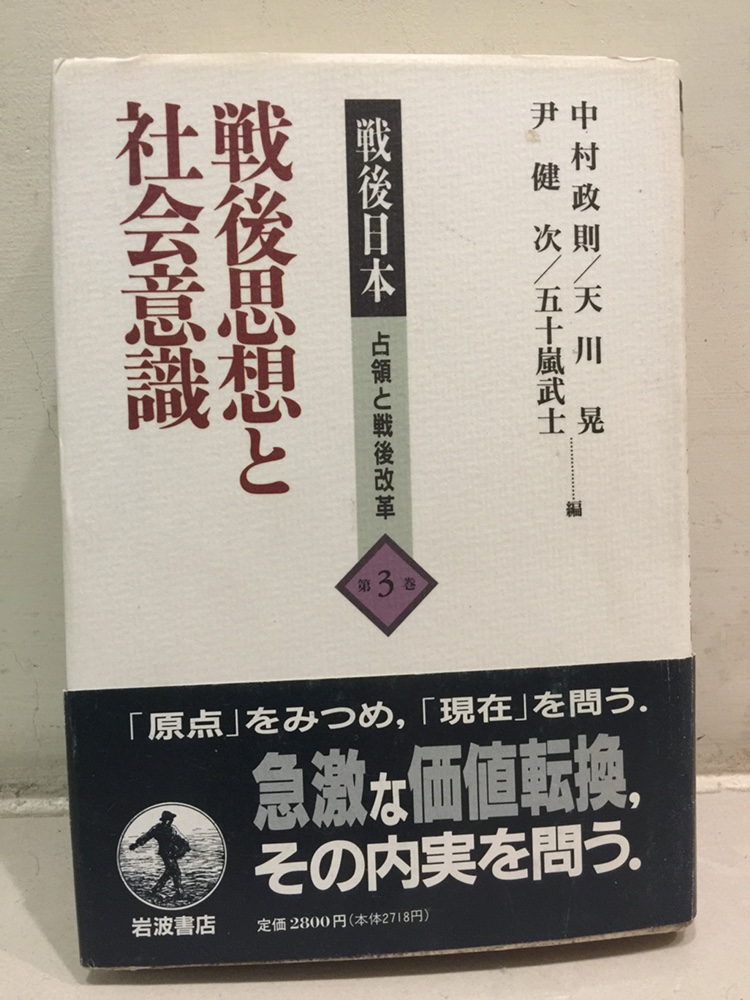

說到世界文學名著,寒吉忽然大聲說道,您說的是《悲慘世界》嗎?三高承認地說,就是主角「冉阿讓」啊,在他結婚以前,就喜歡這部小說。寒吉頓時啞然無言,因為《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形象,不就是三高吉太郎酒醉哭訴時的真實寫照嗎?三高似乎有點餘醉未醒,大概也記不得這段往事了。只是,他的表情依舊苦笑以對。三高強調,冉阿讓的說詞很有意思。然而,寒吉察覺到,三高的情緒有點失控,有一種萬不得已的苦衷。受到這股情緒的感染,他向三高夫婦告辭,疾步地回到家裡,立即打開他珍視的筆記本。他認為,這筆記將為他提供寶貴的破案線索。(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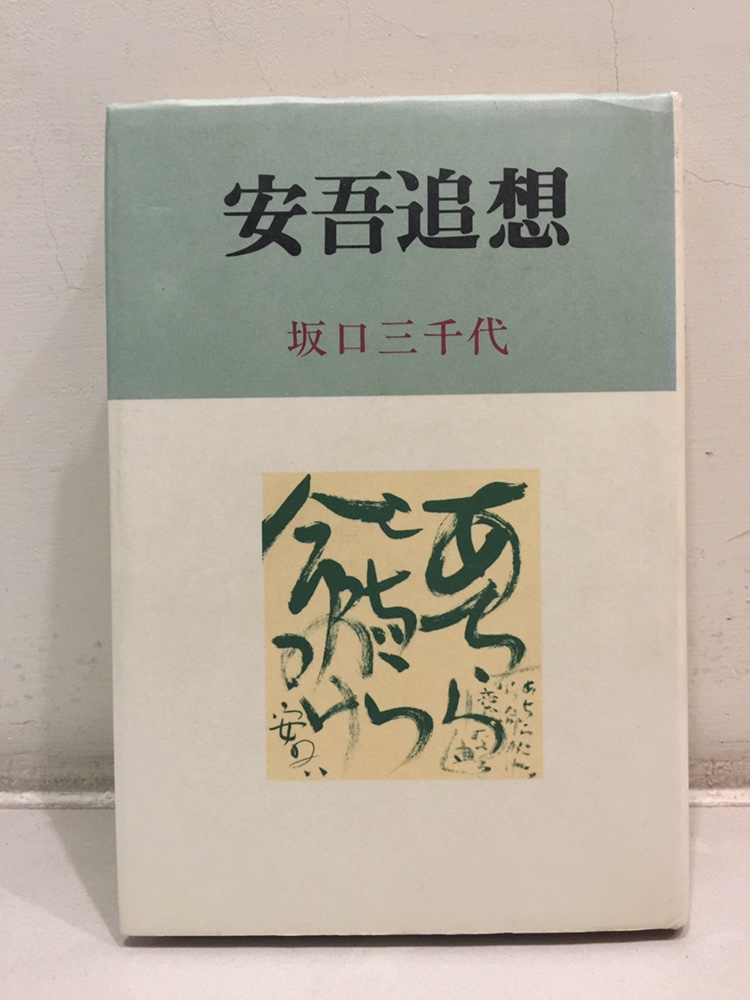
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