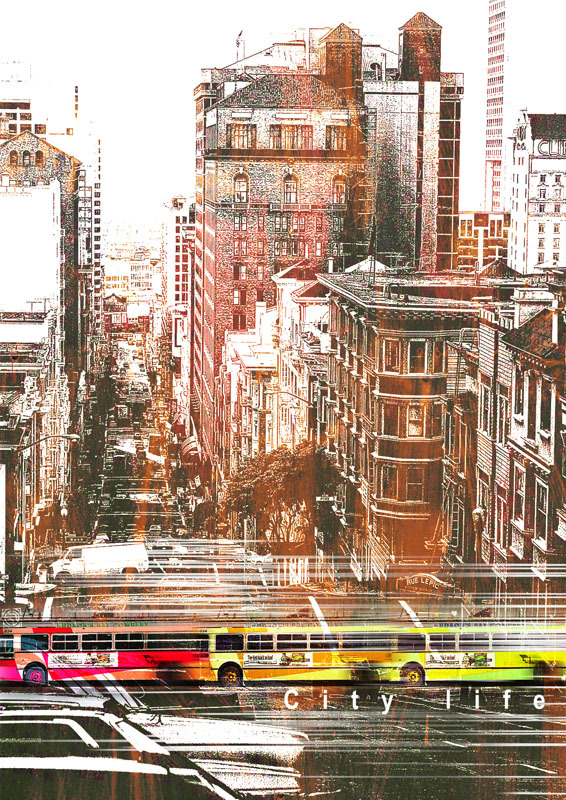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這是一棟屋齡超過30年的半舊公寓,電梯也老舊到總是雜音作響,還有閃爍不定的燈光與混濁的氣味,最近內門更出現無法閉合的問題。自從絕命終結站的系列電影問世、告訴你死神無所不在以後,神經質如我者,每次坐在這座電梯裡面,總是在想像著鋼索隨時斷裂、車廂應聲掉落一類的事情。
「才檢查過的,你看那邊還貼著驗證標章。」當我去一樓櫃台反映,大樓管理員這樣跟我說。
對於此我難免露出狐疑的表情,他看了後忍不住笑了:「我做這麼多年了,在不同的大樓,還沒聽說過有人因為電梯掉下來而摔死的。走在路上被車子撞死還比較容易。」
這樣的回應,不禁讓人有點惱怒,除了被輕率地敷衍了以外,同時,對於顯得怕死,也令我深感難為情。然而趕著出門的我終究沒有再說什麼,轉頭離開。
面對死亡,常人如我,總是缺乏了一點瀟灑,就像是對於並不起眼的人生,有太過自我感覺良好的貪戀,而這一點都稱不上好看。當然有時也會想像如太宰治一樣,慣常性帶著女孩子走到橋上,然後就一起縱身往下跳去。對我來說,這樣的場景,其實遠比他的小說更饒富感受。然而,每次走過河邊,這樣的念頭,卻也總只是一閃即逝,又或許那個時刻尚未抵達。
然而卻也因為人們對死亡的如此懼怕,所以塑造出了求死的重量。而不管是鴻毛或泰山,標定這個重量的,往往就是那些活著的人繼續要面對的事。就像是這個四月裡面所看到的許多事物一般。

整個四月,在我的臉書動態訊息上面,也充滿著死的論述。轉貼著鄭南榕自焚歷史的人,也通常轉載著西藏青年自焚的新聞,讓兩個敘事進行平行剪接,意象相互纏繞,就像是那把火燒了一個世紀那麼久。這是兩種求死的敘事,但訴求的是同一種的勇氣:因為生之可戀,所以死之昂貴。死成為一種交易神聖事物的貨幣。
而這樣的交易,是否總是合算?這成為一個令人不忍啟齒的提問。就像是另一段在這個四月裡面再度被提及的舊事:絕食的IRA政治犯,都死在牢裡了,而他們沒有因此推翻了囚禁他們的體制,也沒有獲得自由。當然,最後的最後,佘契爾終究也死了,在她死掉了以後,這些事情才被提起,成為訃聞中的一段註腳。
 我們不禁要探問:如果死亡未曾掀起實質的改變,只能像是叩著一座倒扣於地而未曾懸起的巨鐘,有一陣陣悶悶的微響,卻未能發出足以震動世界的聲音,這樣是否值得?或者,我們存活下來的人,又是否值得?也或許,因為生活本身就如此艱難,所以我們忘卻了死亡的重量,所以對那聲音充耳不聞?
我們不禁要探問:如果死亡未曾掀起實質的改變,只能像是叩著一座倒扣於地而未曾懸起的巨鐘,有一陣陣悶悶的微響,卻未能發出足以震動世界的聲音,這樣是否值得?或者,我們存活下來的人,又是否值得?也或許,因為生活本身就如此艱難,所以我們忘卻了死亡的重量,所以對那聲音充耳不聞?
各式各樣死亡的價值換算,卻未曾止息地盤桓於我們的週遭。
就在前幾天的晚上,在某個身份特殊的人,從這個監獄換到那個監獄的前夕,上吊求死而未成之際,這個國家也一口氣槍決了六個人,作為某種遮掩。又或是遮掩別的。死的交易遂又再次上演。
法務部說,因為那6個死囚,他們謀害了42條人命,所以這是一件值得的生意,雖然我們並沒有看到6場死刑換回了42個活人;而在那個特殊身份者上吊之後,獄政單位說,我已經給了你200坪的空間,可以了,但上吊者說,你給我一整個台中監獄也是不夠。這則是一場沒有結論的講價。
人是萬物的尺度,而死是人的尺度,為你我貼上各自的標價。
好在就像Block的推理小說講的一樣,只要這座城市有八百萬以上的居民,就總有八百萬種以上的死法。這整個世代、整個國家,就是在一座前途未卜的老舊電梯裡面。我們每天在此上上下下,去到我們的辦公室、俱樂部、理容院,或是百貨公司,卻無視於任何一種集體毀滅的危機。
就像那之前或是之後,有人在馬拉松比賽裡面被土製炸彈炸死,有人在地震襲來的夜晚裡面葬身危樓,死亡終究有太多的面貌,像是終於通貨膨脹的貨幣一樣,使得我們無暇顧及他人的死亡。即使,是在同一場電梯的墜落之中;即使,我們下的是同一個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