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被學術界認為是政治人物,被政治圈說是讀太多書頭殼壞去,想當作家但是藝文界覺得他沒有才華,因此只好繼續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流浪,並嘗試寫一些風花雪月文章來野人獻曝。
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aswing1978
上星期談到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比連續劇還曲折,有些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我所提到被扭轉為日本人認同的的「漢人認同」說,缺乏多元族群的概念。
但我卻認為,當時的人們不太可能具有當今看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多元族群」觀念,因此幾經考量,還是選用了「漢人」字眼。
我選用「漢人」的時候的確有經過一些考慮,我認為中國人、華人或者中華民族,當時都是相當模糊,而且正在建構的概念,1895年在馬關條約與日本簽和約的國家叫做「清國」,這說明了那時根本沒有「中國」這個國家,而「台灣人」同樣也是彼時萌芽中的概念。
我採用的漢人之說,雖然排除了原住民族,但以現在能夠取得的歷史資料,幾乎都是使用漢文的知識份子著作看來,漢人大概還算是勉強堪用的概念。
換句話說,當時的民族意識中,並沒有原住民的存在,原住民被納入台灣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想像,應該是更晚近的事情。
那麼,當時萌芽中的「台灣人」概念,究竟是什麼?
在1923年「治警事件」的法庭辯論中,蔣渭水在辯論庭上用了「中華民族」、「漢族」等字眼,認為日本既然是大和、哀奴、琉球等十三個民族(みんぞく, 較接近英文ethnics)組成的國家,就應該讓台灣人以中華民族或者漢族的身分,成為日本國民(こくみん, 接近英文的nation)的一員,因此所謂「中華民族」或者「漢族」,都不應該被視為「不穩文句」。

蔣渭水的說法到現在看起來都相當前衛,因為日本到現在都不認為自己是多民族國家,作家新井一二三還寫過一篇文章「何來單一民族國家」,舉了軟銀總裁孫正義和王貞治的例子,批判日本人在戰後突然出現對於純血統優越性的想像,並指出像孫正義這樣來自舊殖民地的韓裔日本人,是如何在這種環境中辛苦的奮鬥。
在將近一百年前,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對殖民者說出「以中華民族或者漢族作為日本國民」的主張,毋寧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在這場法庭辯論前後,另一位台灣民權運動者蔡培火也提出了「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的台灣」的主張,這是後來被簡化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主張的濫觴。
後世的研究者普遍認為,蔣渭水與蔡培火的說法,凸顯了正是日本人處處營造本島與內地差異,而讓台灣人感受到不平等,而後才有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
也就是說,台灣開始被認為是一個固定的疆域,並且有一群「台灣人」生活其間,是日本時代開始的事情,而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因為中央政府的存在,甚至在民主化後由外來政權演變為本土政權,更使得台灣作為一個民族(nation),成為一個既定事實。
無論這裡叫做殖民地台灣、中華民國或者台灣,總之台灣民族主義起源與附著在這個確定的疆域上,並且因應時勢而有所變化調整。
今天所謂「四大族群」之說,也是這種社會變遷下的產物,如果仔細檢驗,就會發現四大族群並不同時具有意義,只有在兩兩相對的時候,比如福佬與客家、外省與本省、原民與漢人,這樣的時候,才具有意義。
這幾年更發展出新移民與台灣人的新相對意義。甚且,這些分類本身,也都掩蓋了族群內部的差異性,同樣被歸類成新移民,比如來自越南的與來自印尼的,基本上語言並不通。
族群、民族與國家之間,確實有太多想像的空間。
大三時上民族主義的課程,老師問大家,請問先有民族還是先有國家?當時都讀過三民主義的學生便會想起課本上寫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既然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那自然力當然比武力先存在,不然跟人家叫什麼自然力?
不過當代許多研究都顯示,國家是武力造成的沒錯,不過民族也是武力造成的。
Charles Tilly在《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一書中,指出「暴力」是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徵。他認為在資本累積的過程裡,國家會會不斷地擴張他的統治領域。擴張的手段是戰爭,戰爭就必須要動員、動員必須要金錢、金錢就必須要靠稅收。國家在擴張的過程裡,開始有了比較強的統治能力。
在疆界確認的過程中,要先確認他者,他者就是非我族的人。非我族類對於我族邊界的侵佔,無疑是發動戰爭正當性的來源。
相對的,被納入疆界的人,也被歸類成為一個民族。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語言、文化,比如本來稱呼自己是諾曼底人、高盧人,但這樣的國家出現後,他們都共享「法國人」這個價值,學術上稱這樣成形的國家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重要的民族主義學者Ernest Gellner此現象有這樣的論述,他說:「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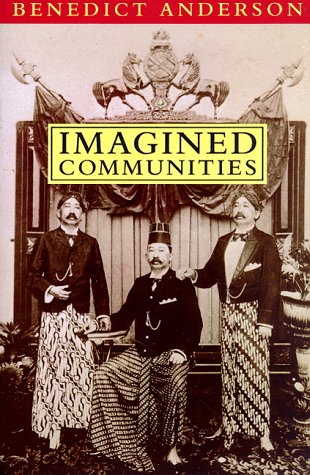
這樣看來,孫中山所謂「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說法,顯然不符合當代民族主義研究主流的後天建構說。
不過說起建構,民族主義研究者也不會認為這種建構是憑空而來,Benedict Anderson在經典作品《想像的共同體》中,就一針見血的批評Gellner:「太熱切的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偽裝在假面具之下,以致於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ging)與創造(creation)」。
依照Anderson的說法,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如何有共同體的概念,其實仍來自於一些共同的文化根源,像是語言、宗教、血緣等等,這樣的文化根源透過當代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刻意的放大,而有了「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概念,人們從而認識了同一疆界內的「我族」。
既然談到印刷資本主義,可見建構論的民族主義研究者,無論是談歐洲的民族主義或者解殖的民族主義,也多半同意現代性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中就可以推理出民族主義的出現,應該是相當晚近的現象。
既然民族主義是發明,那它的定義就有可能改變。而之所以改變,則可能是因為時勢的需要。就像孫中山在革命初期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後面卻要強調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也是因應時勢的需要所做的改變。
在台灣民族建立的過程裡,原住民被納入台灣多元族群的論述,是因為民主化與多元主義興起,再加上原住民運動所抗爭出來的結果。
而棒球場上那些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喊著台灣加油的球迷,則是經歷數十年記憶些什麼、遺忘些什麼的波折中,折衝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共識的一代。
從各種民調中表達自己是台灣人認同的人不斷攀高的趨勢看來,當代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已經接近成熟,只是他最後因為時空環境所折衝出的樣貌,和原初的民族主義者所想建構的,長的不一定一樣。
那麼,回到大三老師的問題。如果國家與民族都是武力造成的,那到底是先有民族才有國家,還是先有國家才有民族?
從歐洲各地的例子看來,應該都是先有國家,然後才有民族;但台灣的例子,卻是先有民族,然後才有國家,或者說,民族主義成熟了,但國家建構還沒有竟其全功。
但儘管如此,台灣民族主義終究是附著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而生的一種主張,儘管他還沒有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但他的疆域早就已經確定。這些經驗,和其他正爭取獨立中的民族主義並無二致。
台灣的例子讓我想起Gellner的一句話,他說:「有些民族擁有自己的肚臍,有些民族必須靠努力才有肚臍,至於其他民族的肚臍則是自己送上門來的。」
我想,台灣大概就是那個必須靠努力才有肚臍的民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