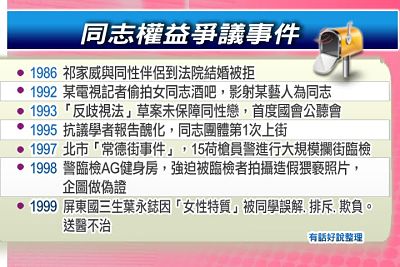薑餅人。曾經在溪州鄉公所服務,台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沒有畢業。志願是推廣台灣文學與文化。
本屆(第十一屆)同志大遊行的主題為:「看見同性戀2.0: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大標題沒有爭議,就是呼應第一屆大遊行「看見同性戀」的2.0升級版。但副標題「性難民」卻造成不小話題。
再加上10/13日主辦單位的座談「娛樂性用藥、BDSM(透過繩索綑綁來達到身體歡愉)及性工作者」(苦勞新聞報導〈追討情慾正義 性難民拒被看「賤」 〉),引發了同志之間的爭議,許多人認為同志大遊行的形象應該是健康的,將藥物成癮當成討論主題,會讓外界對同志大遊行的觀感變差,於是有許多人聲稱不再參加本次大遊行。但也有人提出這種言論是一種「內部歧視」,如同真愛聯盟排斥同志一樣。
的確,同志內部有許多反對聲音,社會輿論可能也會有所質疑,但「同志」本來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全體,有各種階級、族群和認同,能引發討論,其實是良性的循環,畢竟性/別運動本身就是不斷挑戰社會的刻板印象。所以筆者認為,主辦單位並不需要更換主題,只要能讓各種多元聲音都冒出來,讓旁觀者、參與者反省思考再出發,大遊行才能真正邁向「2.0」的升級版本。就算今年少了一些人氣(往年人氣很旺,但被批評為太像嘉年華),或是有不同意見的人另外舉辦其他活動,也並不是負面的現象。
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持續能對「污名」進行討論(參考文章〈給對遊行和用藥的討論,感到生氣的人們〉)。打開社會、同志群體內部對於性少數、邊緣的歧見,遊行的狀態如何反而是次要的事情。
回到主題,回應〈誰在歧視『性難民』?〉一文,其正文主旨是:「『難民』有其特殊定義,同志大遊行不可誤用、濫用『難民』一詞,否則將會削弱『難民』的政治強度。」但筆者認為,這篇文章並沒有著眼於台灣實際「性難民」的問題來對話,是有點失焦的。
張先生提到「同志堅持以一個『不嚴謹』的詞彙」,或許太過主觀。畢竟針對性難民這個詞彙,主辦單位也是經過不少討論過程才決定的,而性/別運動作為一種「被迫前衛」的象徵,每每有新的概念、口號,總是會被認為太過「基進」。比方1994年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也是引發莫大爭議。總之,對於提出「性難民」此一概念,張先生應先理解在工作人員及性別運動參與者之間,也是十分「艱難」的決定。
而我們可能反問:以張先生的定義,難民是否一定要「流亡」,或者實際遭受「暴力迫害」?台灣目前無法計數的同志、性少數、酷兒、愛滋病患者、性工作者在角落被歧視並且遭到社會排出,這是一個持續而且真實的現象,不是政治學的概念。也就是說,這種「你怎麼可以當難民,難民應該是怎樣的人blablabla」這種學理上的認定,只是國語辭典上的解釋而已,我們要看的,是真正對於「人本身」、邊緣本身、受難者本身的經驗,而不是由某某認證機關、某某學家提出來作為關懷準則。語意分析上的政治學,言說的並非語意本身,而是使用者的意識型態。張先生將「難民」作了很「精確」的定義,難道不也是一種政治上的佔據與消費嗎(依據張先生的邏輯而言)?
我們不妨把焦點,轉向伴侶法的修法、性工作除罪、通姦除罪化、愛滋病去污名等等實踐可能,是否更能貼近遊行的訴求及意義呢?
並且,實質上張先生並未說明清楚,「性難民」的使用,為何妨害到其他「難民」的權益?並不會因為邊緣同志認為自己是受迫害者,就使得其他受迫害者的力量萎縮吧?反過來看,不同群體之間出現了「受迫意識」,才是團結、培力的根源,如果有真正更不幸的難民,為什麼不一起站出來參加大遊行呢?我們更應該鼓勵相同經驗者站出來,講出自己的「受難經驗」,然後成為更大、更有影響力的受難者聯盟吧!
最後,身為一位鍵盤參與者,希望所有「sufferers」(受苦者)以及所有關心社會議題的公民們,一起出門為了抵抗歧視、抵抗主流霸權而走!(參考〈那就奪回自己的發言權吧!〉)
「看見同性戀2.0: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10月26日下午一點,我們市府廣場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