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讀台灣電影最早放映的五種說法
為何會有這麼多差異?這些差異或因當事人的記憶有誤,或因電影放映定義等
問題等所致。無論如何,這些第一次電影放映的討論,最終仍應參照當時最重要的《台灣日日新報》(底下簡稱台日)。值得一提的是,台北藝術大學李道明教授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的「台灣電影史研究史料研究庫」,將《台日》的電影相關新聞記事蒐集在資料庫中,這使得查閱工作變得迅速(前面第一次電影放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1990年代的先行研究者是在《台日》的紙堆中辛苦查找台灣電影發展的蛛絲馬跡)。
有了這樣一個資料庫,也便於我們追查相關的發展:
就第一種說法(市川彩)而言,市川彩的《亞細亞映畫之創造與建設》一書,是在推動大東亞共榮圈的脈絡下寫作,市川彩考察日本殖民地台灣、朝鮮到東南亞各國的電影環境,其所涉及的幅員極為遼闊,市川彩很難以一己之力完成研究,其間很可能是訪問對這些國家電影環境有所了解的電影人作為重要參考。
在〈台灣映畫發達史稿〉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如果高松豐次郎記憶沒有錯誤的話」,也就是市川彩在台灣電影部分訪問了高松豐次郎,他是對台灣早期電影有重要影響的人。問題是,高松豐次郎的記憶有沒有錯誤?對照《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上旬台灣日日新報社前並無放映紀錄,倒是10月2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西門外每晚六時起有《英杜戰爭》、《北清事變》等影片放映外加義太夫的表演等,這與高松豐次郎的記憶有一部分重合。
但即便是高松豐次郎提供與放映,這也不是台灣電影史上的第一次電影放映。簡言之,高松豐次郎很可能是以自己的記憶作為台灣的影史的第一次放映紀錄。
第二種說法(呂訴上),其實就是採取市川彩的說法。羅維明的〈「活動幻燈」與「台灣紹介寫真」:台灣電影史上第一次放映及拍片活動的再考察〉對此曾有一番考察,他發現1901年11月的《台日》未見呂訴上所說的電影放映記事,倒是有一則新竹竹陽軒電影放映的紀錄。這則新聞記事相當重要,最後筆者會加以討論。
第三種說法(李道明),則把台灣電影史上第一次電影放映把時間前移。李道明文中也提到,1900年6月16日淡水館便有放映活動,新聞記事也詳列放映片目,諸如曬布、軍隊出發、火車入站出站等,按李道明推論,這些片目與十字館相同。李道明之所以將放映日期較後的十字館放映是為台灣第一次電影正是放映,其理由應是正式兩字,淡水館是日本官方招待性質,十字館的放映如盧米埃兄弟針對大眾開放。
就第四種說法(葉龍彥)而言,約二十年前來台灣留學的日本學生三澤真美惠根據碩士論文改寫的《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2002,前衛出版社)對此提出合理質疑。葉龍彥的依據由兩部分組成,第一是《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日「興形物年代記」一文,這篇文章以年代記事的方式記述日本領台以來娛樂業的發展,其中,「明治29年8月覗き眼鏡(建昌街)後文武街及祖師廟前放映」。
然而,這段記事裡完全沒有提到放映電影片名,此外,覗き眼鏡的覗き是從小孔看的意思,未必是西洋鏡,也有可能是裝在箱子裡的紙芝居。
那麼,葉文當中提到的《大力士桑多》等片名從何而來?這些片名是根據李祐寧所寫的《電影的故事》一書當中,愛迪生系統在美國引起的熱潮以及放映的片名而來。簡言之,葉文是先把《台灣日日新報》當中所說的覗き眼鏡認定為Kinetoscope,再將愛迪生在美國放映的片名附上而成。這個台灣最早的電影放映紀錄確實如三澤真美惠所說,需要更強的證據才能存在。
第五種說法,是國家電影資料館為紀念電影一百年,以台灣電影發展相關的新聞記事記錄台灣電影百年發展的歷程。真宗少年教會的放映活動,刊登於1898年9月15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廣告欄上,上面記載「少年教育映畫會 本日午後八時放映 北門外本派本願寺出張所 真宗少年教會」。根據廣告,僅知是少年映畫,無法得知放映電影名稱。
換個角度思考「第一次」
台灣第一次電影放映到底何時開始?這個問題從市川彩開始,不斷有人在史料中爬梳,找出新的見解。台灣早期電影史並不算是個熱門的領域,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會是政治運動的研究,顯得十分寂寥,這些研究者的用心誠摯。
在筆者看來,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早期電影史。
從文章開頭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早期電影史的特性:就是高度不安定與跨界電影發展初期,還在攝影放映系統激烈競爭的狀態,但19世紀中期以來全球貿易網絡的浮現,也使得競爭隨著個網絡跨越國界。最早的電影幾乎都是寥寥數分鐘簡單再現真實的影片,專門放映電影的電影院還不那麼普遍也沒有那樣的需求,大多數的狀況下電影放映隨與各國的大眾文化相搭配,在西方是馬戲團,在日本是歌舞伎,在中國是茶館。

在這個階段中,電影雖然受到歡迎,但基本上是以奇觀之姿大獲人氣,此時,也開始有人或租或買器材與影片四處巡映尋找利基,在浩瀚的電影史裡,這些人的姓名可能都未留下紀錄。此外,電影問世之初,也是帝國主義高張的年代,關於戰爭的再現也是奇觀之一。這是電影發展初期的狀態,電影被視為藝術,大約還要二十年後美國導演葛里菲斯(D. W. Griffith)的《國家的誕生》開始。
在世界早期電影的特色下,《台日》的新聞記事裡有那些值得注意的「第一次」?
(1)最早的放映新聞記事是以漢文寫成,1897年5月14日,「近日有內地人來台,在於西門外張大布幔為影戲場。從玻璃鏡內看去,人物山川樓台亭閣以及花木禽鳥,無不設色明豔,彷彿如神仙世界也。每日觀者如堵,得貲當必不少也」(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新聞記事無法判別是否為電影放映,儘管紀錄者從放映機裡看到諸多新鮮景象,但未強調有動態,因此也可能是幻燈放映。事實上,1880年代日本的基礎教育就開始強調以幻燈強化學習效果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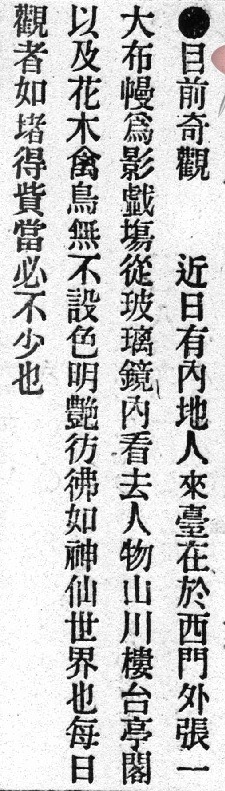
既然極可能不是電影,為何還要強調這段記事的重要性?文章開頭就提到,台灣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不僅是領土意義,也是台灣成為一個媒體已經相當發達的新興帝國的一部份。即使是幻燈,這段記事也意味著台灣進入「視覺現代性」的開始,此外,刊載這篇記事的媒介─《台日》,也是現代性的一部分。
(2)最早的愛迪生Vitascope系統放映。1899年9月8日,將於十字館以愛迪生放映系統放映《美西戰爭》等影片。隔日的報導,也確定了這場放映的舉行,還稱《美西戰爭》的影片如親臨實境。
(3)最早的盧米埃系統放映。1900年6月16日 淡水館盧米埃兄弟電影的放映,1900年6月19日與21日,分別以新聞介紹與廣告方式刊登佛國自動幻畫協會代表大島豬一將於淡水館與台北座進行電影放映的消息。
台灣人的電影震驚記事
前面所列舉的第一,大體能夠彰顯早期電影發展的軌跡以及台灣視覺現代性的形成。
此外,還有一則《台日》成立以來最詳盡的一篇觀影新聞記事,前面考究台灣最早電影放映紀錄的研究者當中,李道明與羅維明的文章也都談到1901年11月21日的新聞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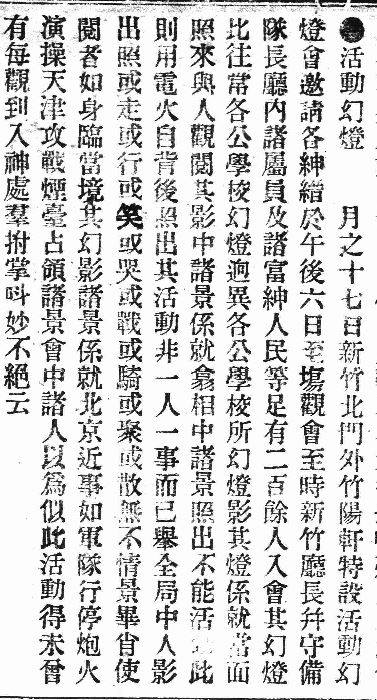
「月之十七日,新竹北門外竹陽軒特設電影幻燈會,邀請各紳縉於午後六日(筆者注,原文有誤,應為時)至場觀會,至時新竹廳長並守備隊長廳內諸屬員及諸富紳人民等足有二百餘人入會。其幻燈比往常各公學校幻燈迥異,各公學校所幻燈影,其燈係就當面照來,與人觀閱其影中,諸景係就翕相中諸景照出不能活動。此則用電火自後照出,其活動非一人一事而已。舉全局中人影出照,或走或行、或笑或哭、或戰或騎、或聚或散,無不情景畢肖,使閱者如身臨其境。其幻影諸景,係就北京近事如軍隊行停砲火演操,天津攻佔、煙台占領諸景。會中諸人以為似此活動得未曾有,每觀到入神處,羣拊掌口斗妙不絕云」(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這則新聞記事的特別之處在於,這是《台日》以來最詳盡的一則電影放映報導,不僅時間地點都有記載,電影內容也有相當的描述(應是八國聯軍相關影片),此外,更重要的是新聞記事較少描述的觀眾反應也在其中。在此前的研究中,多把這則記事解讀為日本官方所舉辦的電影放映會,其目的在於洗腦。
事實上,這樣的解讀可能忽略了新聞記事裡的關鍵詞——竹陽軒。竹陽軒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2018年《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當中,李維修的〈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家〉一文,介紹了竹陽軒與塚迺家兩家新竹旅館的興衰,作者文中的討論,揭開了竹陽軒的神秘面紗。
按照文章所述,北郭園為開台進士鄭用錫所建,1851年落成後號稱北台名園。日本治台之初,北郭園曾暫充官吏宿舍。1897年擔任新竹縣知事的櫻井勉善與仕紳交遊,不但重開1886年竹塹詩人的竹梅吟社,也引鄭家家主鄭如蘭加入統治協贊之列。此外,更是安排總督乃木希典下榻北郭園,增添北郭園的重要性。日本人片岡光楚見到商機,於是承租北郭園的一部分經營竹陽軒旅館。
1998年到1900年之間,可以在《台日》看到多筆日本殖民政府要員因地方巡視之需入住竹陽軒的記事。竹陽軒除了旅館經營之外,依據1901年11月14日《台日》的報導,竹揚軒成立竹塹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會員每月繳會費二圓,可使用俱樂部內的圍棋、弓箭等遊藝設備,報導也特別強調「入會人員接一時名流」。竹塹俱樂部成立後三天,就舉辦了電影放映會。
隨著新的歷史研究的出現,可以看到對這則記事的解讀也可以改寫,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日本領台初期,來台日人如何與台灣本地資本合作並透過日本官方的關係與象徵日本國家力量的電影強化自己的地位。
此外,更重要的是,德國文化評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經典作品《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當中,提到對觀眾來說,電影因為不斷變化的影像帶來震驚的效果,在這則記事裡,我們在「或走或行、或笑或哭、或戰或騎、或聚或散」的影像變動裡,看到觀眾「每觀到入神處,羣拊掌口斗妙不絕云」的反應。
這是台灣視覺現代性的反應與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