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有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什麼時代,作家都是眾所羨慕的行業,欽羡者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當,享受社會大眾的尊重,若加上媒體持續的傳播,很快就能名利雙收,走向恩寵的讚美聲中。這些世俗社會的期盼和想像,如今都已獲得歷史性的證明,所以它們才成為難以撼動的他者形象。然而,這裡存在必要的質疑:果真,所有的作家走入墳墓之前,都能享有這般輝煌嗎?
有的作家為了寫出好文章,真所謂嘔心瀝血地把自己的身體折騰得破敗不堪。夏目漱石是一位稱職的專業作家,終日伏案寫作苦思題材,面臨家庭財務危機之外,還得抵抗胃疾的惡意折磨。太宰治和坂口安吾等神經敏感的作家亦然。他們在成名之前,生活的風浪翻騰不止,寫作總會遇到瓶頸,謬思女神卻遲未現身,只好依靠安非他命來拯救受困的靈感(靈魂)。當然,有的作家揚名之後,便舒心快意躺進安樂椅裡,或者沉迷於虛華的人工神壇中,日子一久,最終被清醒的讀者和時間所遺忘。就此意義而言,我們與其討論機遇對於作家的重要性,毋寧是聚焦於大作家煉成的過程及其義無反顧的意志,似乎來得有說服力。這就是說,作家一旦失去這些感人的行動力,自然就沒有後來的故事,更無法激發我們談論的興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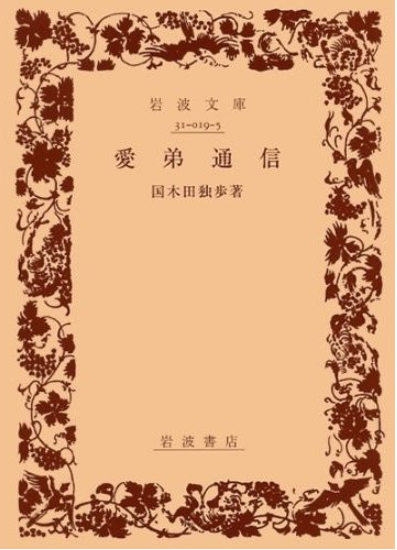
出版狂想與文字生涯
眾所周知,國木田獨步(1871-1908)寫過諸多名篇佳作,《武藏野》(明治34年出版)即其代表作之一。這部抒情性的小說出版後,獲得文壇極高的評價,被譽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傑作。依照這部小說給人的印象,國木田獨步可能是個隱居世外的高人,否則怎能寫出那麼絕美的作品呢?但實際的情況是,他是個極富行動力的人。當年,他就讀東京專門學校(現今早稻田大學)期間,就在雜誌社擔任編輯,20歲那年,一度返回故鄉千葉縣銚子經營私塾。不過,他翌年就回到東京了。畢竟,明治時期的東京是人文薈萃之地,他經常出入由德富蘇峰主持的「民友社」,增長了不少見聞。
在那以後,他又參與文藝雜誌《青年文學》的撰稿和編輯工作。明治26年,他發表文章明示「立志於文學事業」的決心,展現具體的行動。這時,好運道立刻向他投以微笑。同年9月,經由文藝評論家德富蘇峰的介紹,政界領袖矢野龍溪(注:《經國美談》一書作者,擔任過中國公使)的推薦,進入大分縣鶴谷學堂擔任訓導主任,在職期間,他利用時間博覽群書,鍾情於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作品,並計畫將來開辦出版社。一年後,他辭去了教職,進入《國民新聞社》當了一名記者,隨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以隨軍記者的身份,登上千代田號防護巡洋艦,見識日本聯合艦隊與清朝北洋艦隊開戰的經緯。他用給弟弟寫信的形式,以題為《愛弟通信》發送報導,表達個人觀察和省思,獲得讀者大眾的好評。

隔年,他與基督教徒佐佐城信子自由戀愛,不顧周圍朋友的反對強行結婚。他們一度考慮到北海道空知川沿岸開拓新天地,最後卻因各種因素未能成行,遷居至神奈川縣的逗子開始新生活。不料,他們的婚姻生活極為短暫,時隔一年,信子背離不告而別,最後以離婚收場。他為了排遣心靈創傷,同年,尋求內村鑑三(以無教會主義聞名的思想家)的幫忙,試圖前往美國開創新局,結果仍然失敗了。經由一連串的挫折,他終於沉潛下來,回到寫作的場域。正如前述,他26歲時,發表處女作〈源老爹〉,其後又在《國民之友》雜誌上,發表〈現今的武藏野〉,亦即後來改題的名作《武藏野》。

大展身手的重要性
明治32年,國木田獨步經由矢野龍溪的介紹,進入《報知新聞社》擔任政治記者,在政治外交方面表現活躍。這時期,他與自由黨的眾議員星享意氣相投,翌年便辭掉工作,進入了星享主持的《民聲新聞社》,並擔任民聲新報的總編輯。兩年後,他獲得星享的支持,一度想出馬角逐故鄉千葉縣銚子地方議員選舉,然而,對藩閥政治批判猛烈的星享,卻遭到伊庭想太郎(池波正太郎《幕末遊擊隊》、司馬遼太郎《坂上之雲》、山田風太郎《明治暗黑星》、柴田鍊三郎《心形刀》等時代小說,對伊庭想太郎多有描述)的謀殺。伊庭想太郎是幕末明治初期的教育者,擔任過私塾文友館館長,他在公眾面前刺殺了時任遞信大臣的星享。對國木田獨步而言,政治後盾駭然驟逝使他打消從政的念頭。同年歲末,他將妻子托付給老家照料,自己則寄居在時任立憲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的邸第。儘管如此,他出版文藝作品的夢想尚未死滅。進入明治36年,他的經濟狀況更為惡化了,他依舊執意創辦《東洋畫報》雜誌,爾後改名《近事畫報》。翌年,隨著日俄戰爭爆發,其雜誌再次改名《戰時畫報》,印量和銷售略有上揚,他繼而創辦《新古林》、《婦人畫報》等雜誌。
投以同情視角的理解
看得出來,國木田獨步非常熱衷於編輯和出版,有些時候,卻又想躋身政治界,做出一番作為。對他而言,這是一種嚴重的困惑,難怪其後輩作家芥川龍之介不無感喟地說:「他(國木田獨步)有敏銳的頭腦,同時又有溫柔的心靈。然而不幸的是,它們在他的身上失去了調和;因而他是悲劇性的人物。(出自〈文藝性的或太文藝性的〉)這就是說,國木田獨步的獨特性是源於其誠實地凝視這種矛盾,並奮力與之搏鬥,雖然最終如唐吉訶德式的挫敗,但也因為這樣,體現其鮮明的作家性格。
日本近現代文學史家中村光夫對於國木田獨步研究甚深,他在其《日本近代小說》一書中,就這樣提及:「不可否認的是,國木田獨步的性格中,也有一種俗氣或者投機心理。我們可以體諒他著手『賺錢』卻失敗告終的困境,那是時代的風潮所迫。從甲午戰爭至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它在新時代的青年之間,可謂最無從扺抗的追求成功發跡的時期,與此同時,這也是個人的野心與理想主義並行不悖的時代,它們之間並無矛盾而且可以共存。在這方面,獨步是這個時代的竉兒,自然極力追求事業的成功,並不斷維持著強力的熱情。另一方面,他甚至將『我極有信心為理想而存在,並把『批評人生』視為自己的天職。這個內在的矛盾或者悲劇,已經磨損他整個心身,奪去了他不足四十歲的生命。相反的,由於他生活在那樣的時代裡,因為更加意識到生活的徒勞與空虛的特異位置上。就此意義而言,他是一個敢於直面生活的殘酷,以小說形式將明治社會內部的空虛感表達出來的詩人。
國木田獨步創辦「近事畫報社」期間,平日忙於編輯和開發新題目,創作之筆仍未停歇下來。明治38年8月,他由該社出版第一部作品《獨步集》,該文集中收錄〈富岡老師〉、〈牛肉與馬鈴薯〉、〈女禍〉、〈老實人〉等作品,可惜沒能引起矚目,初版僅印五百部。他歸結其中原因,當時日本社會大眾尚不知自然主義文學為何物,更別說對這種文藝思潮的理解了。然而,他並不因此悲觀,只是出版第二本詩集《獨步集》時,其營收每下愈況,他在序中這樣寫道:「雖然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當今的讀書界大受歡迎。但非常不幸啊,迄今為止,我的作品乏人問津,與現今的當紅作家相比,在文壇上,我僅只是一個徒具虛名的作家罷了。」
翌年3月,為了挽救頹勢,他堅持出版第二部作品《命運》(佐久良書房),這部作品出版後,他總算擺脫了心理陰霾。當時,文壇一致認為,這是新文學的名著之一,他的聲名也跟著水漲船高。另外,在同時期,島崎藤村出版長篇小說《破戒》獲致極大的好評,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這才得以抬頭挺胸正式走入公眾的視野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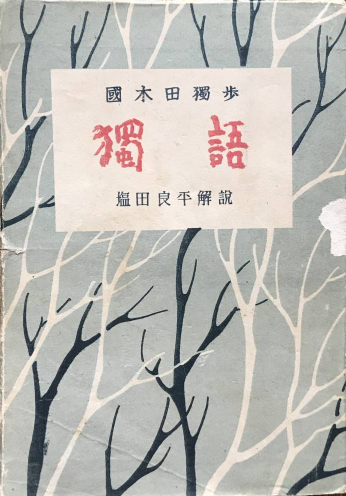
孤高與獨步的位置
在那以後,國木田獨步躍身為著名作家,各種商業文藝雜誌相繼約稿,但實際上,同年6月和10月,他只在《中央公論》發表了兩篇作品:〈岡本手記〉和〈入鄉記〉,還沒有正式成為收入穩定的專業作家。不過,他在〈岡本手記〉中,依然透露內在心聲:「我迫切的願望是從沉睡中覺醒,是擺脫夢境,是正視這不可思議的、無窮無盡的宇宙和這個宇宙中的人生,是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宇宙中的赤裸裸的我。我並非要了解不可思議,而是要驚訝於死亡的事實。我不是要得到信仰,而是如果沒有信仰片刻也不能安寧,是痛感這個宇宙中毫無掩飾的可怕的事實。」
更具體而言,在之後相對安定的生活裡,他仍然掛念出版社的經營。當年,歌人窪田空穗正是獨步社的員工,他對於國木田獨步力圖挽救出版社的精神姿態有詳細的記載:「毫無疑問,國木田獨步不諳生財之道。如果說,那時有誰最為依靠,那就是《愛弟通信》裡的主角收二了。彼時,其胞弟收二擔任神戶《又新日報》主筆或總編輯,儘管是新聞從業人員,他能給予兄長的援助有限。順便一提,在獨步的讀者中,不乏經濟優渥的人,不過,他們僅止於欣賞獨步的文才,對於深陷出版業之苦的獨步則興趣索然,不提供任何資助。我得知這種事情心裡非常悲痛……」
明治40年4月,獨步社終於宣告破產了。國木田獨步的妻子治子,深受丈夫的影響,平時就筆耕不輟,後來治子將這段經歷寫成題名〈破產〉的小說,可謂真正體現著夫妻同命的信念。
或許是上天的安排,倒閉破產之後,國木田獨步結束出版社的事業,舉家搬到東京郊外西大久保,過著閉門寫作和偶有稿約的生活。然而,在精神壓力和窮困的交迫下,進而導致他的肺結核病更加惡化。這時候,發生了一件賖賬糾紛。某日,國木田獨步到米店取米,突然看見米店門口貼了一張告示:「國木田獨步購米賖賬未還」。意思是說,如果前賬未還,店家就不再予賖米。為此,他找上米店的年輕員工理論,劈頭就是一陣訓斥:「你們不只這家米店,應該還有好多家吧!就算我的欠款尚有遲延,你們根本不必擔心這米店會倒閉。而且,我不去其他店家購米,只到這家米店賖賬。如今在緊要關頭,這米店若不特別通融,我們家人可能就會餓死!」他進而詰問道:「……其中利弊得失,你年輕伙計不懂,你們老闆可明白得很,你回去就把我這話帶上。」結果,那名員工對於國木田獨步的駁斥無法招架,只好讓獨步繼續賖賬取走白米。關於這段軼事,在《日本文壇史》中有所援引,證明作家在抵抗窮困的同時,並不因此放棄人性的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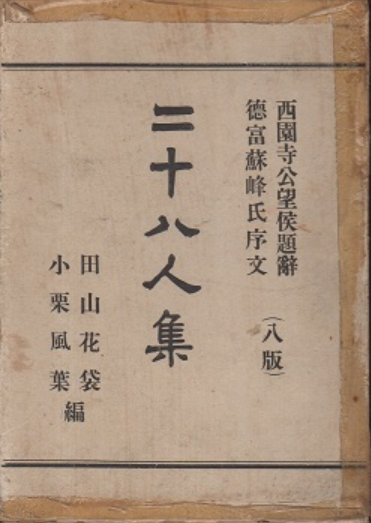
然而,翌年2月,國木田獨步的病情惡化,緊急送往神奈川縣茅崎的南湖院(肺結核療養所)住院。這是他出版《命運》揚名文壇,還不到兩年。與國木田獨步的同時代作家,對於獨步的苦難遭遇深表同情,田山花袋、島崎藤村和德田秋聲等作家,合寫《二十八人集》(新潮社)送至病榻前為他打氣。小說家真山青果與獨步相交甚深,此時他持續撰文〈獨步先生近況〉,於《讀賣新聞》上連載,直到獨步辭世為止。不過,同年6月23日,國木田獨步不敵病魔,因肺結核病去世,享年37歲。以作家的際遇而言,國木田獨步的確生不逢時,生命中充滿困頓與周折,但這並不影響他對於文學創作的追求,以及對於編輯與出版的熱愛,一種對於文字的敬重與使命感。
令人感動的是,同輩作家們適時為他送來了溫暖,他們合寫《二十八人集》,並將文集版稅所得,贈予國木田獨步的遺孀,堪稱是日本文壇史上的美談。如果說,國木田獨步孜孜不倦的寫作精神,令人想起相似的歷史場景,那就是罹患肺炎仍然埋頭寫作的臺灣作家鍾理和了。他在修改中篇小說《雨》時,突然咳血不止,鮮血濺灑在書稿上,這情景正體現著「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陳火泉語)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