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如果我們以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普魯東(1809-1865),在1843年出版《秩序在人類中的創建》這本近六百頁的大書與之譬喻的話,那麼其進行社會改革和打破舊有秩序的思想,似乎可運用於使日本畫起死回生的三大師:恩內斯特.費諾羅薩、狩野芳崖和岡倉天心身上。尤其是,岡倉天心這位時代的巨人,值得一書。因為他在藝術領域卓然有成,充分體現折衷主義的智慧,進而奠定了日本近代美術發展的重要基礎。而要呈現這段歷史過程,我們似乎有必要從幕府晚期的政治社會體制出發,考察新舊時代(德川幕府——明治維新)接替的變遷,以此作為起點,將有助於我們重新描述日本畫的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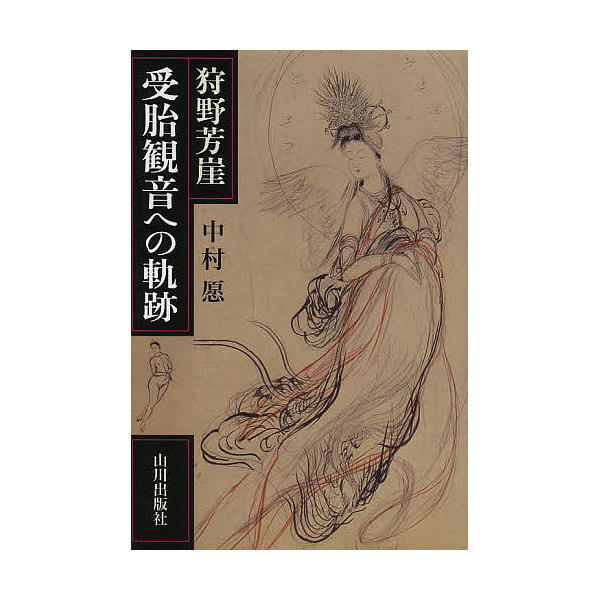
諸如許多日本美術史專著指出的那樣,德川家康在江戶取得政權後,極力要鞏固社會思想和民眾行為秩序,以維持政權的穩定。因此,按照岡倉天心的說法,在德川統治初期,整個社會猶如被鑄進了同一個模式,藝術領袖方面的表現,同樣受限於這個規範。

以狩野畫派為例,他們將近二十名畫家,都在德川政權的保護下,進行符合官方審美意趣的繪畫,而正規的封建宗藩關係,正是由這種絕對性的依附和生產關係構成的。簡言之,每個繪畫門派都有世襲的主君,他們恪守本業。只不過,這裡存在一個矛盾。無論主君是否為有品味的藝術家,全國各地的繪畫門生都會擠在他的門下,這些弟子必須在江戶學成畢業,才能返回家鄉,成為各藩主的官畫師。但問題是,他並非藩主的藩臣,而是狩野畫派主君的藩臣。另外,還有一個事實,每個畫師並不能擅自作畫,他們都有特定的題材布局和固定著色程序。不遵守這些規範,他們就會受到集體排擠,落入孤立無援的狀態中。當然,除了狩野畫派之外,土佐氏及其幼支住吉派,都在德川統治初期重振了家聲。
進入幕府中期以後,日本水墨畫(南畫、人文畫)仍然蔚為流行,其原因在於,歷史的連續性和承襲天保年間的畫風,再者即當時文人多半有漢學素養,他們將時代精神傾注在文人畫裡,並以這種方法呈現自身的文人氣節,其畫風同樣影響著同時代人。然而,主流傳統的體制再怎麼固若金湯,就有新興的思潮向其挑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突顯兩個世界觀——開放與固步自封的對峙。舉例而言,隨著蘭學(洋學)的輸入日本,日本近代美術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意識,開始衝撞著德川封建制度的束縛,借鏡自然科學的和實證主義的精神,為藝術的創造性預做準備。在此,有明顯的實例可供佐證。
1720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做出重大政策改變,放寬了對於禁書的輸入。換言之,他允許開港都市長崎港輸入(藉由荷蘭)西洋先進的思想,除了宗教書籍以外,有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測量學、植物學、醫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等書籍,包括來自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漢譯書籍。當然,「蘭學」得以興盛有其成因背景,更準確地說,隨著日本國內貨幣經濟的發展,城市中的町人(商工)階級意識逐漸高揚起來,初期資本主義的擡頭,德川的封建體制被迫做出改變,回應這股要求變革的聲音。
在這勢所難擋的時代裡,日本國內各產業所湧現的自然科學(格物致知、實學)的精神,使得「蘭學」這種嶄新的學問更為穩固下來。面對這種新思潮,難怪當時像司馬江漢、平賀源內、渡邊華山等著名畫家,看到蘭學書籍中的插畫,明暗有別的寫實主義技法,象徵歐洲文藝復興成就的在繪畫領域所展現的透視畫法,都讓他們嘆服不已。為此,司馬江漢在《西洋畫談》(寬政元年)一書中,用「此技法之精妙,甚為逼真也。」來形容蘭學書籍裡的插畫。而這個向西方學習的藝術潮流,還可推至日本畫家圓山應舉(1733-1795)奠定的荷蘭學派。他以隨著進入日本的蘭學(文化和醫學相關)書籍中的荷蘭繪畫,作為參考和借鏡。進言之,就整個幕府晚期的藝術表現來看,在京都的四條畫派,亦即以松村景文為代表的繪畫大師,多少展現著藝術氣息,江戶的浮世繪以及南宗畫派,或多或少都未能擺脫狩野土佐畫派的窠臼。
然而,正如新時代的崛起必然會出現徵兆一樣,而舊時代也在這樣潮流中,做出最後的努力。慶應2(1867)年,巴黎舉行萬國博覽會,日本積極參與了這個盛會,向世界展示浮世繪版畫日本紙和美術工藝品的實力。出訪成員皆為當時的俊秀之士:由德川昭武將軍帶領,法學者箕作麟祥、外交官田邊蓮舟、著名漢詩詩人向山黃村、名村泰藏等人隨行。在萬國博覽會「日本展示室」所展示的浮世繪版畫,可謂相當成功,給予來訪美術愛好者極大的感動。也許,我們可以形容這是德川幕府垮台前投下的最後一抹歷史餘暉,但它同樣慷慨映照在明治維新政府的勝利上。
而援引正面歷史記述可以得知,明治政府推動維新政策,以西方近代化為師,打破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體制,而走上了國富民強的道路。毋庸置疑,這種迎新棄舊的潮流迅速湧向了美術領域,傳統畫作的收藏者和審美觀點,出現極大的變動。因此,許多傳統派畫家的作品乏人問津,生活頓時陷入困難,不得不兼作其他差事,才能勉強養家糊口。簡單講,在此局面下,西洋畫派風光勝出,文人畫派走下坡。不過,在高揚西方為師的明治維新時期,佛教寺院和建築遭到的浩劫,僧徒被迫改信神道教、否則立刻面臨生命危險等恐怖威脅,絕對遠比傳統派畫家的失意落寞來得慘烈。在維新政府看來,新的時代已經來臨,自然導致神道教的復興,而這意味著愛國主義的恢復,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止要全面貫徹,更要把這種意識滲透到任何的領域上。從其本質上而言,推動文明開化即擺脫野蠻狀態。彼時,假名垣魯文《安愚樂鍋:牛肉店雜談》和式亭三馬《酩酊氣質》這兩諷刺性的作品,似乎最能突顯明治初期以文明開化為先的社會怪狀。
換言之,在那時期流行的個體自由觀念,的確讓多數的民眾趨之若鶩,對狂熱追捧西方文化的光彩,卻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盲目追奇獵新,缺乏批判性的自省。對於這種怪誕的現象,作家夏目漱石多年(1914)以後,在學習院輔仁會以〈我的個人主義〉為題發表演講,道出了他的切身觀察。在夏目漱石尚未成為專業作家之前,曾經公費留學英倫兩年,在那段期間,他努力學習英國文學,領略文學理論之奧妙,但卻遇過被人種歧視的苦澀經驗。所以就此來說,他比同時代的日本人更能體會何謂西洋語境中的「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他的個人主義,並非西方個人主義的翻版,毋寧說是道義上的個人主義,必須意識到他者的存在,公正處理自我和他人的關係,必須用人格、義務和責任等社會觀念來約束自己。他的個人主義建構在克己觀念的基礎上,而不是被金玉其表的西化風潮所淹沒的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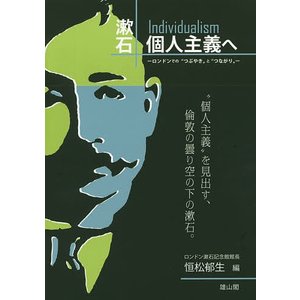
就年齡來看,本名岡倉覺三(明治29年改名天心)比夏目漱石年長五歲,他們有相同的學業背景,兩者出身於東京帝國大學,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名聲,都因他們的藝術成就得到更多理解。當然,在岡倉天心推動和闡述東方美術理想的修習過程中,美籍美術史專家恩斯特.費羅諾薩,發揮著提攜和啟蒙的重要作用。
明治11年,費羅諾薩受聘到東京帝大文學部教書,彼時岡倉覺三還是在校學生,在學期間,他和有賀長雄二人英文能力極佳,擔任費羅諾薩的翻譯和研究助理,曾經陪同費羅諾薩深入各地,調查日本古代美術寶物的情況。明治17年,岡倉覺三繼承費羅諾薩的美術事業,除了創立鑑畫會之外,更積極投入美術運動和振興傳統日本畫的地位。正如上述,是年他經常造訪京都和大阪地區考察日本古代美術。當他初次見到法隆寺裡觀音立像之時,大為佩服驚嘆,這可說是他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新發現,自己的美術視野因此開闊起來。

後來,岡倉天心在其《日本美術史》一書中,如此感性寫道:「余於明治十七年,與費羅諾薩及加納鐵哉,面見寺僧委其開扉。寺僧曰,此扉若開,必引來雷鳴。明治初年,神(道教)佛(教)之爭正熾,曾一度開啟,卻終日暗雲密布,雷鳴轟隆,眾人皆驚,半途作罷。因有前例,寺僧執意不開,余言吾等願受雷擊之過,堂扉竟微開,寺僧驚駭四逃。余打開堂扉,千年鬱沉之氣撲鼻而來,令人無法呼息。撣除蛛絲,凝目細看,前有東山時代之几案,移其几案,可觸及尊像。此佛像高七、八尺,以布片和經切等數層包覆。忽然堂內蛇鼠出現,眾人一時愕然。余近前揭下布片,發現一枚白紙,揭其後,方得見尊佛之莊嚴面像。此乃余一生最大快事也。」相信富有想像力的人,讀完他的記述,必然可以理解他在發現日本傳統佛像時所發出的讚嘆,這種對於自身民族文化底蘊的震撼,注定使他成為永恆藝術的探索者。
細緻探究的話,我們還可以推論這種思想根底的來源。也就是,岡倉天心重新發現日本美術之精髓,既有自覺性的美學思想,還含有當時民族主義的思想。相對於那時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統治,日本必須直面國內的政治問題,面臨採取歐化政策躋身列強之林的焦慮感。此外,明治新政府與列國簽署不平等條約,例如治外法權、關稅自主權、片面給予最優惠國家條款等問題,讓多數日本國民認為,其國家是否已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態?進言之,岡倉天心正是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時代下,挖掘出日本的美術傳統,發現精神與造型的原鄉,運用美術史的方法,給予組織和建構成帶有日本特色的美學體系。
明治19年,費羅諾薩和岡倉天心前往歐洲考察旅行,為將來設立教育美術機構預做準備。兩年後,他們在上野公園舊博物館的舊址,設立了日本近代第一所國立的美術學校。狩野畫派的代表人物狩野芳崖加入了教授群,但於明治21年匆然離世。初期在美術學校就讀的學生中,出了不少英才畫家,如橫山大觀、下村觀山和西鄉孤月等,而菱田春草是明治23年入學的學生。明治23年以後,岡倉天心由幹事升任校長,招聘狩野畫派的日本畫家橋本雅邦、狩野友信、結城正明;四條畫派的川端玉章、木雕刻家、高村光雲等擔任該校教授。依照費羅諾薩和岡倉天心的主張,那時該校沒有設立西洋畫和西式雕刻科。總結地說,岡倉天心致力推動傳統與現代的精神融合、理想類型的折衷主義,是由該美術畢業生為之完成。進入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時代,該校原本僅設日本畫科和木雕科,新設了西洋畫科和雕塑科,顯現出新時代的推移,明治26年歸國名聲響亮的黑田清輝,在其三年後擔任該校教授。耐人尋味的是,岡倉天心於明治31年期間,擔任博物館美術部長和美術學校校長之職,因遭到排擠而辭職。不過,與此同時,他亦帶走橫山大觀等日本畫家,與其同志另外設立日本美術院。同年10月,日本美術院舉辦第一屆美展,橫山大觀的《屈原》和菱田春草的《寒林》畫作,皆是參展中的名作。持平而論,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岡倉天心師徒聯手寫下了時代的見證,終究是一種千金難得的歷史際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