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旅日學者,研究興趣橫跨勞動法和國際政治,立志成為征服日本列島溫泉露天風呂的業餘專門家。作為偏好政治力學的「H型人間」,對包括從勞資關係到國際關係的「power balance」都很有興趣。
大島渚導演在1月15日逝世滿一周年了,當天日本電視台特別製作並播出了紀念專輯「大島渚:給電視的遺言」紀念這位日本戰後映畫界中最偉大的導演。

片中播放1963年大島渚導演拍攝的第一支紀錄片「忘れられた皇軍」(被遺忘的皇軍),描述一群曾經被日本政府送上戰場而負傷傷殘的在日朝鮮人老兵,四處向國家陳情請求給與補償、以及他們生日常的生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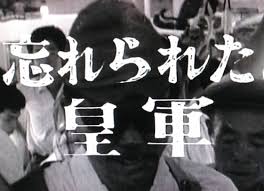
這是大島渚年輕時代的記錄片作品,在昭和年間的黑白鏡頭下、失去雙眼、肢體殘缺的在日韓國人老兵,步履蹣跚的往來街頭、國會、首相官邸、乃至皇居陳情,卻遭到日本政府以在日朝鮮人已不具有日本國籍為由,而拒絕給予因二戰成殘的老兵補償而淪落市井街頭。
紀錄片不斷交錯著苟延殘喘地存活在日本社會最底層的殘疾在日朝鮮人老兵的日常生活,時而聚在一起飲酒、豪邁悲壯地唱著出征時的日本軍歌。時而回想逝去的同袍與自身悲慘的人生而放聲大哭,時而激烈爭吵,因為對於對國家陳情抗議的路線、以及屢遭政府拒絕乃至日本社會歧視與嘲諷甚至仇恨的失意......
一名失去雙眼的老兵在述說著遭遇與回憶時,從凹陷的眼眶深處,泌出潺潺的淚水,這一幕「沒有眼睛的眼淚」的畫面,在電視在日本開播三年後,首次震撼了整個日本社會......

「我要讓我的畫面深刻的刺痛日本人的心胸」大島導演在成名後的訪問中如是說,正如同這部黑白記錄片片尾留下的激昂的旁白般,不斷地複數著那句話一般
「各位,這樣對了嗎,日本人阿,這樣對了嗎?」
伴隨著畫面中老兵沒有眼睛的眼淚,一句句地直接刺進、敲打觀眾的心靈深處,那是終戰後第十八年,一個日本甫告別戰爭重創而百業復興、經濟起飛的年代,也是一個國家與國民自我們都不斷地說服自己快快遺忘過去的年代......
大島渚導演崛起了,他透過鏡頭站在弱勢者的身邊,他親身參與學生運動、反安保鬥爭,頭帶鋼盔執攝影機,與手持汽油彈與竹竿學生與勞工們一同衝向鎮暴警察的人群中。
這位畢業於京都大學,成為日本映畫界極為知名導演的憤怒青年,以《青春殘酷物語》、《日本夜與霧》、《絞死刑》以及《感官世界》等數十部作品享譽世界影壇,在他的鏡頭下永遠充滿著對國家權力的憤怒與批判,卻永遠對受到國家權力殘害的弱小人民充滿的無限的溫柔。

這樣的意識形成,來自於大島渚導演少年時期親身的戰爭經歷。戰時還是中學生的大島渚,一生永遠無法忘懷在終戰前夕,學校師長不斷著教導孩子們「如果美軍登陸日本本島,你們就要集體切腹自殺」
孩子們甚至在學校被不斷地被教導與演練如何切腹自殺、以及如何幫助切腹的同伴解脫——那樣深刻的生命經歷,使大島導演成為一個國家的不信者、國家的批判者,並終其一生不曾改變......
大島導演在晚年時,目睹今日日本民族主義的再度崛起,特別是出生成長於富裕的八零年代,卻共同經歷日本的經濟與國力伴隨中國與韓國崛起而下降、更在非典型勞動的苦境裡充滿茫然的青年世代中日漸高張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他更憂心的是,整個國家的媒體與電影產業日漸單一的價值論述,日本人從電視與映畫中,不再看的到多元的視角,整個媒體圈好像再度成為國家的御用工具般,將這一代日本人型塑成價值單一的群體......
因此大島導演在過世前不斷的交代後輩的電視與映畫工作者,必須要用所有的力氣保存媒體的多元性,他說「哪怕八成的國民已經被國家塑造的價值所掌控,我們要用力用鏡頭保存剩下的兩成,永懷批判與自由的信念,作為改變這個國家的關鍵力量。」
這,就是一代導演大島渚留給電視的遺言。
古城京都歷經昨晚一夜大雪,伴隨晨曦中展開一片雪白世界,從京大圖書館的窗戶向外望去,西部講堂古老的黑色的屋瓦覆蓋了一片雪白,那是京大的學生社團中心、日本搖滾樂發源之地、也是青年導演大島渚的發跡之地,學生時代的大島渚與同窗們在此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飲酒、辯論、談笑,並拿著手搖攝影機開始拍攝學生電影......
而今日朝陽灑在覆雪的西部講堂屋瓦上潔白奪目而絢爛,我想,這幅珍貴的雪景正好最適合向心地永遠潔白善良、卻用一生拍攝那些炫目燦爛的作品憾動人心、用一生的鏡頭傳達反抗與溫柔的校友、大島渚導演致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