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往前閱讀:【日治時期電影史漫談】高松豐次郎的台灣時光:他為何離開?(上)
電影放映理念與機構的變化
正當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的事業走向谷底之際,日本的政治也發生了變化。明治維新以來快速的工業化,也產生了城鄉與階級的分化,勞工運動也隨之快速發展,1910年幾位社會主義者被指控有謀殺明治天皇的計畫,以此展開對社會主義者的大逮捕,共有二十四名人被逮捕,1911年包括幸德秋水在內共計十二人遭到處決,這個事件被稱為「大逆事件」。

按日本年長一輩電影史大家田中純一郎的《日本教育映畫發達史》(1979)的說法,大逆事件之後,日本政府為了強化天皇制與排除異己,1911年組成「通俗教育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兵分三路,一是針對出版物與展覽、二是幻燈映畫與活動寫真、三是講演會,三路並進,以通俗教育為手段穩定民心。1913年易名「通俗教育委員會」,其中也制定幻燈映畫與活動寫真的認定規章。事實上,電影問世之後,已有拍攝紀錄片,例如1901年中國的庚子事變甚至是1912年的南極實寫,1913年通俗教育納入教育映畫之後,各種題材的拍攝更形活絡。
大逆事件是長達四十五年的明治時代的最後尾聲。1912年日本進入大正時期, 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這件事對日本殖民來說心存警戒,擔心台灣受此激勵反抗殖民政府。隨著日本內地通俗教育委員會的成立,1913年台灣總督府也成立通俗教育部。1914年9月24日的《台日》便提及領台二十年來總督府各項建設都在積極進行當中,唯獨通俗教育的推行總有力有未逮之感,應以幻燈與活動寫真報作為教育之用。報導中也提及,總督府學務部已向東京訂購放映機器一部。
事實上,教育系統的刊物《台灣教育》在1913年3月當中,就可看到作者竹月生對台灣電影環境的憂慮。在竹月生的連載專文〈窗的落葉六〉(窓の落葉 六)裡,作者提到1912年12月25日到朝日座看年終的活動寫真,朝日座便是高松豐次郎經營的戲院,當日電影院裡有很多兒童前來觀賞。作者對高松豐次郎推動電影事業極感佩服,但是,卻在朝日座裡看到台灣電影環境的根本問題,一是辯士文化水準低落,雖然他的言說讓大家哈哈大笑,但卻沒什麼可取的內容。二是放映的電影本身,不要說跟日本內地的時間差,這些電影在台灣本身都是放映很多遍的老片子(作者看到的放映電影包括日俄戰爭,足見日俄戰爭在台灣是反覆放映多年的片子)。也因此,他呼籲為了兒童,教育機構對電影要加以監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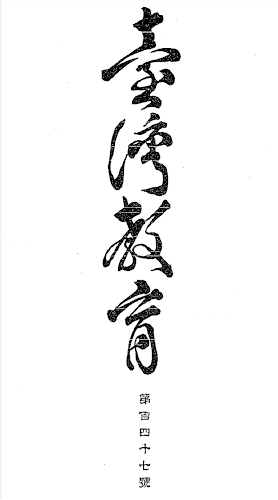
總督府設通俗教育部,就是要以幻燈與電影放映進行宣導,主要對則象是兒童與家長。竹月生的文章反映了教育系統的看法,以電影宣傳文化的高松豐次郎是有心人,但其他電影放映與解說者的水準卻讓人憂慮,成立通俗教育部有一個好處,就是由教育系統把關使電影放映與解說的水準一體化。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原來設有活動寫真部,這也是高松豐次郎來台之初的重要舞台,不過,也隨著高松豐次郎自行在台灣南北分別成立戲院之後,愛國婦人會的活動寫真部的重要性也慢慢降低,當通俗教育開始進行時,1916年愛國婦人會的活動寫真部也就畫下休止符,通俗教育部也就成為以電影面向大眾宣傳文明的最重要機關。
台灣教育會開始進行電影放映之初,影片來源有向日本購買的,也有以台灣為題材者。向日本訂購的部分,1916年3月的《台灣教育》當中的「會報」部分便提到台灣教育會通俗教育部向大阪梅田商店訂購了《文明的農業》、《學生花運動》、《汽車競賽》、《軍艦下水典禮》、《動物園》、《台文台與天文學》、《御大典大閱兵式》、《京都保津川順遊而下》。這些影片當中,有國家儀式,也有現代文明的知識。
離開台灣是必然
以台灣為主題的影片,就是高松豐次郎為1916年台灣始政式第一次舉行博覽會所拍的影片。該次的博覽會閑院宮殿下來台參觀博覽會,高松豐次郎的博覽會實況拍攝便以閑院宮殿下的參訪行程為主,依1916年6月《台灣教育》〈台北通信〉一文所述,高松豐次郎所拍影像包括:
「共進會第一、第二兩會場外觀內部及夜景。閑院宮兩殿下抵達台北車站、台灣神社參拜、蒞臨共進會開幕式、蒞臨紅十字會總會、巡視台中公園、巡視台南遺跡、巡視打狗港、蒞臨僑仔頭製糖株式會社、東門官邸接見番人之情景、樺山大將一行赴芝山巖祭祀場參拜之情景」。
1917年,高松豐次郎開始淡出台灣的舞台,回到日本發展。1916年台灣首次博覽會的拍攝,可以說是他在台灣最後與官方的合作。這時候的高松豐次郎,歷經戲院經營的失利、負債等挫折,或許是1907年《台灣實況紹介》的成功拍攝與宣傳,官方委以重任。帶著冒險性格逆風前行的高松豐次郎,會僅僅因為負債與經營失利退縮嗎? 1914年日本民權運動推動者板垣退助來台訪問,高松豐次郎也在歡迎之列並寫有〈台灣同化會總裁板桓伯爵閣下歡迎之詞〉的文章。這篇文章當中,高松豐次郎略顯激憤,其大意是不少人對演劇、活動寫真等存有偏見,認為這些仍是低級趣味,但在他看來,娛樂是手段,目的是向上奮發,文部省通俗教育委員會都已將演藝納入,如劇場、寄席之地就是佈教所,藝術家與演藝者就是教職員,其地位之重大自不待言。
為何說高松豐次郎略顯激憤?通俗文化的力量,日本已注意而且賦予活動寫真作為教育之用的功能,台灣也快速跟進,而且是以總督府之力更大更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高松豐次郎的悲憤或許是當年他接受挑戰來到台灣,這個角色正是他扮演的,然而,現今他卻失卻位置。
這是一種必然,治理台灣之初,急需敢於冒險願意擔當大任的人前來台灣發展,但是當後藤新平打下良好的基礎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整個治理組織的深化與運作。高松豐次郎屬於來台冒險開拓型的人物,慢慢地,他原本的角色與功能便移轉到通俗教育部,由較有組織化的官僚體系來執行。關於以電影放映作為教育之用的報導《台日》或《台灣教育》不少,但筆者所見最完整的卻是1915年中國學生來台參訪所寫下的心得,台灣省文獻會所出版的《台灣旅行記》(1965)收錄三名學生的心得,其中一位提到:
「晚膳後,台中廳派員來請余等至通俗教育會看電影,校長乃率余等往。至則觀者已滿,不下千人。彼員乃導余等由左門而入,至左廂觀,已先留有隙地足容余等;前列乃一隊之女學生。所演影片,皆與通俗教育有觀而裨益於社會者。每演一節畢,則風琴奏,有女小學生數十人唱歌而興;鶯喉細轉,音調甚高,聽之令人忘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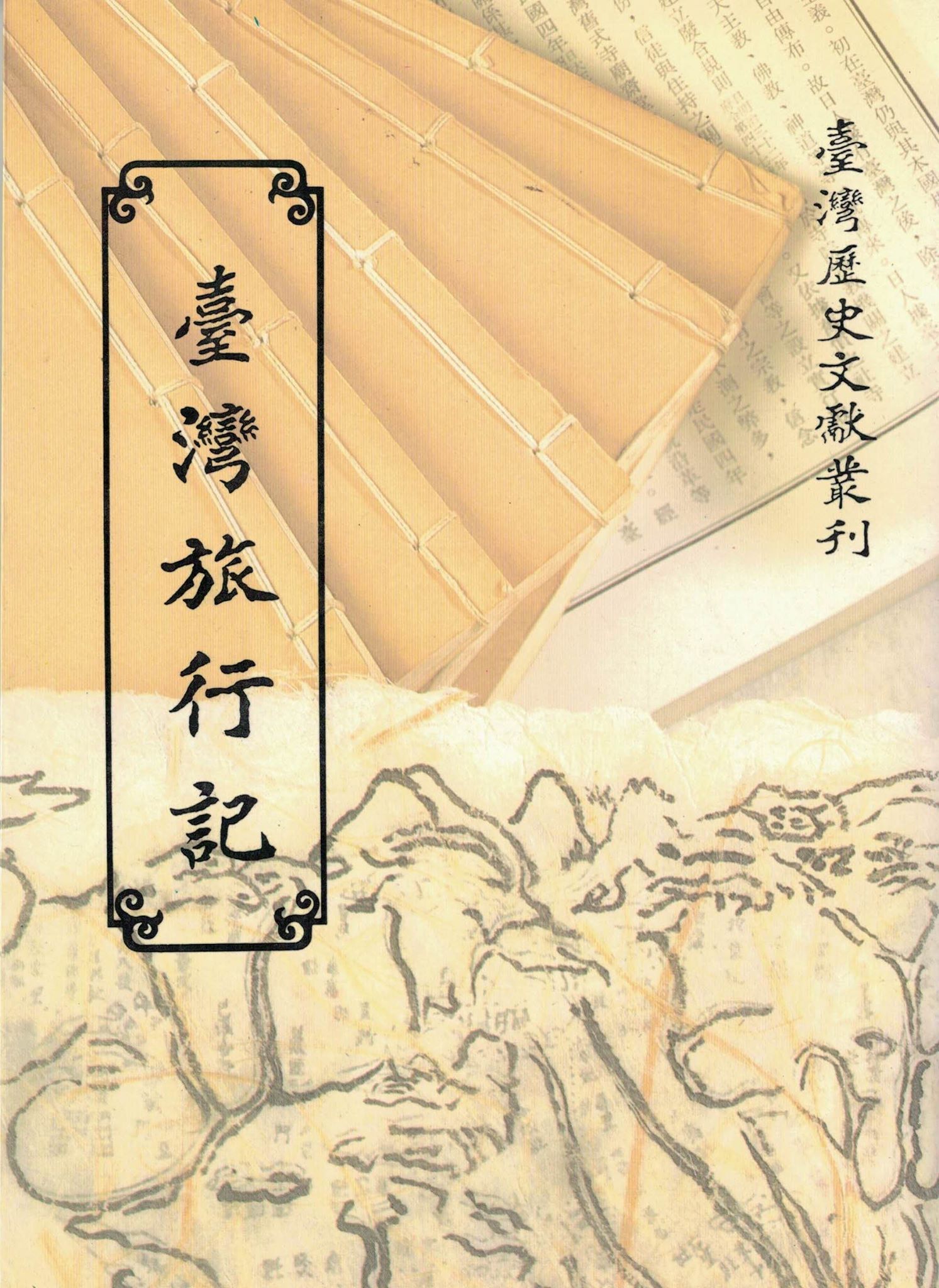
可以看到,通俗教育的動員,以眾多小學校、公學校為對象,這是教育體系的動員,已不是高松豐次郎個人之力所能及。高松豐次郎回到日本後也不寂寞,繼續在東京進行電影事業。有趣的是,後藤新平此時也結束滿鐵總裁的工作回到東京繼續擔當大任,後藤新平對高松豐次郎的電影事業時而給予支援,台灣早期的治理就是兩人的交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