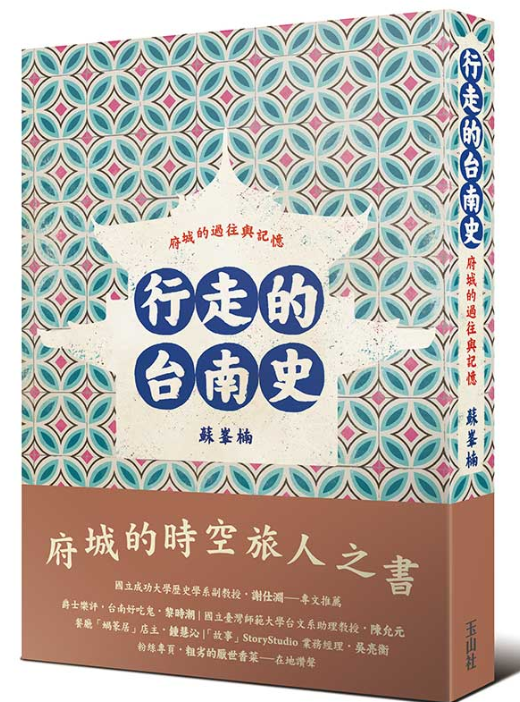漫步照相者,放空愛好家,博物館研究員,以及一個只要吃到正統府城碗粿(再配個魚羹),就能深刻感受到滿滿生存意志的台南人。
有些城市會挑選一種鳥類,作為自己的代表象徵。日本的東京,依據平安時期古典詩歌《伊勢物語》的描述,將百合鷗(紅嘴鷗)指定為都鳥。中國的北京,也選了長久棲息在北京城內的雨燕作為市鳥。這些鳥之所以被選定,往往因為牠們與當地歷史文化息息相關。
府城所在的舊台南市,在2005年也選定了市鳥,當時由「喜鵲」來擔任。
2010年縣市合併後,透過票選活動,重新選定了新台南市的市鳥,是以漫步於官田、下營菱角田中優雅身姿而廣為人知的水雉。喜鵲則就此退出市鳥的舞台。
不過,漫步在府城街區時,若留意腳下的路面,偶然還是會見到台南市污水下水道孔蓋上,鐫刻了鳳凰花、燕尾古厝屋頂,以及一隻獨立於枝頭的喜鵲圖案。
喜鵲曾被選為市鳥,說明牠們對府城的意義,不僅是一個孔蓋圖案而已。府城曾經到處都有喜鵲的蹤跡,牠們本來就是府城的住民。甚至,府城可能是喜鵲祖先們在台灣生活的起點。

城內喀喀叫聲
喜鵲是鴉科的鳥,身姿深黑、長尾,但肚子跟羽翼部分是白色,特別是翅膀上還有一抹靛藍,看似身著西服的優雅紳士。不過,牠的叫聲沒想像中婉轉優美,而是喀喀喀大聲作響,正如學名「Pica pica」一般。
喜鵲原本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但台灣原先似乎沒有。若是如此,台灣的喜鵲打哪來的?
1770年代初期,任職海防同知的湖南人朱景英,在他的文集《海東札記》裡,曾經提過這樣的故事:當時的道員蔣允焄,看到台灣沒有喜鵲,於是從中國內地帶了一些喜鵲到台灣來野放。
這批野放的喜鵲,一度都不見蹤影,人們懷疑他們是否皆未存活下來,也猜測是不是因為喜鵲越不過海。朱景英也在猜測喜鵲是否「土性不相習」,也就是水土不服。種種猜測,表面上在推敲喜鵲無法存活的原因;另一方面,其實也流露出當時來自中國的移民與官員,在水土不服的生活經驗中,對於台灣所抱持的異地想像。事實上,喜鵲非但沒有在台灣消失,反而大量繁衍,成為常見的鳥類,尤其是在府城。
19世紀初期的《續修台灣縣志》裡,就說到喜鵲「今孳育,郡城多見」,才不是當年《海東札記》所說的連一隻都沒有。之後也來到府城的英國人郇和,同樣在府城看到非常多的喜鵲,甚至在北台灣沿山地區也看得到一些。1863年,郇和將喜鵲編入他的「台灣鳥類學」名單裡,於英國皇家鳥類學會的期刊上發表。
照這樣來說,以前府城的市街,會有些什麼聲音呢?也許有人們的交談聲、店舖匠人的工具打造聲、市場的叫賣聲、牛車運貨的車輪滾動聲,以及迴盪在屋宇與城牆間,喜鵲喀喀喀的淸響叫聲。
移民社會的情緒
在歷史文獻裡,喜鵲在台灣的故事,大多從蔣允焄放養的事蹟開始講起──雖然後來一些文獻,常把「蔣允焄」誤記為「蔣元樞」,成為「蔣公子故事」的一部份。不管如何,牠們除了「喜鵲」(hí-chhiok)這個名字之外,也因為蔣公子故事, 一度被叫過「蔣鵲」(chiún-chhiok)。
此外,老一輩的台語,還有把喜鵲叫做「客鳥」(kheh-chiáu)的。也許人們一直很淸楚,牠們是從海外來的,不是台灣本地的鳥兒。只是,讓人好奇的是,台灣的喜鵲眞的是蔣允焄首先帶來的嗎?
19世紀,府城有位名叫徐宗幹的官員,曾經描述他對喜鵲的感覺。
1851年秋天,洪紀、林鬧等人在今天官田、六甲一帶糾集群眾,擧旗起事。當時的道員徐宗幹,與總兵葉紹春合作,調動兵馬,很迅速解決了這場動亂。
隔年,徐宗幹因這項功勞,獲得朝廷賞賜戴花翎;而前幾天,他就在庭院裡,聽到喜鵲們聒噪的叫聲。之後,他弟參加科擧,考中進士第33名,那陣子他也常聽到喜鵲的聲音。
對於這些現象,徐宗幹是這麼解釋的:台地向無鵲,皆附船桅而來,或有人攜一雙至台而哺育之。不常見,見則必有喜音,或鄉人至。
他先說到,台灣以前沒有喜鵲,都是海上船舶帶過來的,因為經常有人帶來養。這可能表示,就算蔣允焄曾經帶過喜鵲來府城,也不代表他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或許,喜鵲早就以寵物鳥的身份,多次來到台灣,是當時社會生活中一種習俗文化。
接著,徐宗幹又提到,如果看到喜鵲,可能會有好事要發生,或者可能有同鄉、親戚來訪。而他自己就有幾次類似的經驗。
在中國文化裡,喜鵲有「報喜」及「聯繫」的寓意,所以在傳說中,喜鵲被安排去幫牛郎與織女搭銀河橋。而在府城的寺廟裡,也常能看見以喜鵲為母題的雕刻或彩繪。牠們經常被拿去跟梅花擺在一起,製作出一幅「喜上梅梢」的吉祥畫面。
有這般美好的寓意,再加上身處在海外異地的台灣,這「聯繫」的感覺似乎就更為強烈了。徐宗幹認為,若是聽了一兩天喜鵲pica pica 的叫聲,三天內必然有親人朋友要從中國內地渡海而來,想必這些喜鵲是依著船舶,先飛到台灣岸上,來報平安的吧。
因此,喜鵲落腳於府城,帶給人們美好的景象,但似乎也有難以言喻的遠離感。城裡的人們,也許不想孤獨承受這種既細緻又複雜的情緒,所以就把這個情緒寄託在喜鵲身上吧。
少年葉石濤的愁緒
這樣的情緒,也曾遺留在府城作家葉石濤1930年代初期的少年記憶裡。
葉石濤記得,城內曾經有一處以喜鵲為名、被喚作「喜鵲巷」的地方。
那是一條小街道,本來的名字,並不叫喜鵲巷,但他也沒講眞正的街名是什麼。對於一個當時還在念末廣公學校的孩子而言,那是什麼地方,不是他關心的重點。他只記得,那是台南孔廟對面的巷子,路口矗立著一道貞節牌坊,而相當照顧他的四叔,以及四叔的女兒──長他一歲的堂姐,就住在街尾。

依照他的描述來看,這條街,應該是今日的府中街,以前叫做「柱仔行街」。往昔,這是通往孔廟的主要道路,所以街上靠近孔廟大門前方,豎立了一道石造的「泮宮」牌坊,那是1777年知府蔣元樞為了壯大孔廟的入口景觀而建立的。當年知府大人意氣風發的建築功績,百餘年後,在這位少年葉石濤因為重度近視而迷濛不淸的眼裡,成為了某某人家的貞節牌坊。
四叔家隔壁,是姓黃的大戶人家。黃家有位年輕的婢女,名字叫「喜鵲」,出身茄萣,讀過公學校。她與葉石濤堂姐弟的交情甚好,有時,喜鵲會指導他們做學校的算術習題;有時,也會跟他們一同拿竹竿,在庭院裡打芒果。
喜鵲的存在,讓葉石濤對這條小街巷有了深刻的印象。堂姐弟倆,把這條街暱稱為喜鵲巷。這個名字成為他們對喜鵲的記憶與懷念。
喜鵲在黃家的生活,過得並不開心,甚至受到虐待。某天,她選擇逃離黃家,臨行前還送了一個小錢包給堂姐留念,這讓葉石濤堂姐弟頗感悵然。過了幾天,喜鵲的遺體就在台南運河裡載浮載沉,被人發現,打撈上岸。
1988年,葉石濤將喜鵲巷的記憶──這段懵懂少年時光的優雅與愁緒,寄放在作品〈石榴花盛開的房屋〉中的字裡行間。
流動與生根的縮影
同樣都是外來物,如果說,府城的梅花是貼近統治者與大歷史;那麼,喜鵲應該就比較貼近地方社會人們生活與情感的縮影。
喜鵲跨海來到府城,算是「外來種」;但也有人認為,牠們已融入本地生態,成為台灣常見的留鳥,更合適的歸類應該是「歸化種」。
在這塊土地上就此繁衍生息的喜鵲,持續被人們視為美好、幸運之鳥。而較少人注意到的是,牠們也幫忙背負著移民社會的異地感,以及長久以來城市人們的各種纖細情緒。
隨著舊城區的都市化,今日在城內,已無法像往昔一樣,還能頻繁看到喜鵲蹤跡了。不過,在市區近郊,像是安平、億載金城一帶,偶爾還是看得到許多棲息的喜鵲。牠們成為評估現代都市生態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
喜鵲這樣跟隨著人們足跡,四處流動,繼而在新天地生根繁衍。這本身就很像是移民的縮影了。
作者:蘇峯楠
出版時間:2020年2月
出版社: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