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正如諸多研究者指出,當我們論述日本近代文學的發展史,必定要將森鷗外(1862-1922)的文學歷程置於日本近代史的視野裡,否則就不易找出這條主線。然而,要面面俱到評述森鷗外的思想作品,本身就是一種艱難的挑戰,因為不論對其語言(明治時期的文體)或者卷帙浩繁的存在,都足以讓好奇者望而卻步。

已故著名日本文學家唐納德.基恩在其《閱讀日本文學》評論集中,就曾提及他面對森鷗外文學的尷尬境地。他說,他寫信給日本文學專家同行求助,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考察,方能掌握森鷗外的精神面貌?結果,那名文學評論家告訴他,閱讀森鷗外沒有捷徑可言,因為其作品每部都很重要,必須仔細閱讀,有機連結似的加以融會貫通。就這樣,唐納德.基恩,接受了這個建議,從森鷗外於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所寫的日記、各類型的小說、乃至公共衛生領域的文章,逐篇讀起思考,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最終把《森鷗外全集》讀畢。就此而言,這種深入細緻的閱讀等同站樁練功,自然構成其評述森鷗外文學的重要基礎,更使他撰寫日本近現代文學顯得遊刃有餘。在此必須指出,本文囿於篇幅,對於森鷗外文學的描述,至多符合如其一作品的標題〈面影〉,亦即我們縱使秉持努力進取的精神,僅只能描摹龐大歷史中的片斷。
自我開啟文學之門
按編年史來看,森鷗外於明治17年至21年前往德國留學,正值二十出頭的青春年華。佐藤春夫曾將森鷗外這段留學經歷視為日本近代文學的開端,這個說法有其歷史連續性的考量,因為佐藤把明治時期全盤西化的進程,以及引進西方文學思潮,以此改變傳統文學局限的努力連結了起來。所以,森鷗外的德國取經之行很自然地被賦予重大任務,不可推卻地為明治時期的新文學開疆闢地。而森鷗外本人,對於時任陸軍省軍醫的自己能夠實現德國留學,畢竟是頗為喜悅和自負,在其《航西日記》中有詳細提及。嚴格來說,森鷗外就讀東京帝大期間,即是一個狂熱的讀者。據說,他讀遍了東京租書店的文學書籍,舉凡傳奇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到隨筆文類,江戶後期通俗小說家山東京傳、曲亭馬琴、為永春水的作品,甚至對於《剪燈餘話》、《燕山外史》、《情史》、《金瓶梅》等中國艷情小說有所涉獵,而且又酷愛漢詩詞文。他任職於陸軍期間,曾漢譯過《源氏物語》中的和歌以及《牽牛花日記》。
留學德國期間,森鷗外深受叔本華和哈特曼的影響,愛讀波爾.海澤、赫爾曼.庫爾茨的《德國短篇集》和這兩位作家合編的《新德國短篇集》。他愛讀這類小說的程度,從其撰寫的短評中可看得出來。波爾.海澤是具有仿古典傾向的慕尼黑派重要作家,亦是第一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但晚年時期,他遭受來自自然主義的攻擊,這也是後來森鷗外強烈批判自然文學的遠因之一。他返國之後,很快即譯出《德國短篇集》中的作品,這些作品包括:克蒂斯特的〈惡因緣〉、霍夫曼的〈懷玉有罪〉、哈克連德爾的〈兩夜〉等等。後來,森鷗外出版處女作《舞女》,從《舞女》內容和時代氛圍來看,都與上述作品有相似之處。就其文學階段而言,這時期的作品《舞女》、《水沫記》《信使》,標誌著他留學德國的生活縮影,同時顯現出早期傾向浪漫主義的清新氣質。研究者長谷川泉指出,森鷗外的文學特質有自然抒情的一面,亦有冷靜透徹和重視精確的追求。他不是那是耽於空想和以虛構見長的作家,反對空想無物的寫作風格。依他而言,即使其私小說的構思裡,亦是在傳達實際生活的側面,雖然在其《性生活史》作品中,又出現牴觸和矛盾。當然,這些文學影響是多重性的,有許多外國文學的影響、日本古典文獻和自然科學檢索實驗的成果。

與自然主義思潮的對峙
如上所見,熱衷於西化運動的明治時期,日本文化界人士無不做足思想準備,以迎接西方文藝思潮的到來。中村兆民譯出《維氏美學》(兩冊,明治16-17年),介紹了自然主義與何謂美學教育思想,尤其是,法國自然主義主將左拉的《論實驗小說》,形同向日本文壇投下了巨大的波浪。然而,出於自身的文學主張和審美觀點,森鷗外並沒接受《維氏美學》中的美學理論,反而藉由該書作者的說法批評左拉倡導的理論。左拉在文中指出,「實驗小說是這個世紀科學發展的一個結果;它延續和完善了生理學本身傾向於得到化學和醫學的支持;它用研究自然的人取代了研究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人,自然的人受到生理學的或化學的法則支配,並且要被環境的影響所改變。直言之,它就是我們這個科學時代的文學,正如古典的和浪漫派的文學是與經院哲學和神學時代一致的那樣。」他進而強調,「構成實驗小說的關鍵在於,要擁有關於人與生俱來的現象之機制的知識,要表明在遺傳和環境影響之下,人的智力與感性顯現的系統,正如生理學為我們提供的那樣,最後,要展現生活於由人本身創造出來的社會條件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變那些條件,在那些條件的核心部分中,他經歷了持續不斷的變化……」。在左拉看來, 文學不僅是對作者心理的表現,藝術家的個性始終都要服從於真實性和自然的更高律法。
然而,森鷗外反對左拉的觀點,他在《國民之友》發表文章〈最真實的科文學〉以「極美的美術」的對立詞加以反駁。在這篇文章裡,他由倫理道德的「善」價值而承認了美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頗有以德國人的科學精神,反制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思潮。同樣的,他也把以德國之思,用來批評同時代的文學健將坪內逍遙(1859-1935)。坪內逍遙與森鷗外同樣出身東京帝大,是個才華卓越的文人,能寫小說劇本又寫評論(翻譯過莎士比亞的作品)文章,日本第一部近代文學評論集《小說神髓》(1886),正是出自他的文筆。不過,森鷗外並不以為然。他認為,坪內逍遙批評近代小說的結構過於鬆散,人物特徵不明顯,並試圖將藝術之美從勸善懲惡中解放出來,誠然發揮著某些作用,但坪內逍遙並未能充分認識到美的自律性。另外,他甚至把筆鋒指向另一個戰場和對象。日本引進自然主義思潮以後,逐漸展現出具體成果,島崎藤村《破戒》(1906)和田山花袋《棉被》(1907)的問世,即是強有力的例證,進入大正年代,自然主義的勢力更壯大起來。所謂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森鷗外反對自然主義的聲音,得到同時代作家們的回應。例如,夏目漱石亦不贊同自然主義,其門下的安倍能成和阿部次郎等人,均提出論述反對自然主義。不過,自然主義作為移植自西歐的文學思潮,已經紮根在日本近代文學的土壤上蓬勃發展起來,不可能輕易被連根拔起。因此,與其說我們想知道在這場論爭中何者勝出,莫如說這些作家持不同立場就此展開的文學論爭,才是日本近代文學史研究者所關注的事件焦點。

從《即興詩人》到《性生活史》
從文如其人的角度而言,森鷗外在嚴肅捍衛自己的文學主張,以及後來向自然主義發出戰帖,無不顯露出其性格特質。他於1892年11月,在其主編的文藝雜誌《しらがみ草紙》上,翻譯連載安徒生的自傳《即興詩人》,後來結集出版,在其序言中寫道:「……由於我母親年老視力衰退,卻時常閱讀我的著作,為了不增加其視力負擔,本書採用4號鉛字排印……」由此可見,這是他發自真摰的孝心。在森鷗外的日記裡,還經常提及他們母子一起做校對的情景,即使時光回到現今社會,這種體貼母親的孝行,依然感動無數的讀者。其次就是他於1909年文學生涯的重大轉變。是年3月,他撰寫日語體小說〈半日〉,投寄給《昴》雜誌,在那以後,投稿次數更頻繁。7月,學醫出身的他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進一步邁向功成名就之路。然而,比這個更富精神成就的是,他發表了小說《性生活史》。在當時明治政府看來,這是一部驚世駭俗的小說,內容猥瑣不堪,嚴重違反善良社會風俗,因而遭到查禁。不過,森鷗外並不服氣,因為他對於西歐自然主義的本質知之甚詳。依照他的寫作企圖,寫作《性生活史》絕非模仿自然主義的作品,毋寧說,他是明確而有意識地採取與自然主義對抗的立場。如他所言,他每次讀到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會看到作品中的人物,無論在起居坐臥中,無論何事不管何時,盡是描寫性慾湧生的場景,難道人終其一生只能浸淫在性慾的生活中?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其實左拉的長篇外遇小說《身體的惡魔》即是此類型的代表。
從寫作策略來看,《性生活史》頗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諷意味。森鷗外認為,自然主義文學既然要描寫人生,卻硬性地扯上不正常的性慾描寫,本身即是一種矛盾,這如同對人生態度的僭稱。他還尖銳表示,《性生活史》不是描寫他的人生,而是為讀者而寫的。這就是說,讀者必須從《性生活史》中的旨趣加以掌握,才能理解他批判盲目接受這西歐文學思潮的用意。話說回來,這畢竟是森鷗外的文學觀點。從宏觀和時代格局來看,森鷗外與夏目漱石的作品裡,有一種貫徹著明治時代的倫理道義的氣概。在此,亦可這樣解讀,夏目漱石的人生觀深切影響或改變森鷗外的精神姿態。正如森鷗外的小說《青年》(1910),即以夏目漱石的《三四郎》為藍本而寫。與此相比,國民作家夏目漱石於大正5年去世,他在世時題書自勵的「則天去私」,充分表現對安心立命境界的追求,森鷗外的達觀則是他歷經明治和大正時代,進入老年之後,在苦惱艱難中到達的世界觀。
打開沉默之塔
回顧森鷗外晚年的精神結構,有助於我們理解其文學生涯和明治與大正時代的歷史光影,正是因為拾得這些有機的光影,我們才盡可能尋得政治歷史與文學場域之間的關聯。研究者發現,明治40年之後,森鷗外對於國家權力的批判有明顯增強的傾向。進而言之,從明治末期到大正時期日本政治社會局勢的變動極為巨大,政府對各種激進思想的鎮壓亦隨之加劇。以幸德秋水為首的「大逆事件 」為例,整肅和逮捕反映國家機器與訴求社會變革的知識人之間的對決。尤其是,明治43年日本政府開始對全國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展開大肆檢舉行動,是年12月10日,大審院(相當於最高法院)召開刑事特別庭,院方提出相關具體證物,起訴了此案異議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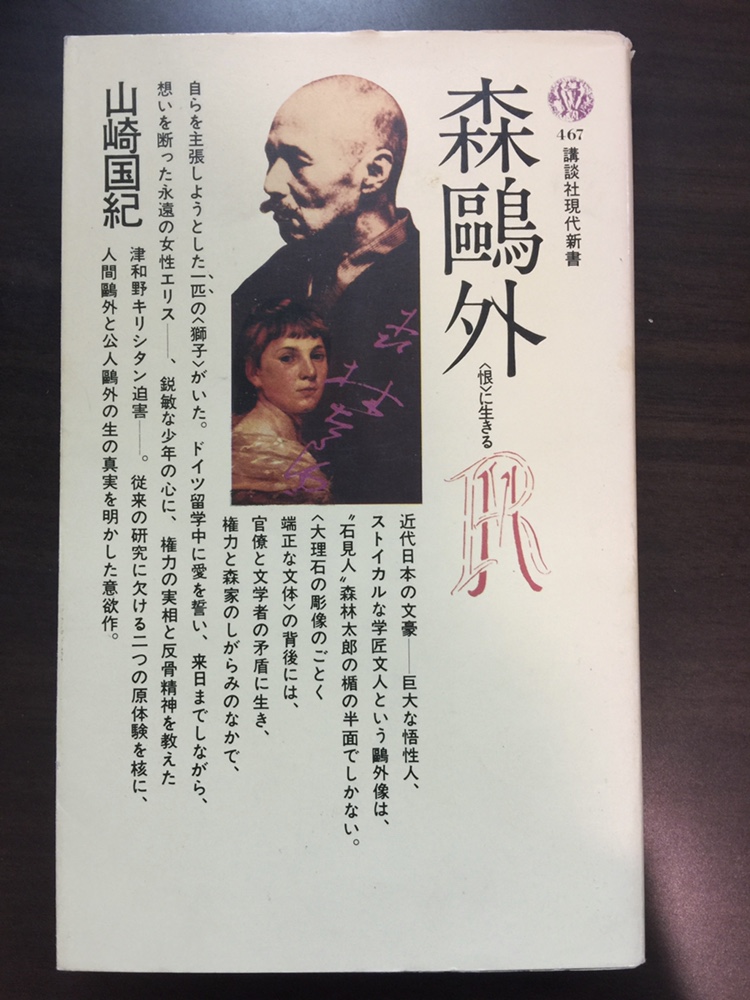
據神崎清編《大逆事件紀錄》(全3卷)中指出,召開公審當天森鷗外出現在特別旁聽席上。有了這條線索,我們是否就能找到森鷗外聲援反體制人士確切的證據?然而,在森鷗外的日記裡,並未出現「大逆事件」的相關記述,僅記載「他數日天來向特別辯護人平出修請教無政府主義方面的知識而已。」如果說,他對此事件有更大的暗示,那就是12月14日的日記裡「請平出修與謝野寬(著名歌人與謝野晶子的丈夫)進晚餐」,由此可見,在政治風雲詭譎多變的時代裡,身為政府的高官要職,當他們也在反思國家主義的本質,即使在私密的日記裡,同樣不宜輕易表態,更不可留下具體證據。如同政治哲學史家所言,他們必須習得和掌握隱微的政治修辭,才能安全地進入「迫害與寫作技藝」中,保全自身地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

按照這個思想路徑,森鷗外在短篇小說〈沉默之塔〉(明治43)中,即巧妙運用了文學的象徵手法。他這樣寫道:「高塔矗立在晚空下。許多烏鴉棲在高塔上,牠們想展翅飛起卻又停住了,不斷嘎嘎喧嚷著。後來,幾隻烏鴉飛走了。這時候,兩三隻海鷗彷彿憎恨牠們自由飛走的姿態,斷斷續續地叫著,時而接近高塔,時而黯然地飛向遠方。一台馱負重物的馬車來到了高塔下面,馬兒露出疲憊不堪的表情。他們好像在卸下什麼東西,接著又把東西運送至高塔內。接著,一台馬車離去,下一台馬車旋即又到,由此看來,塔內應該堆積不少東西了。我站在海岸上,凝視著這幅光景。夕陽下,浪濤波光粼粼拍打著岸邊的石牆。那些從市區駛來的先到高塔下又返回市區的車輛,從我的面前經過。我看見每台車輛的駕駛都戴著灰色帽沿下垂的軟帽,他們都低伏著身子。乍聽來,那疲倦的馬蹄和車輛碾壓小石子的聲響似乎更顯得單調困乏了。我一直站立在海岸上,直到灰色的高塔融入蒼茫的暮色裡。」換句話說,森鷗外在〈沉默之塔〉中,並未直接指名「大逆事件 」,托名「無政府黨事件的匪徒」,其實即是同情大逆事件中的受刑人。當時,森鷗外位居陸軍省醫務局長的高位,以其立場發言必然有所顧及。然而,對他個人有其意義,至少他為自己打開了沉默之門,為禁制失語的時代留下良心之聲,後代的讀者就能從這些文字之聲判讀或辨識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