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在日本詩歌的天空中,中原中也(1907-1937)是一顆不可抹滅的明星,值得同病相憐者和關注憂傷的人,向他投以最誠摯的目光。在他的詩行裡,尤其蘊藏青春與孤獨的糾纏,帶有濃烈的象徵主義氣息,引起讀者們的持續共鳴。這位國民詩人的生涯雖然短暫,但卻有跨越時空界限的抒情魔力。
按照中原中也的年譜來看,他於少年期間,即擅長作文和嚐試新體詩歌的創作。有一次,他在雜誌上看到譯自俄國白銀時代的安德烈.別雷的詩作〈斷章〉,心儀不已,其後投稿《婦人畫報》和《防長新聞》等報刊的短歌欄,前後共入選80餘首作品。1929年起先後參與創刊《白痴群》、《四季》、《歷程》等同仁詩刊。1934年,自費出版詩集《山羊之歌》,收錄1926-1932年詩作44首。後期作品《一個童話》(1936)、《無詞歌》(1936)等,抒寫飽經人生滄桑的感受。1936年,其年僅兩歲的長子因病夭折,他因而悲痛致疾,翌年住院治療。出院後,移居鎌倉,寫有詩歌《春日狂想》(1937)等,1937年10月22日,因結核性腦膜炎辭世。遺著詩集《往日之歌》(1938)多為1934-1937年作品,共計58首,帶有靜謐的幻想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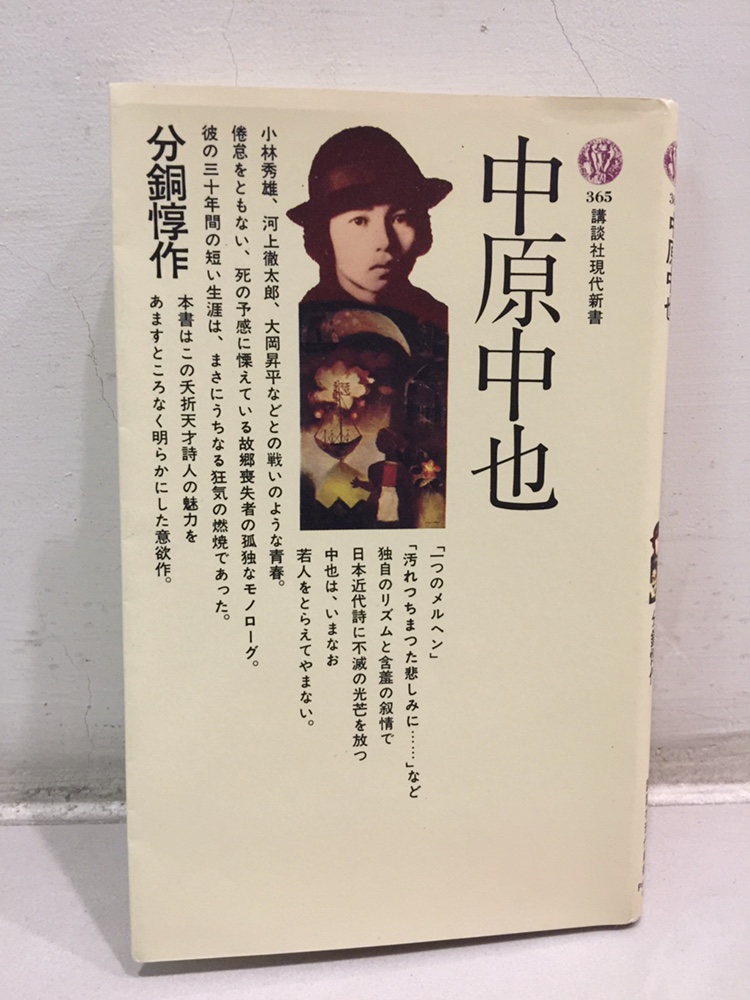
京都與青春歲月
對中原中也而言,從故鄉山口縣來到京都求學,標誌著他青春生活的印記,與達達主詩歌的相遇。看得出來,他對於大正12年春至大正14年春,居留京都這段經歷的重要性,以致於他後來在「詩的履歷表」(我的詩觀)中,特別地把它突顯出來。文章這樣寫道:「大正12年春,我因耽溺於文學而留級,轉校到京都的立命館中學。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離開父母身旁,頗有單飛的快感。是年秋末,於寒夜中,在丸太町橋邊的古本屋(舊書店),閱讀達達主義詩人(高橋)新吉的詩作。其中數篇,讀來甚為感動。大正13年夏,(詩人)富永太郎來京都,我向他請教諸多法國詩人的作品。大正14年11月,他因病去世,令人特別懷念。」
事實上,中原中也自小成績優異,但因迷戀文學創作,而遭到學校留級,此事對其父母親的心理打擊甚大,一時不知所措,卻又得顧及社會和親友們的觀感。中原中也原本想前往東京,之所以轉校到京都,是因為其家庭教師井尻(山縣)民男,從山口高校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所以,儘管他在文章中所說「頗有單飛的快感」,畢竟那時他才16歲,對於這個初來乍到的少年,終究一時無法抹除孤獨不安與寂寞的陰影,尤其他身為留級學生的挫敗感,像一道舊傷隱隱作痛。出於這種複雜的心理作用,或說少年敏感的心境投射,那種不受傳統規範的超現實主義的新奇詩歌,輕易地就闖入了他春青的徬徨之地。
與達達主義者相遇
高橋新吉(1901-1987)的第一部詩集,出版於大正12年2月,由辻潤(1884-1944 翻譯家、思想家,達達主義的核心人物之一)編輯。這種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試圖通過廢除傳統的文化和美學形式發現真正的現實,帶有無政府主義的藝術革命思潮運動,是由高橋新吉率先在日本詩壇引進和點燃的,彼時他還是個籍籍無名的詩人。高橋自愛媛縣八幡浜商業學校休學以後,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1920年,他參加《萬朝報》短篇小說徵文,以〈舉起火焰〉獲得入選,後來,於該年8月15日,在《萬朝報》上發表詩作和文章:〈享樂主義的最新藝術:戰後備受歡迎的達達主義。〉1922年12月,他向一名計程車司機宣稱:「從現在開始,我將要向世界宣傳達達主義!」卻因此與司機發生了衝突,他拿拐杖毆打對方,因而遭到逮捕。1923年,其詩集《ダダイスト新吉の詩》,以「DADA即断言否定一切」開始,接著為突顯自己在食堂清洗器皿時的心境,用「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皿/倦怠」的圖式來表現,顯示其天馬行空的詩作。有趣的是,像這種前衛的詩歌風潮,也跨越海洋影響著日治時期臺灣詩人的表現手法。毋庸置疑,高橋的詩作裡有著濃厚的達達主義色彩,不過他年輕時即傾心於禪學佛法,因此在其詩作當中,經常出現「禅-超越-形而上学」之類的詩句。根據分銅惇作的《中原中也》傳記指出,有些時候,他會一面讀著《大藏經》,一面融入達達主義的詩歌世界裡。

中原中也是如此喜愛高橋新吉的詩作,為其新奇的表現技法為之入迷,但是嚴格講,他並未完全能夠理解高橋晦澀難懂的詩意。為了打開這道詩歌之門,他必須藉助前輩詩人的提點,例如佐藤春夫為其詩集的序文和辻潤的後記,都給予很大的裨益。佐藤春夫說道:「從精神氣質來說,高橋是個充滿理想的人,同時也是個迷失於理想的人。因此,在他的作品當中,有一種苦悶和不輕易表露出來的真實情感。他對於前世紀的頹廢傾向所消蝕的美感導致毀壞的結果感到憤怒,因而就更貪婪地索求這種難以捉摸的情感流動。就此而言,作為理想主者的高橋,與深刻的務實主義者是聲氣相通的。」由此看來,文學前輩佐藤春夫這樣評語,對於中原中也後來撰文〈論高橋新吉〉有著明顯的影響。另外,辻潤在後記中說道:「文學藝術就是恐怖的遊戲,一種冒險和思索。就此意義來說,新吉的詩集大概無法成為資產階級家庭裡的讀物、不宜作為學校的教科書,不適合作為耶誕節禮物。然而,在日本,他是最初和最稟承達達主義精神的人,甚至是最深刻把握的先知先覺者!」而這些雄辯性的評價,同樣給予這個16歲的少年莫大的刺激。
愛情的苦澀
從那以後,我們必須把視點置於中原中也的文學友伴們,亦即他與富永太郎和小林秀雄的交誼,以及劇場女演員長谷川泰子的情愛世界,因為在其後來的詩歌生命中,他們對於這個早慧的詩人影響甚深。然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原中也竟然不知文學好友小林秀雄,在那時正與長谷川泰子暗通款曲。他們這段奇怪的三角戀愛關係,很快就成了人們飯後的談資。儘管如此,小林秀雄對其詩友的關懷,還是被引為佳話。他在1925年9月7日的札記中,這樣寫道:
「探望T之後,我與N走在青山路上。下午四點,昏黃陽光照映在布滿塵埃和嘈雜以及如塗上油漆色彩的都市。我們二人在六丁目的資生堂坐下,都覺得疲憊萬分。一隊士兵高唱著軍歌,像褐色的隊伍緩緩經過。N看著行進的隊伍,表情厭惡地問:那是什麼顏色?我說,那是保護色,他們連水壺都塗上相同的顏色。我們二人默然不語。此時,我想起了Y子。士兵的隊列繼續前進著。我說,你看,那也是令人迷惑的形式之一呀。N回答說,哪個人不被這種形式迷惑呢?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夏天,他們只知道暑氣和赤身裸體。我說,你別再說了。我感到焦灼起來。與其說分辨哪些事物是美或醜,不如說,我最先考慮的是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的問題。總而言之,這一天,我感到特別痛苦。然而,對於我和N見面而想起與Y子之間的關係,沒有被性格激烈措詞嚴厲的(N)看穿,倒是有幾分僥倖心理。但每次意識於此,我就會內疚不已。我最初與N認識時,他給我的印象很奇特,既吸引我又使我厭惡。顯然,N具有我所沒有的特質。他那達達主義的風格,與我的虛無主義形成對比。但若要說我為何對他感到厭惡,我也說不上來。據他解釋,這是他因其早熟而來的卑劣行為。」
研究者指出,小林秀雄在札記中的英文縮寫,T是指富永太郎,N是中原中也,Y則是長谷川泰子。實際的情況是,詩人富永太郎於大正13年2月,從京都返回東京之後,於大正14年2月,第二次咳血,6月併發肋膜炎,夏秋之間,他的身體愈來愈糟。從那以後,他在代代木的住家臥床不起。小林秀雄所這裡所記述的,即他與中原中也去探望富永太郎返家路上的情景。這時,小林秀雄是東京帝大文學部法文科的學生,他是經由其高中學長富永太郎的介紹而認識中原中也。換言之,彼時他們結識不到半年,而小林秀雄卻被長谷川泰子的氣質深深吸引,進而在札記中寫道:「我對她已痴情到極點……」。對於這件事情,小林秀雄終究還是感到愧疚的,他在〈回憶中原中也〉的文章中,這樣提及:「不用說,當我回憶中原的時候,就必須把這件事情置於核心,只不過,我悔恨的洞穴既深且暗,使我不相信自己是否具有坦白的勇氣和撰寫往事的才能。」
寒夜中的自畫像
然而,這段糾纏三個人之間的戀情,於昭和3年5月命定似地劃下了句點。小林秀雄與長谷川泰子還是分手了,而中原中也接獲父親去世的消息,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必須返回山口老家處理葬禮。回想起來,他的確辜負了父親的期待,不專注於學業的精進,在都會過著浪蕩的生活,如無根漂泊的人,在這時候,詩歌成為他心靈的最大支柱。小林秀雄前往奈良以後,中原中也經小林秀雄的介紹,結識了年長他五歲的河上徹太郎,他們二人志趣相投,為文學與詩歌貢獻心力。昭和4年4月,他們創辦了同仁雜誌《白痴群》,以此展開新詩的探索。除了中原與河上外,該雜誌同仁,包括阿部六郎、內海誓一郎、村井康男、大岡昇平、古谷綱武、富永次郎、安原喜弘等七人。不過,這份同仁雜誌,因沒有擺脫文學青年的習氣,終至沒能形成氣候。正如大岡昇平指出:「我們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同仁全來自中原中也的文友,每人繳交10圓會費,而且是隨興而寫,收稿的情形不佳,因此到昭和5年4月為止,共出刊了6期,即告停刊了。」當然,這並非停刊的所有原因。詩刊同仁異口同聲認為,中原中也是個不易相處的人,他的言行極為隨興,與人二話不合,就動手打架,極端自戀和自我厭惡,是個矛盾的集合體。也許,這就是詩人稟性和宿命,一如中原中也發表於創刊號的詩作:
〈寒夜中的自畫像〉
雖說不上身手敏捷
緊握著這一根韁繩
穿越這黑暗的地域!
只要意志明確
面對冬夜我不嘆息
那唯有焦躁的哀愁啊
因憧憬而附隨的女人們的哼唱
任其,刺痛我的肌膚。
踉蹌著腳步卻保持平靜,
帶著些許做作的心態
我勸諫我的懶惰
一邊行走於寒月之下。
開朗,坦蕩,且不出賣自己,
這是我靈魂的祈願! (引自吳菲的《山羊之歌》中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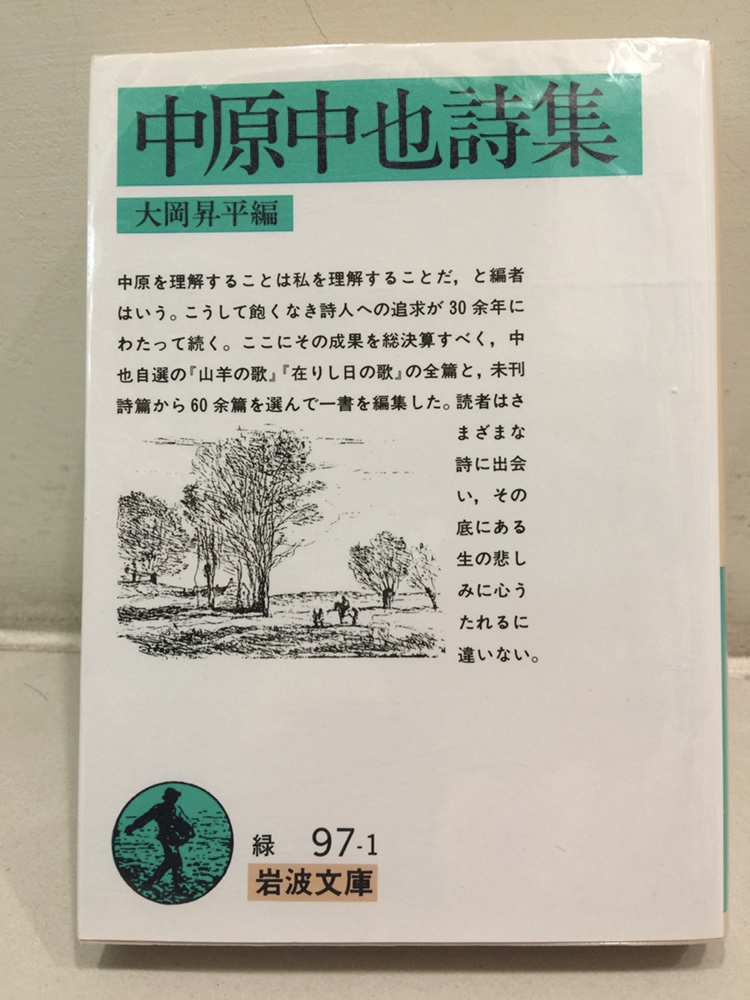
為青春的詩魂祈禱
一生中活著自卑與自戀中的中原中也,晚年期間病情逐漸惡化,這使得他更珍惜在世的時刻。昭和12年晚春,小林秀雄和中原中也到鎌倉的妙本寺觀賞海棠花。關於這段記遊,在中原中也的日記中亦有簡單記載。他們在八幡宮的茶棚喝了啤酒,在暮色中看著青煙似的柳樹。但是這時情況有異,中原喝了一口啤酒,突然語氣悲愴地喊道:「啊,ボーヨ―、ボーヨ―;ボーヨ―到底是什麼回事?」然後,他目光呆滯地說:「我前途茫然啊!ボーヨ―、ボーヨ―。」眾所周知,他所說的「ボーヨ―」,是指他和小林秀雄及長谷川泰子的三角畸戀,結果就是他的文友搶走了他的情人,由此可以看出,這件事情表面上已如煙消逝,中原中也直到臨終前仍然無法忘卻。進言之,從詩歌的含義中,固然可以理解一個詩人的思想世界,但還必須顧及詩人的肉體與靈魂的細微連結。根據其朋友記述,中原中也到了是年9月,身體狀況越來越糟,視力模糊、經常頭疼,甚至步行困難,不斷重複說很想返回故鄉老家。這時候,他開始整理和謄寫《往日之歌》詩稿。這部遺作託付給小林秀雄,後來交由創元社出版。

確切而言,中原中也在世期間名氣不大,所以其撒手人寰的消息,並沒有引起日本詩壇的震盪。他生前出版過《山羊之歌》詩集,翻譯過三冊《藍波詩集》而已。正如前述,其第二部詩集《往日之歌》亦是死後出版的。應該說,中原中也在去世之後,才逐漸受到日本詩壇的重視。因此,為了哀悼這位抒情詩人,各雜誌陸續推出追悼號專輯。例如《紀元》(昭和12年11月)雜誌、《四季》、《文學界》、《手帖》(均於昭和12年12月)。所有在雜誌的撰文者,幾乎都是中原中也生前的文友,包括青山二郎、河上徹太郎和大岡昇平,他們極其細微地寫出與這位詩人的思想情誼。在《文學界》的追悼號上,刊載了島木健作、阿部六郎、草野心平、菊岡久利、萩原朔太郎和關口隆克等作家的文章。

當我們回顧詩人的一生,難免為其英年早逝而惋惜,為其波折的生涯而喟嘆。不過,正如不幸中也有幸運的一面,詩神慷慨地賜予他寫詩的才能,任他運用細膩的筆觸抒發心靈的創傷,這是庸碌之人所夢寐以求的立身之地。更幸運的是,在戰爭酣熱未止的年代,他並沒有被送往前線戰場上打仗,沒有在半夜中吶喊母親名字的恐懼,而是得以埋骨故鄉的家族墓地裡。兩相對照之下,我必然是肯定這種幸運的結局,退一萬步說,這世上沒有人喜歡與苦難不幸打交道,最好是離它越遠越好,站在自由光亮的土地上,安然哼唱著屬於自己國度的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