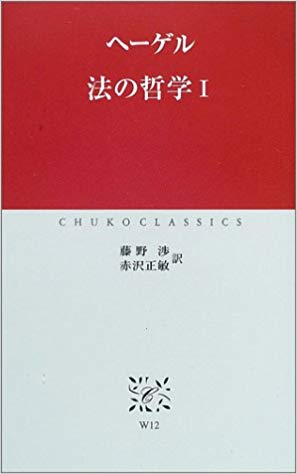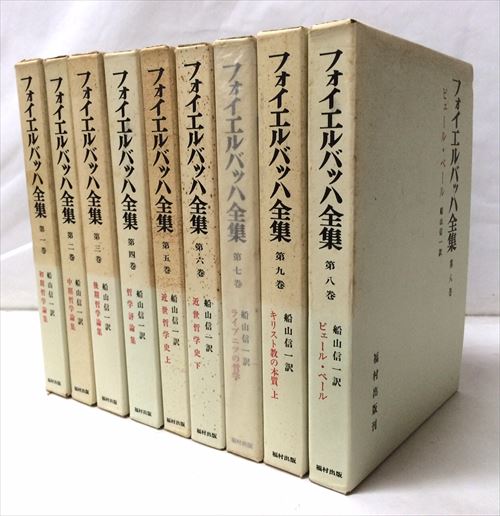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基於某種時間的壓力,我手上一得空,便要整理雜亂的書庫,否則真的快堆得寸步難行了。平時,我甚少運動或健步養生,以前還抽空到游泳池,游個八百公尺,健壯肺部兼瘦身,試圖消減哮喘的發作,只是這些運動,現在全成明日黃花了。於是,我想既然失去戶外活動的動能,不如整頓書籍的秩序,將它變成室內運動,以此來鍛鍊手臂和大腿的肌肉群,看自己坐在電腦前打字的時間,是否真能增長?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厚積的灰塵,往往會因搬動而升揚起來,這時沒戴上口罩防護,恐怕支氣管又要遭殃了。在這方面,我有切身的苦澀經驗可供佐證。
我以這樣作為拙文的開場白,倒不完全沒有一點好處。我發現,為書籍和書架的層板拂去灰塵之際,許多擱置多年的舊書,彷彿突然睜開了眼睛,向我投來召喚的目光,像是在提示著什麼。在這種指引之下,我很快地就與舊有記憶的線索接連了起來。我以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四卷本)為例,因為這套書與我頗有緣份,彼此往來了三十餘年。大約在1985年左右,我在臺灣大學前的書攤前,幸運地購得這套書。我知道其書(中譯本)的存在,當然是從閱讀馬克思的論述中得知的。當時,在浪漫主義色彩壓倒左傾思想的讀書界裡,凡是馬克思批判過的和讚譽過的人物和書籍,他們盡其可能都要找來一讀方可罷休。但不容否認的是,這種書籍只宜在地下傳閱,不能公開的閱讀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有因禁書而反動的仰慕,也有(文青)時代病的意味,未必每個讀者都能讀得通透,將來成為馬克思的專家,恣意汪洋寫出萬言文章來。

我購買《哲學史講演錄》的動機極為簡單,完全出於利已主義,與閱讀時尚無關,僅希望增加哲學史的基礎知識。試想,對不諳德文和英文的讀者而言,要弄懂哲學史就不容易,手裡有中譯本可讀,絕對是刻不容緩的樂事。另外,我即將於翌年前往東京學習日本語文,在尚未掌握這門外語之前,藉由閱讀而保住中文表達的通暢性,不致於使半調子的日文和外強中乾的中文,彼此混用交纏在一起。後來證明,這個自我提醒還是有用的。我在正規日文教育之外,在打工結束以後,返回簡陋的公寓裡,陸續閱讀著《哲學史講演錄》。但不知什麼原因,我每次閱讀到興奮的頂點,就想上廁所,情況嚴重一點,竟然拉肚子。這種奇妙的經驗,也發生在我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時候,看來處女座的讀者胃腸不好,已是不可逆的宿命。
說來有點邪門,讀完黑格爾的哲學史,自然就有一種慾望和衝動,更想閱讀費爾巴哈的著作,因為馬克思曾經大力批判過費爾巴哈的哲學觀點,這使我也想知道費氏到底何許人也,他有什麼本領惹得馬克思用很大篇幅評析他的哲學起源。只不過,據我所知,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臺灣,要找到人民版的《費爾巴哈選集》已經實屬困難危險,能夠獲得地下複印本,就值得放鞭炮慶祝一番了。彼時,我的確是天真無知。我一直認為在漢語文化圈裡,只出版兩冊《費爾巴哈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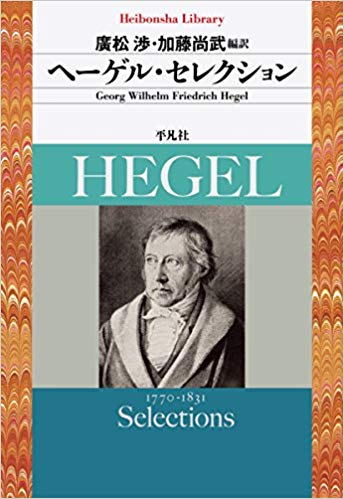
進入一九八七年,我尋找中譯本《費爾巴哈選集》似乎出現了生機。我們班上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其中有兩個同學品行不錯,下課後我們稍有往來。我經常藉機與他們談點馬克思什麼的,可我發現他們似乎興趣索然,有時露出困惑的表情,最後他們向我坦承,他們這一代人已不讀這種書籍了,擺著都顯得佔據空間呢。後來,我靈機一動,請他們於中國春節返鄉探親之時,幫我購買《費爾巴哈選集》,一定全額照付。我想,他們必定認為我是個怪人,竟然在讀這種不安之書?不過,基於我在日文方面給予他們很大的照料,他們還是接受了我的請託。開學後,來自上海的同學說,他找到了《哥達綱領批判》,但臨行之前,卻把它忘在車上了,他為此深表遺憾。我說:不要緊,也許時機尚不成熟,費爾巴哈暫時是不想見我,我再稍等時間看看。來自北京的同學說,費爾巴哈真是難找呀,他跑了幾家舊書攤,都沒找到我所渴求的經典作品,沒能回應我的央託,心裡有點過意不去,所以贈予我兩卷《西方文學理論》作為補償。其實,我很感謝這兩位中國籍的同學。他們尋書未果有許多因素,至少透過他們的說法,我知道自己的閱讀立場,我還在閱讀不合時宜的書,這無異於是自我檢視的機會,我到底所為何求?我真的不是跟隨流行,真的很想閱讀費爾巴哈嗎?
我一如既往,不打工的日子,就到神田的舊書店街巡視,以此擴大眼界和見聞。某日,我無意間在書店裡發現了日譯本《費爾巴哈全集》的身影,儘管那只是品相普通的分冊,對我卻是極大的亮點。有了分冊和導讀的指引,我事後才知道《費爾巴哈全集》已於1974年出版,共計十八卷之多,真是不簡單啊!必須指出,這套全集由出自西田幾多郎門下的哲學家船山信一(1907-1994)以個人之力譯出的,其崇高的譯業令人欽佩。說到這套全集,以我當時的打工收入,幾乎沒有任何餘裕買下。因此,我稍為改變做法,從日本學者撰寫的《費爾巴哈傳》入手。我打算了解得更深之後,再購買全集不遲。只是,人生的歲數有限,不可能同時踏入兩條河,終究必須做出抉擇。隨著往事和思想的發展,蒐齊日譯本《費爾巴哈全集》的夢想就此打住,我只買了兩冊,以此表示我對老費和翻譯家船山先生的敬意。

談完我短暫的費爾巴哈情結,接著,我必須回到「黑格爾」的話題上,事情不可講得含糊其詞,語言的明晰特性,永遠受到哲學家的愛戴。1990年,我返回臺灣求職的時候,這套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也隨行而回。遺憾的是,那時我徒有青春之力,收入並不穩定,因多次搬遷的緣故,最後把黑格爾死後由學生筆記整理的代表作,置放在苦寒潮濕的八里的公寓裡,因不敵風雨和白蟻侵蝕,被整得面目全非,書頁潰爛到不容辨識的程度了。但從那以後,我又興起了整全《哲學史講演錄》的念頭,彷彿那是一件應盡的任務。目前,我手頭上這四卷本平裝書,正是我為自己和閱讀黑格爾所做的紀念。換言之,從閱讀黑格爾到找尋費爾巴哈的譯本過程中,我自始至終都在履行讀者的角色,用最緩慢的速度,用堅定的目光追尋著文字之思,然後隨之移動,隨之躍過語言的橋樑,抵達先是由想像構成的後來眼見為憑的哲學風景。這由兩個作古多年的德國哲學家所構建的哲學世界,不論是唯心論或者唯物主義,在歷經時光的反覆淘洗,其真實的樣貌似乎絲毫都不曾改變,他們如塗上神奇的化妝水一樣,永葆青春和煥然如新。從這意義來說,我不得不認為在與時間的較量中,終究是哲學家的著作技高一籌,他們死後的骨頭並未朽敗,而且還硬得很。根據歷史考古學家指出,它們的用途廣泛,可以用來擂鼓宣志,也可以敲醒現今世紀還在貪睡的靈魂。